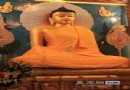日本古建築為什麼看起來很新?
日期:2016/12/14 22:00:50 編輯:古代建築史首先要分清,前現代的建築維護更新和現代文物保護的維修原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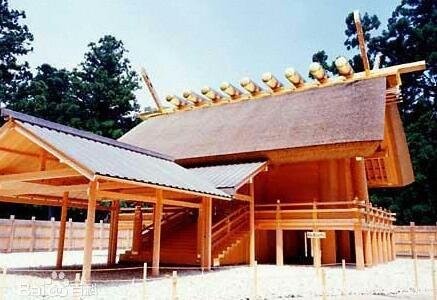
先說前現代。對於幾乎絕大部分東方木構體系的建築文化而言,“修舊如新”其實原本是建築整修的第一原則。古人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文物保護意識,除了個別的一些建築可能由於獨特的歷史價值受到少數人的保護(比如我國很多古代石刻依存都是由地方士紳建造圍牆房屋保護的,但這個數字很少)。蘇東坡在《東坡志林》提到,他曾在見過某地漢代的講堂,並認為這是海內遺留下來的最古建築。推想起來可能是類似武梁祠的石造建築。不論如何,蘇東坡如在當地任職,肯定會設法保護這座建築。但這是相對特殊的歷史建築而言。與此相對,對於實用建築,不論是宅邸宮殿還是壇廟城垣,既然是生活中使用的一部分,要求其新而堅固是正常不過的事情。可以想見,這種指導思想之下如維修一座木構建築,那麼必然是丟棄全部腐朽的木料,替換上新的木料,用時興的架構取代原有的架構(屋架制度無論中日韓,歷史上都是不斷演變的),最後再粉刷一新(或者全部拆除重建)。這種做法的原因,梁思成在《中國建築史》上將其歸為客觀和主觀兩方面:客觀上土木結構保存不及石構;主觀上東亞文化就有不求木構建築長久的傳統,基本是公允正確的。所以首先,說只有日本人追求“修舊如新”的效果是不准確的,更不能說替換部件或者改變內部結構的維修方式是日本做法,因為整個東亞地區前現代建築維修的指導思想都是“修舊如新”。只不過由於日本潮濕的氣候和歷史上形成的文化傳統(比如許多神社的造替制度),這一點
很明顯,這種維修思想和現代歷史文物建築的保護理念是存在沖突的。現代文物建築保護的原則,在1964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制定的《威尼斯憲章》說的很清楚:
第四條 古跡的保護至關重要的一點在於日常的維護。
第五條 為社會公用之目的使用古跡永遠有利於古跡的保護。因此,這種使用合乎需要,但決不能改變該建築的布局或裝飾。只有在此限度內才可考慮或允許因功能改變而需做的改動。
第六條 古跡的保護包含著對一定規模環境的保護。凡傳統環境存在的地方必須予以保存,決不允許任何導致改變主體和顏色關系的新建、拆除或改動。
第七條 古跡不能與其所見證的歷史和其產生的環境分離。除非出於保護古跡之需要,或因國家或國際之極為重要利益而證明有其必要,否則不得全部或局部搬遷古跡。
第八條 作為構成古跡整體一部分的雕塑、繪畫或裝飾品,只有在非移動而不能確保其保存的唯一辦法時方可進行移動。
第九條 修復過程是一個高度專業性的工作,其目的旨在保存和展示古跡的美學與歷史價值,並以尊重原始材料和確鑿文獻為依據。一旦出現臆測,必須立即予以停止。此外,即使如此,任何不可避免的添加都必須與該建築的構成有所區別,並且必須要有現代標記。無論在任何情況下,修復之前及之後必須對古跡進行考古及歷史研究。
第十條 當傳統技術被證明為不適用時,可采用任何經科學數據和經驗證明為有效的現代建築及保護技術來加固古跡。
第十一條 各個時代為一古跡之建築物所做的正當貢獻必須予以尊重,因為修復的目的不是追求風格的統一。當一座建築物含有不同時期的重疊作品時,揭示底層只有在特殊情況下,在被去掉的東西價值甚微,而被顯示的東西具有很高的歷史、考古或美學價值,並且保存完好足以說明這麼做的理由時才能證明其具有正當理由。評估由此涉及的各部分的重要性以及決定毀掉什麼內容不能僅僅依賴於負責此項工作的個人。
第十二條 缺失部分的修補必須與整體保持和諧,但同時須區別於原作,以使修復不歪曲其藝術或歷史見證。
第十三條 任何添加均不允許,除非它們不致於貶低該建築物的有趣部分、傳統環境、布局平衡及其與周圍環境的關系。
第十四條 古跡遺址必須成為專門照管對象,以保護其完整性,並確保用恰當的方式進行清理和開放。在這類地點開展的保護與修復工作應得到上述條款所規定之原則的鼓勵。
顯然,將一座歷史建築整修成新建築的前現代做法明顯違背了上述的第五,第六,第九,以及第十一到十三條。但事實上,如果我們用《威尼斯憲章》的規定去比照,就會發現,“修舊如舊”這個概念也是存在問題的。很簡單,如第十一條的規定,如果一座建築存在後代的改建,那麼現代文物保護人員的工作,不是將這些後代改建拆除,而是將它們與早期的結構一並保存整修,而非修復到早期結構原始的那個“舊貌”去。回到樓上賀六渾的答案舉的例子,我們可以發現,唐招提寺維修鮮明反映了這兩種維修理念的變化:對於元祿時代的人而言,一旦發現上層梁架結構陳舊損壞,那麼就直接使用當下流行的小屋組桁架予以代替是再自然不過的事;對於明治時代的人而言,現代文物保護理念還未完全成形,保存建築物的存續和大致外觀就成為了維修的目標,為此使用鋼架結構自然也就是允許的;而到了2000-2009的大修,我們可以看到它事實上嚴格貫徹了威尼斯憲章的規定,沒有改變元祿大修添加的小屋組桁架結構,也沒有替換明治大修使用的鋼構,同時也盡量使用了老的建材(700余根椽子依然是天平時代的原物),充分體現了《威尼斯宣言》所強調的原真性與可識別性兩大原則。相反的例子是我國的兩座唐構:山西五台山南禅寺大殿和河北正定開元寺鐘樓,在維修過程中(前者70年代中期,後者1990年)都拆除替換了後世的改建,從門窗小木作,到屋面瓦作都使用了“復古”的做法,在保留唐代建構的同時,剔除後代增改部分,最後修復成了我們現在能夠看到的“唐風”建築。這種“修舊如舊”的做法,既不符合中國古人的維修方法,也與《威尼斯憲章》所體現的現代文物建築保護理念相左。
熱門文章
熱門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