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根源緣何成文化圈民國“大佬”
日期:2016/12/14 18:49:42 編輯:古代建築史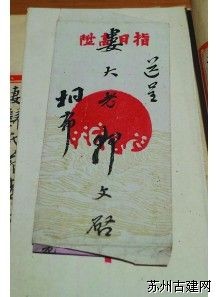
建設新農村、西部訪古、邀社會各界小王山留下文化遺跡……李根源隱居蘇州後迅速融入了當地的主流“文化圈”。然而令人困惑的是,經濟並不富裕,而且資料顯示並沒有固定來源的李根源又是如何擔當起"無米之炊"的重任?此外,在根深葉茂的“本土”文化聚集地,來自異域的李根源又是如何做到“一呼百應”,成為蘇州文化圈內的民國“大佬”?
“桃園三結義”李根源打進蘇州文化圈
蘇州是座歷史名城,地面地下文物古跡比比皆是,掌故轶事更是數不勝數,這對酷嗜金石文獻的李根源來說,可謂如魚得水。分析一下與李根源來往的蘇州鄉紳與文士便可以理清這樣一條脈絡——從中,我們不難看出李根源這一“舶來文化”融入根深葉茂蘇州文化的氛圍的路徑。
留學日本,與孫中山一起籌建同盟會,並成為首批會員,在雲南發動新軍響應武昌起義,參加二次革命、護法運動……多年積累的政治影響力以及特有的人脈關系網,已經有足夠的魅力讓他迅速融入當地的文化主流。
事實上,有著“代總理”頭銜的李根源落戶蘇州時,已經與當時的“國字”號文化大家們相交甚廣。
有據可考的資料顯示,退隱吳門後不久,李根源應章太炎邀,偕於右任、柏文蔚、田桐等人祭掃了上海宋教仁墓。此時,李根源的老同學李鴻祥、殷承獻李曰垓及好友韓玉辰也正好來蘇州休養,因李宅房屋寬敞,都寄住在李家。
這年冬季蘇州文人名士金天翮、張仲仁等邀請李根源參加“九九消寒會”,李根源從此與吳中賢俊吳蔭培等蘇州耆紳名人交往。吳蔭培是吳中保墓會會長,李根源又歷來重視保護文物古跡,所以這些人一見如故,深相投契。
張仲仁先生(1867-1943)是蘇州有名的巨紳,在清末,他中了經濟特科的第二名(相當於榜眼),民國初年就任教育總長,位高而望重,說出來的話一言九鼎,極有分量,被蘇州市民尊稱為“仲老”。或許是因為有著在北洋ZF共事的經歷,在眾多名人志士之中,章太炎、張仲仁與李根源相關最為密切,可謂有“桃園三結義”之交。而這便為李根源進入蘇州文化圈打開了一扇大門。
加盟南社文化圈裡的民國“大佬”
九十八年前的一個秋天,蘇州虎丘虎阜橋堍的張公祠裡熱鬧非凡,一群意氣風發的文學志士,像天邊的鴻雁飄然而至,雅集於此,談詩論詞。觥籌交錯、酒酣耳熱之際,發起人陳去病、柳亞子等同盟會會員振臂一呼,眾人一致響應,就此誕生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革命文學團體——“南社”。
南社不單純是一個革命文學團體,而是一種歷史的文化景象,大多數南社骨干,是近現代軍事、思想、文化、教育、出版等各領域的精英,他們不同程度上受西方先進思想的熏陶,以天下興亡為己任,把個人功名事業與國家安危聯系在一起,李根源便是會員之一,除此之外,會員中更有陳其美、黃興、宋教仁、廖仲恺、於右任等辛亥革命中叱咤風雲的人物,而且在報界、學界、文壇等領域,南社社員更是一統天下,如蘇曼殊、李叔同、蔡元培、沈尹默、馬敘倫、馬君武、劉半農、沈雁冰、包天笑、周瘦鵑、曹聚仁等,他們發表的詩集、文集、小說、翻譯文學,乃至參加編輯的報刊雜志總數在千數以上,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正是有了這個“南社”的集聚平台,李根源走入了蘇州文化圈的核心,更因為他的威望,李根源成了民國時期蘇州文人舞台中的一位“大佬”。而縱觀李根源一生,為人仗義而豪邁,身處政壇之時,常常不吝大手筆資助落魄之人,退隱之後,來自親朋好友或者舊同僚之間的資助亦堪稱“豐厚”,因而雖然生活並不富裕,但是也用不著為經濟發愁。
推薦閱讀:
晉城:一村之中就有兩處“國寶”
婦好長方扁足鼎青銅禮器
長沙將建漢長沙王(國家)考古遺址公園
埃及金字塔附近發現4000多年前祭司墓(圖)
巨金購得周用的“象笏”吳江望族感恩建“笏園”
在與蘇州社會名門望族交往中,李根源與吳江周麟書(字迦陵)的一段交往則至今仍為人們所津津樂道。
李根源寓居姑蘇,與蘇州一班文人學子交往密切。除了章太炎、金松岑之外,就要數費樹蔚(1884-1935)了,說起來他還是柳亞子的親舅舅,曾創辦蘇州電氣廠、織布廠等實業。費氏的韋齋堂上,天天高朋滿座,李根源與周麟書都是韋齋堂的常客。
周麟書是吳江松陵鎮人,與李根源同是南社社友。周麟書早年畢業於蘇州府中學堂,歷任吳江中、小學校長,吳江鄉村師范學校教師,是吳江知名詩人,有《笏園詩鈔》存世。說到“笏園”的命名,要追溯到李根源。
周麟書喜愛收藏,尤其是搜羅祖上的象笏、官服、腰帶、印章等等珍貴遺物。1927年冬的一天,李根源與周麟書前來參加韋齋堂的消寒會。周麟書拿來了祖上的一幅《歸牧圖詩》墨跡,李根源欣賞之後,知道明朝工部尚書周用就是麟書的先祖。便將先前在開封用巨金購得的一柄周用的象笏贈予周麟書。就在韋齋堂上,眾人看到了四百余年前的象笏,上面還有“周氏六世孫”镌刻的文字。
得到祖上的象笏,周麟書高興得不得了,在吳江松陵北下塘故宅園內大興土木,專門籌建華屋,作為藏室。這座建築即將建成時,李根源為周麟書的新屋題寫了“傳笏堂”的匾額,金松岑也作了一篇《作堂記》,周麟書自己又請名家繪制了一幅《還笏圖》中堂。“堂成大觞賓客,骈列其家珍冠帶,自遠而至,當是時也,可謂至盛。”周麟書也算是一個有心人,他時時處處,搜集祖上象笏,歷四十余年而堅持不懈,最後搜得象笏150余種,這些古代的象笏對周迦陵而言,既可以作為家珍同時又是國寶。柳亞子先生觀賞過象笏之後,曾經賦贈五律《題周迦陵〈還笏圖〉》一首,其中有“偶然遺尺笏,合浦珠光燦”等句,詠李根源先生的善舉,也贊美周迦陵的美意。柳亞子之後,蘆墟南社社員沈昌眉有《周迦陵招飲傳笏堂,出示先德遺制百五六十種,琳琅滿目,蔚然大觀,賦此紀盛》,其他社友及文人墨客也都紛紛作詩填詞予以贊歎,成為轟動一時的吳江盛事。
書寫墓志銘更是李根源的拿手“本領”。他為上海義士、南社詩人劉三書寫的墓志銘則被傳誦一時。
辛亥革命時期,重慶人鄒容19歲就完成舉世震驚的《革命軍》。1912年2月被孫中山追贈為“大將軍”。他撰寫的《革命軍》,在當時風行全國,成為鼓動人民參加革命的號角,討伐清ZF的檄文。1905年,鄒容著《革命軍》,觸犯清廷,被關進監獄。劉三旦夕探詢,還常常帶些油酥餃、如意酥、寸金糖等鄒容向來最喜歡的食物前來看望。烈士死後,沒人敢為他收斂,劉三哭之恸,為之營葬華泾家園旁,慨然以私人之田園,讓地數弓,為埋骨之所。章太炎在《鄒容墓志銘》中稱劉三雲:“上海義士劉三,收其骨,葬之華泾,樹以碣,未封地。”又雲:“劉三者,性方潔,廣交游,業為君營葬,未嘗自伐,故君諸友不能知葬所。”這篇墓志銘,由李根源手書。至此,江南義士劉三的大名遂傳遍海內外。
編纂民國《吳縣志》留下珍貴歷史資料
而李根源對編撰方志的愛好也是頗值一書。
當年,吳中紳士為保護吳縣古墓葬,有個民間組織,叫吳中保墓會,一度由前清探花吳蔭培主事。吳探花突患中風,臨終前,將保墓會委托給李根源主持,李根源義不容辭,承擔了下來。該會對調查和保護吳縣古墓葬作了不少工作。至今,有些古墓葬還保留著該會建立的石碑。由於李根源對吳中古墓葬作過深入調查,所以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修《吳縣志》時,聘請李根源擔任總纂之一,負責修其中的《冢墓志》。這部縣志已出版,為三十年代所修地方志中水平較高的一種。
李根源一生為我們留下了大量著作,如《雪生年譜》、《阙茔石刻錄》、《曲石文錄》、《曲石詩錄》、《松海》等,這些著作,為我國軍事、政治、金石、歷史文物、名勝古跡、國故文學等方面的調查、考證、纂修工作,提供了豐富的內容,作出了較大的貢獻。
事實上,李根源在蘇州時,過往密切的文化界朋友不計其數,晚年李根源時常懷念在蘇州時舊友,曾作《吳門贈友詩二十四首》。其中贈吳湖帆詩為“吳門憶吳裝,海上足徜徉。丹青無二手,采筆自凝香。”,贈周瘦鵑為:“園林春事晚,蜀魄聽聲聲。啼到口流血,瘦影綠陰橫。”贈范煙橋詩為:“石湖美風月,千古屬范家。行春橋下去,蓑笠老煙霞。”
贈《謝孝思》:康樂乘時會,保全吳文物。存殁均同感,其績應著錄。
建林則徐紀念碑留住蘇州文化豐厚遺產
李根源對蘇州古城文化的貢獻意義,遠不止於此。
在蘇州市中心北局廣場,有一座“林公則徐紀念碑”,碑身雖不高,卻樸質凝重。林則徐的英名當然由他的浩然正氣鑄就,但在廣袤的華夏大地上,真正為他立傳樹碑的地方卻並不多見。那麼緣何蘇州會有這座林公紀念碑?誰又為林公書碑勒石?林則徐早年曾先後任過江蘇按察使、布政司、江蘇巡撫,在江蘇任職八年,治水利、赈災民、辦漕運、舉吏治、改良農業等方方面面都有政績,急民之所急,為黎民百姓做過不少好事,姑蘇後人是一直懷念在心的,只是缺少一個為他樹碑的發起人。1931年,日本軍國主義在東北發動“九·一八”事變前夕,在民族危亡之際,隱退在蘇的李根源為激勵蘇州民眾伸張民族氣節,當仁不讓地當了這個發起人,他奮書“林公則徐紀念碑”以志紀念。李根源的愛國思想也稱得上是與林公精神一脈相承,“往昔去思碑尚在”,林公碑,正是蘇州文化精神中的一份豐厚遺產。
蘇州自古以來佛教興盛,寺廟繁多,有著名的虎丘山寺、靈巖寺、上方山楞伽寺院、開元寺、文山寺等。對此現為蘇州博物館收藏的《吳都法乘》記載甚詳,不失為我們考研吳都佛教文化的重要佐證。然而,《吳都法乘》的留傳,與李根源先生不無關系。李根源曾經一直很想求得這套書而未得,後來終於在清怡親王祠見到這套書的舊抄本,便與主僧商量借抄,主僧答應借十日,於是李根源先生迅速斥資請了二十人“秉燭夜書”,結果如期竣工歸還。當時很想付之刻印,以廣流傳,但終因“茲事體大獨力難任”,又由於“人事蹉跎”而沒有成功。最後一直到民國25年由“裕甫”諸公於上海景印宋版藏經會印成此書,從而留住了又一份文化遺產。
推薦閱讀:
晉城:一村之中就有兩處“國寶”
婦好長方扁足鼎青銅禮器
長沙將建漢長沙王(國家)考古遺址公園
埃及金字塔附近發現4000多年前祭司墓(圖)
- 上一頁:名人墓留住蘇州文化“坐標”
- 下一頁:漫話蘇州古城水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