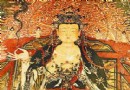中國傳統香道文化 香霧隱繞輕簾,缥缈幽回花窗
日期:2016/12/14 22:02:28 編輯:古代建築史
香之為用,其利最溥。物外高隱,坐語道德,焚之可以清心悅神。四更殘月,興味蕭騷,焚之可以暢懷舒嘯。晴窗搨帖,揮塵閒吟,篝燈夜讀,焚以遠辟睡魔,謂古伴月可也。紅袖在側,秘語談私,執手擁爐,焚以薰心熱意。謂古助情可也。坐雨閉窗,午睡初足,就案學書,啜茗味淡,一爐初熱,香霭馥馥撩人。更宜醉筵醒客,皓月清宵,冰弦戛指,長嘯空樓,蒼山極目,未殘爐熱,香霧隱隱繞簾。又可祛邪辟穢,隨其所適,無施不可。
——明朝屠隆
香,靈動高貴而又樸實無華;玄妙深邃而又平易近人。既能悠然於書齋琴房,又可缥缈於廟宇神壇;既能在靜室閉觀默照,又能於席間怡情助興;既能空裡安神開竅,又可實處化病療疾;香道,既是一種文化,又是一種精神。
我國香文化意蘊深邃,源遠流長。相傳孔子在從衛國返回魯國的途中,於幽谷之中見香蘭獨茂,不禁喟歎:“蘭,當為王者香,今乃獨茂,與眾草為伍!”遂停車撫琴,成《漪蘭》之曲。
自古文人讀書以香為友,獨處以香為伴;衣需香熏,被需香暖;士大夫於公堂之上以香烘托其莊嚴,松閣之下以香裝點其儒雅。調弦撫琴,清香一炷可佐其心而導其韻;幽窗破寂,繡閣組歡,香雲一爐可暢其神而助其興;品茗論道,書畫會友,無香何以為聚?
孟子曾言:“香為性性之所欲,不可得而長壽”。他不僅喜香,而且闡述了香之大道,認為人們對香的喜愛是形而上的,是人本性的需求。從魏晉時期流行熏衣開始,上流社會便將焚香視為雅事,將愛香當作美名,相沿成習。唐宋以後風潮更勝,不僅是民間,官衙府第也處處用香,甚至接傳聖旨和科舉考試之時也要專設香案。
一爐香,一縷煙,既可靜思,又能洞察梵煙缥缈。凝神靜觀縷縷清煙,或筆直冉冉而上,或迂回缭繞而行;時而旺熾澎湃如墜五裡霧中;時而形單孤拔如絕壁卓然靜逸。潛心攝受入鼻根之香氣,或香甜、或清新、或雅致、或醇厚……香韻的千姿百態,如夢似幻,似假還真,一如眾生實相,皆是存在與虛無相續間的泡影。
香,靈動高貴而又樸實無華;玄妙深邃而又平易近人。既能悠然於書齋琴房,又可缥缈於廟宇神壇;既能在靜室閉觀默照,又能於席間怡情助興;既能空裡安神開竅,又可實處化病療疾;香道,既是一種文化,又是一種精神。
我國香文化意蘊深邃,源遠流長。相傳孔子在從衛國返回魯國的途中,於幽谷之中見香蘭獨茂,不禁喟歎:“蘭,當為王者香,今乃獨茂,與眾草為伍!”遂停車撫琴,成《漪蘭》之曲。
自古文人讀書以香為友,獨處以香為伴;衣需香熏,被需香暖;士大夫於公堂之上以香烘托其莊嚴,松閣之下以香裝點其儒雅。調弦撫琴,清香一炷可佐其心而導其韻;幽窗破寂,繡閣組歡,香雲一爐可暢其神而助其興;品茗論道,書畫會友,無香何以為聚?
孟子曾言:“香為性性之所欲,不可得而長壽”。他不僅喜香,而且闡述了香之大道,認為人們對香的喜愛是形而上的,是人本性的需求。從魏晉時期流行熏衣開始,上流社會便將焚香視為雅事,將愛香當作美名,相沿成習。唐宋以後風潮更勝,不僅是民間,官衙府第也處處用香,甚至接傳聖旨和科舉考試之時也要專設香案。
一爐香,一縷煙,既可靜思,又能洞察梵煙缥缈。凝神靜觀縷縷清煙,或筆直冉冉而上,或迂回缭繞而行;時而旺熾澎湃如墜五裡霧中;時而形單孤拔如絕壁卓然靜逸。潛心攝受入鼻根之香氣,或香甜、或清新、或雅致、或醇厚……香韻的千姿百態,如夢似幻,似假還真,一如眾生實相,皆是存在與虛無相續間的泡影。
熱門文章
熱門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