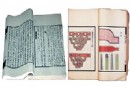王學義:把一塊泥巴摔出了名堂
日期:2016/12/14 9:53:32 編輯:古代建築史

蛐蛐罐也是一種文化
蛐蛐的學名又稱促織、蟋蟀,是一種善斗的鳴蟲。最早,農民們為了慶豐收,常常在地裡挖個土坑,捉一對蟋蟀讓其相互撕咬,後來逐漸演變成了一種獨特的民俗活動。追溯歷史,斗蟀的傳統已超過千年。興盛之期上至皇宮內院、達官顯貴,下至庶民百姓,都有大量癡迷於此道者,這樣盛蛐蛐的容器(俗稱蛐蛐罐、蛐蛐籠)的制作手藝也成為了一項絕活傳下來。
制作蛐蛐罐的材質和造型都相當講究,從初始的金質、象牙,到瓷罐、紫砂、澄泥,而精細的宮廷御制罐,其工藝和裝飾則更為豪華,無論雕刻、鑲嵌,都達到極致。珠寶、鑽石附著其上,小巧富麗。瓷罐中不乏官窯極品,藝術價值不亞於其它瓷器。罐的外形也有頗多創造,最常見的有鼓圓形、鼎圓形、直筒形、菱形、八角形等等。若按時間順序來講,在唐朝用的是金絲編成的金絲籠,宋朝就用瓷罐了。到了明朝,雖有些窯口還時興精瓷彩繪,但隨著紫砂罐的問世,逐步代替了瓷罐。而此時出現的澄泥罐,因其透氣性好,泥質罐從此占了主導地位。澄泥罐又稱澄漿罐“澄漿”,顧名思義,是最細的泥沙。用這種材料制成的罐,呈青灰色、淺綠色,式樣古樸,特別是其中一套復雜的砸底工藝,更顯其造詣的功夫。此工序要用高溫消毒罐體,再用黨參、朱砂等中藥秘方調成面漿,使用專用工具一層層的砸底,稍有閃失就會砸破罐底而前功盡棄,可見其功力之深。蛐蛐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裡,既補氣,又安神,所放食物也不易變質,十分有利於蛐蛐的成長。
隨著澄泥罐的普及,湧現出了不少的制罐名家。最有名的是明代的萬裡張和清代的趙子玉。萬裡張的罐,糠胎大甕刀切底,柔和潤美,堪稱一絕,淘換到一個萬裡張的罐,現在至少得幾十萬元。趙子玉的罐,漿皮細膩,端莊大氣,也是難得的精品。這些老罐的存世量雖然已經不多了,但可喜的是,古老的制作工藝還是流傳下來了。蛐蛐罐也成為了一項不容忽視的藏品。它的民族特色和歷史淵源,都為藏家所喜愛,由此而凸現的市場行情也呈迅急上升的趨勢。
郭氏罐子的傳承
郭景生是全國知名制陶人,1936年生於天津,他自幼喜歡中國古文化。年幼偏好蟋蟀,對蟋蟀頗有研究,固此對蛐蛐罐收藏也樂此不疲。年輕時往返京津兩地,尋覓老蛐蛐罐,了解制罐過程,結識了不少名家。經北京秋蟲名家,蛐蛐罐鑒賞家黃振風老先生指點,專心攻於仿制趙子玉蛐蛐罐,經多次失敗後最後終於成功。通過京津兩地藏罐名家鑒定,與存世趙子玉罐對比,達到了以假亂真的程度。愛好者鼓勵年輕的郭先生批量生產,可為人正直的他拒絕了仿制。一心研制,開發個人對蛐蛐罐理性認識,總結自制對蟲體飼養有利和不利的經驗,多年來從蛐蛐罐膛底到蛐蛐罐器形變化,做出早秋,晚秋用罐的標准和尺度。在用泥方面仍遵循古人之道。經過幾十年的摸索,在全國各地喜愛蟋蟀人士,都知道天津有個罐子郭。
在郭先生開發津門蛐蛐罐之時,收了早期弟子王學義為徒。王學義自幼喜好蟋蟀和蛐蛐罐,在郭先生的指導下,從選泥、淋泥、揉泥、制坯、修整直到看火燒窯掌握了制罐全部技術。並在開發新品種,成為郭先生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文革時期,民間藝人不好生存。郭先生忍痛割愛允許弟子王學義自立門戶,因此就出現了津門學義派系的各種制陶工藝。其風格獨特,蛐蛐罐品相端莊,手感細膩,窯火到位被愛好者視為極品,從民間把玩提升到了亦可把玩也可收藏的境界。
王學義陶藝,在繼承古法的基礎上,集合現代文化科技,不斷創新,無論制陶藝術,還是藝術品味,都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王學義制陶30多年,不斷搜索,苦心鑽研,不僅練就了一身镂空絕技,並創造出來一套獨特的燒制工藝,無論白陶、彩陶,所創造出來的造型別致,工藝精湛,均屬藝術珍品,為了傳承提高發展這一遠古文化藝術,做出了卓越貢獻。
王學義速寫
王學義,一個干瘦的農村老人。在村口接我們時,因為長年在轉輪前工作,患上了塵肺,走路過多便會喘個不停,所以騎在電動自行車上基本不能下來了。
進到他的院裡,也是他工作的小作坊,簡陋而零亂,屋裡屋外堆滿了一袋袋的沙土和各種原材料,再有就是一排排的蛐蛐罐成品和泥坯。在陰暗的小屋裡,兩台沙輪旁便是他的床鋪,30年來,他就在這裡一直兢兢業業地守候著他所鐘愛的陶藝事業,而且每天一干最少是12個小時!長年殚精竭慮地對陶藝的研究與制作已把他熬得骨瘦如柴,弱不禁風。應當說,王學義是個純粹的藝人,靠手藝吃飯的勞動者,一年幾萬塊的收入,對於一個農民來說,不多也不少。如今玩蛐蛐罐的大都是些有錢的主兒,動辄成千上萬一只,可是他從沒有昧著自己的良心胡要價,更不眼紅這個行當裡那些靠做赝品而一夜“致富”的投機分子。采訪當中,幾個買家在挑選時,橫挑鼻子豎挑眼,一會兒說蓋不嚴,一會兒又說罐上面有水印,王學義故意斜觑著眼說:“這些罐子個個都是我用刮刀一下下磨出來的。每個外形也是我夜裡不睡覺,絞盡腦汁地琢磨出來的。”說著又劇烈地咳嗽起來,思傷心、憂傷肺真是一點不假!“外面賣的有不少赝品,價格是便宜,而且看上去好像很精道,可那唬人的玩意只能是唬外行,哄著自己玩兒還行,真拿出來騙人,讓行家一看就露馬腳了。這些仿制品做法都極其簡單,就是用做蜂窩煤的馬蹄形模子軋制,一下十個。”說著他又拿出一件未完工的罐子來做給我們看,他說:“我的這些制品,選材用的都是上好的澄漿泥。然後拖出大概形狀,陰干。再後铉罐,把罐體的表面積密度增大,再次陰干。陰干的過程不能太快只能在屋裡背光的地方自然風干,之後每三小時按三角形旋轉一次,每一次的陰干大概需要1周的時間,待罐體干透以後在表面進行浮雕,刻出自己想要的人物及其他。再次陰干,待罐體全干以後方可進窯燒制,在進窯燒制時一定要控制溫度的高低,不然就會前功盡棄……”
在訪談中,王學義從沒有多少空洞的炫耀,他也根本不尋什麼所謂的虛名。翻看他的資料時我們看到,作為一名民間藝人,他是天津市民間藝術家協會會員,天津市工藝美術學會會員,2002年中央電視台,2004年《每日新報》,2005年新加坡早報網上對王學義的事跡與作品都有報道。他曾參加了南京首屆中國民俗吉祥藝術節,獲二等獎;參加了第一屆和第二屆中華民間藝術精品博覽會,他的得意之作一百單八將還獲得了第三屆中華民間藝術精品博覽會第一名。采訪中王學義說起一件趣事:“現在什麼人都有,有人被熟人領著來了,你對他熱心相待,而且前後給他便宜了很多了,可此君晚上卻跳過院牆接著來玩‘順手牽羊’,我就在黑暗裡看著他這個人在那挑選,當時真是感覺既可悲又可歎,臨完看他‘選’得差不多了,沖著他喊了一聲,走時把門給我關好!”說罷屋裡人都哈哈大笑起來,從這件看似玩笑的小事上或許證明了他的陶藝制品的價值所在吧!
他說:“我很少賣鬧自己的手藝,也不需要別人幫著我去賣鬧!”他指指外屋慕名而來的買家說:“你看看這些人,哪個也不是忽悠來的!”他指著桌頭的一塊泥坯說:“這幾十年,哪個人吹牛,把一塊泥巴摔出名堂來,能用它換來錢!”這話不假,不久前,他還從上海接手了一筆三百對蛐蛐罐的訂單,差不多有7萬元。
-
没有相关古代建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