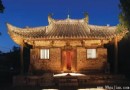家常著的同裡
日期:2016/12/14 9:58:30 編輯:古代建築史家家門前,都傍河擺著籐編桌椅,上有涼棚撐著,茶壺一把,茶杯幾只。你若走累了,就坐下來喝口茶吧。不喝也沒關系的,就坐坐吧,坐到天晚了也沒人趕你走。一直急不可耐的時光,在這裡,緩慢下來,像一方暖陽,泊在那裡。真好,不用急著趕路,也沒有未完的事在催著,這會兒,你屬於你自己,一顆心完完全全放下來,像那房檐下蹲著的一只發呆的小白貓。
發呆?確是如此。河裡不時有游舫搖過,那上面就坐著幾個發呆的人,臉上有陽光的影子在跳躍。河不寬闊,河水也不夠清澈,甚至有點渾濁。岸邊的倒影,在水中模糊成一團色彩,仿佛有人隨意潑上了一大桶顏料。卻沒有人介意這樣的河,沒有人介意這樣的水,要的,只是這樣一個悠閒的日子,承載難得的清靜和喜悅。
當地婦人埋首在膝上的篩子裡,在剝一些小圓果子。白的肉出來了,小米粒似的。我站邊上饒有興趣地看大半天。她由著我看,至多笑笑,復低頭剝。我終於忍不住相問,你剝的是什麼呢?婦人笑答,芡實啊。見我發愣,她說,就是雞頭米啊,可以做糕點,也可以熬湯煮粥喝,養脾髒呢。要不要來點?她問我。我笑著搖搖頭。滿街的芡實糕,原來是這個做的啊。
游人們這裡探頭看看,那裡探頭看看。看什麼呢?紅燈籠下的人家,一律有著深深的天井。一個天井就是一個或幾個故事,幾世人的悲歡離合,都化作一院的香。是桂花。每家院子裡,似乎都栽有一棵。十月,它的香已濃到極處,滿街流淌。游人們奢侈了,踩著這樣的香,去看退思園,去訪崇本堂和嘉蔭堂,在三橋那裡等著看抬新娘子。
同裡的三橋,幾乎成了同裡的象征。三橋分別是太平橋、吉利橋、長慶橋,呈“品”字形跨於三河交匯處。當地習俗,逢家裡婚嫁喜慶,是必走三橋的。做新娘子的這個時候最神氣了,被人用大紅轎子抬著過三橋,邊上有人口中長長念,太平吉利長慶!探問當地人,這風俗起於何年何代呢?都笑著搖頭說不知。祖上就是這樣的啊,他們平靜地說。祖上到底有多久?隨便一座橋,都沐過上千年的風雨――這一些,在一路奔來的外地人眼裡,都是驚歎,同裡人卻早已把它化作淡然。有什麼可驚可歎的呢,他們日日與之相伴,成為家常。
天光暗下來,游人漸散,同裡回歸寧靜。我回入住的客棧,那是幢老宅院。走過一段狹窄且幽暗的通道,方可進入天井。二層小木樓,木格窗,古樸樸的,很久遠的樣子。我坐在天井裡,我的背後,是一些肆意瘋長的花花草草。一只貓蹲在一口甕旁,靜靜看我一會兒,跳過窗台去。我跟主人王阿姨聊天,我說你們同裡出過很多名人啊,你家祖上是做什麼的?王阿姨低頭笑,說,小老百姓呢。她提一壺茶,給我面前的杯子斟滿,問我,明早想喝粥嗎?我煮粥給你喝。我笑了。這才是好,小老百姓的日子,本是現世的,當下那一茶一飯的溫暖,才是頂重要的。
- 上一頁:百壽古鎮話“百壽圖”
- 下一頁:明清古鎮上的羊樓洞磚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