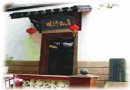車塵馬跡尋古道(四)秦代的主要交通干線
日期:2016/12/16 20:08:08 編輯:古代建築史
四、秦代的主要交通干線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實現統一之後,分天下以為36郡,為了鞏固統一,急需加強交通。於是立即致力於全國交通網的建立,在戰國交通的基礎上,“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史記?秦始皇本紀》),經過修整與溝通,將全國道路納入以全國為規模的交通系統之中。
1. 秦直道
《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五年,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六國年表》: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為直道,道九原,通甘泉”。《蒙恬列傳》:“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裡。道未就。”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蒙恬督師修築自雲陽直抵長城腳下九原郡治的道路,全長1800裡,合今約751公裡(漢制每裡折今417.5米,以下同)。修築道路時,逢山開山,遇溝填平,大體南北相直,一般道寬20米以上,是京城鹹陽至北部邊塞九原最接近的道路,故稱“直道”。
直道南起雲陽林光宮(今陝西淳化縣梁武帝村),沿子午嶺北行,經今陝西淳化縣鬼門口、旬邑縣石門關、黃陵縣艾蒿店沮源關、古道嶺、富縣槐樹莊、張家灣西側、甘泉縣橋鎮鄉方家河村、志丹縣安條林場、侯氏鄉等地進入安塞縣境,又沿橫山南麓經今子長縣北境、子洲、米脂、榆林等縣西境,穿過毛烏素沙漠,進入鄂爾多斯高原,過內蒙古自治區烏審旗北,東勝縣西側,在昭君墳東側渡過黃河,達九原郡(郡治九原,今內蒙古包頭市西孟家灣)。這條直道一半修築在山嶺上,一半修築在平原草地上。其中蜿蜒在子午嶺山巅的一段路線,完全沿山脊直行,遇到河川切斷山嶺處,下了嶺坡,旋即上梁,很少在川道中盤桓,敷設別具一格,是名副其實的“山脊線”。
直道為什麼以雲陽為起點呢?因為雲陽距國都鹹陽不遠,其間有往來方便的交通大道。鹹陽至雲陽之間修有馳道,道的兩旁都築起了垣牆,又稱甬道,車輛駛過如同穿行巷中。雲陽縣北有座甘泉山,峰巒起伏,雲高氣爽,風景十分秀麗,是避暑的勝地。山上建有林光宮,秦始皇經常去那裡游幸。戰國時期,甘泉是子午嶺下的一個顯要關隘,起著屏蔽鹹陽的作用,秦始皇常去林光宮,也包含著一定的軍事意義,所以直道也從這裡為起點。
直道的修築主要是從戰略上考慮的。匈奴長期以來活動於陰山南北,早在秦統一六國之前,就經常向南進攻。秦國以及東部的趙、燕諸國經常受到匈奴的侵擾,首當其沖的又是秦國。匈奴控制的地區,南邊可到寧夏固原、陝西榆林一線,即戰國時的秦長城以北的鄂爾多斯草原和六盤山、橫山北麓,距鹹陽最近處僅250公裡。匈奴的輕裝騎兵疾行一晝夜就可到達。秦始皇以前的秦國,一般都對匈奴采取消極防御的戰略,征發民眾修築長城,但長城並沒有也不可能完全保障北方的安寧。秦始皇統一全國後,就派遣蒙恬率領30萬大軍北征,把匈奴驅逐到了陰山以北。秦王朝在新統一的地區建立了34座縣城,從內地遷徙了大批民眾到這些地方定居,並在今包頭市以西設置了九原郡進行統籌管理。在驅逐匈奴的第二年(公元前212年)下令修築直道,以便有效地統治這一片國土。據史料記載,秦直道修通以後,秦始皇的鐵甲騎兵,從林光宮軍事指揮地出發,三天三夜就可以抵達陰山腳下,與長城構成“T”形戰略防御體系,使匈奴“不敢南下而牧馬”。
直道是一條軍事要道,也是發展商業貿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道路。從多年來直道沿途出土的文物來看,有秦漢的貨幣、銅鏡、車馬器、戈矛,北魏以至明清各代的石窟、摩崖石刻、寺廟碑文等,說明直道長期為商旅所行。
直道於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基本建成,總共用了兩年半時間。其工程之浩大,工期之短促,鑿山之艱巨,填溝之困難,實屬中國古代築路史上勞動人民創造的奇跡。
無情的歷史似乎作了一個有意的安排:秦始皇三十七年,他最後一次出游東方,在山東德州患病,七月死於河北巨鹿的趙國故苑沙丘宮。根據中東府令趙高的安排秘不發喪,載屍的辒辌車經井陉而抵達九原,即是從剛剛修好的直道急速返回鹹陽。
直道從林光宮(又名甘泉宮)北行900公裡直抵邊防重鎮九原。秦代經營的交通大道多利用戰國原有道路,只有直道是在秦統一後規劃施工,開拓出可以體現秦帝國行政效率的南北大通道。司馬遷行經直道全程,曾經發感慨說:“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史記?蒙恬列傳》)
清代嘉慶年間文獻記載:“若夫南及臨潼,北通慶陽,車馬絡繹,冠蓋馳驅……”這表明秦直道的荒廢僅是近幾百年的事。從子午嶺上現存的直道遺跡看,直道是一直循著子午嶺主脈修築的。因為鄂爾多斯草原也散布著許多丘陵台地,所以直道經過草原時免不了一番“塹山堙谷”的工程。在現存的遺跡上,路面最寬處約50米,一般也有20米。歷盡兩千多年風雨滄桑,在山區間,有部分路基保存完好,垭口遺跡明顯,古道清晰可辨,驿站石基依然存在。在今內蒙古東勝縣城西南的漫賴鄉,曾發現一段直道遺跡,路面殘寬約22米,路基的斷面暴露極為明顯,用當地的紅色砂巖填築。由此向北和西南,均可以見到山岡上有當時開鑿的四個寬約50米的豁口。這四個豁口連成一線,向人們訴說著2000年來的風風雨雨。
2. 秦馳道
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馳道是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開始修築的。它以國都鹹陽為中心,通向全國各個重要地區,是專供秦始皇出巡時行駛車馬的道路,即御道。馳道的修築,是秦漢交通建設事業中最具時代特色的成就。通過秦始皇和秦二世出行的路線,可以知道馳道當時已經結成全國陸路交通網的基本要絡。
秦修馳道規模宏大,標准較高。據《漢書?賈山傳》所載:秦“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賈山為西漢政論家,他是反對秦王朝政策的,對於馳道侈麗的描述,不免有所誇張。考古工作者曾在陝西鹹陽市東北窯店鎮南側渭河北岸的東龍村以東150米處,發現一條南北向古道路遺跡,路寬50米,築於生土之上,兩側為漢代文化層。這條道路,北為秦都鹹陽的宮殿區,向南正與漢長安城的橫門相對。以秦宮布局“象天極”的規劃意圖分析,這條道路應當是南北溝通鹹陽宮與阿房宮的交通干道,當時自然當歸入馳道交通系統之中。據調查,陝西潼關以東的秦漢馳道遺跡,路面寬達45米以上。
馳道選線盡量追求平直,減緩坡度,擴大曲線半徑,以便於提高通行速度。馳道是區別於普通道路的高速道路。當時馳道是路面分劃為三的具有分隔帶的多車道道路。“中央三丈”是所謂“天子道”。經過特許的貴族官僚可行旁道。馳道就連皇太子也不得擅自通行,直到漢代仍是一條御用道路。《漢書?成帝紀》說漢武帝做太子時“不敢絕馳道”。他當上皇帝之後,特別優待他的****母,“有诏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不過,漢代的馳道已經不僅僅為皇帝所專用了。只要有皇帝或者太後、皇後的诏令,其他王室成員也可以行於馳道之上。這種交通道路規則固然充滿濃重的****色彩,體現出等級尊卑關系,然而在當時針對社會各階層所擁有交通工具質量、數量差別懸殊的現實,其存在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作為最早的具有分隔帶的道路,馳道在交通道路史上也具有值得重視的地位。
雖然馳道是御用道路,在戰爭年代馳道御用的規定就沒有那麼嚴格了。劉邦的部下周勃攻伐反叛的燕王臧荼,就利用了馳道的交通便利而迅速出兵,在易下消滅了敵軍。
馳道由鹹陽向東作扇形展開,東北通至今河北省北部一帶,東至今山東省一帶,東南通至今江蘇、浙江及湖北、湖南、安徽省一帶。
秦始皇完成統一事業第二年(公元前220年),在首次巡游鹹陽以西之後,下令開辟天子巡行天下的馳道。《史記?秦本紀?集解》引應劭注:“馳道,天子道也。道若今之中道。”《資治通鑒?漢紀》武帝太始三年條胡三省注引孔穎達說:“馳道,正道御路也,是天子馳走車馬之處,故曰馳道。”中道(御道)供皇帝使用,兩側旁道供臣民通行。“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記述了馳道的修築規則。中道寬三丈,種上青松,作為界標。“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是記述馳道的修築技術,意思是說,馳道加鋪路面,並用鐵椎夯實,使之隆高,以分流水。馳道標志著兩千多年前中國道路工程修築技術的進步。馳道建成後,秦始皇曾多次經馳道巡行郡縣。馳道的修成,對後來的交通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條件。漢朝繼承秦制,馳道仍然是皇帝的專用御道。10裡設亭,每30裡置驿,每驿設置官員掌管。
在秦始皇時代,大致由這樣一些主要交通干線縱橫交錯,結成了全國陸路交通網的大綱:
(1)三川東海道
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為秦東門”(《史記?秦始皇本紀》)。這條道路即從關中向東直達海濱,其與黃河並行的區段,曾被稱做“崤道”、“成皋道”。楚漢戰爭中劉邦和項羽的軍隊曾經在三川東海道反復爭奪。由於該道所聯系的地區經濟比較發達,人口也比較密集,因此成為秦漢時期承載運輸量最大的交通干線。
(2)南陽南郡道
這條道路出武關向東南延伸,經過南陽到達南郡,使關中平原與江漢平原溝通起來。還可以通過水陸交通的形式“南極吳楚”(《漢書?賈山傳》),與長江中下游的衡山、會稽地區相聯系。秦始皇東巡,曾三次經過此道。秦末,劉邦由這條道路先項羽入關。這條大道漢時又稱做“武關道”。
(3)邯鄲廣陽道
這條道路經過河東、上黨,或從河內北上至邯鄲、廣陽、右北平,通達燕趙。這條大道戰國時已經很重要。史念海先生曾經指出:“太行山東邊有一條主要道路,與太行山平行,縱貫南北,趙國都城邯鄲和燕國都城薊都是在這條交通線上。”
(4)隴西北地道
由關中通向西北,為著名的“絲綢之路”的東段。秦統一後,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第一次出巡即由此道西行,後來漢武帝出巡,也曾經經由這條道路。
(5)漢中巴蜀道
秦據有巴蜀,當以跨越秦嶺的暢通道路作為基本條件之一。秦嶺山路險惡,工程極其艱惡。開通之後又歷經拓修完善,形成故道、褒斜道、傥洛道、子午道數條南逾秦嶺的路線。蜀道南段諸線路中,較為艱險者又有著名的陰平道。
(6)北邊道
秦統一後,在戰國長城基礎上營建新的長城防線。因施工與布防的需要,沿長城出現了橫貫東西的交通大道。《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巡北邊,從上郡入”。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出巡途中病故,李斯、趙高秘不發喪,棺載辒辌車中,“從井陉抵九原”而後歸,特意繞行北邊,說明此次出行的既定路線是巡行北邊後回歸鹹陽。後來,漢武帝亦曾巡行北邊。顯然,北邊道自有可適應浩蕩的帝王乘輿車騎隊列通過的規模。
(7)並海道
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始皇統一天下後共出巡5次,其中4次行至海濱,往往並海而行。《史記?封禅書》說,漢武帝曾經從泰山“並海上,北至碣石”。顯然,沿渤海、黃海海濱,當時有一條交通大道。這條大道與三川東海道、邯鄲廣陽道相交,將富庶的齊楚之地與其他地區溝通,用以調集各種物資,具有直接支撐中央專制政權的重要作用。並海道北段在東漢時又被稱為“傍海道”(《三國志?魏書?武帝紀》)。
(8)井陉古驿道
河北省井陉縣城向東10裡,有一條長約100裡,貫穿太行山、建在山嶺溝谷中的古驿道,這條古驿道的歷史可追溯到秦代,曾是古代燕趙通向秦晉的交通要隘,控制晉冀兩省的咽喉所在。秦始皇統一中國後,修築了以鹹陽為中心的驿道,井陉古驿道就是當時的主干線上的重要一段。
沿著山溝中陡峭的石路上行,可以看到路邊有一些石馬、石獸,它們或立或臥,大多殘缺不全。另外還有許多明清時期文官武將的石像。繞過一個山口,一座雄關赫然出現在眼前,門額上是“西通秦晉”四個藍底金字,這就是扼守井陉驿道的關城東天門。關城分為東閣、西閣,踞守在南北兩峰之間,兩閣之間相距不足50米,如同兩把鐵鎖,牢牢地鎖住關隘。
關城的門洞下面有兩道又長又深的車轍痕,深達50厘米,深陷在光滑的基巖路面裡。淡青色的鋪路方石光滑如鏡,路面上每隔20米左右就砌有一道高凸而起、近30厘米厚的石檻,這些石檻是供重車上坡時停歇和沿坡緩慢下滑而設的。可見當年的辎重車通過這段路時有多麼艱難和危險。
由於清末修築正太路線,這條險惡、難行的地段從此少有車馬經過,漸漸被人遺忘。正因為如此,這條千年古驿道才幸免破壞,至今還保留著舊貌。
秦代形成的陸路交通網在漢時又歷經拓修完善,並隨疆土的擴展進一步延伸。由漢中巴蜀道向南,秦代有不能通車的“五尺道”,漢武帝時為加強西南地區的道路建設,“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余裡,以廣巴蜀”,“作者數萬人”(《史記?平准書》)。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南夷始置郵亭”(《史記?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隴西北地道再向西北,一支入青海羌人活動地區,一支經河西向西域,成為溝通中西文化的絲綢之路。北邊道也向東西拓展,秦時北邊“起臨洮,至遼東”(《史記?蒙恬列傳》),西漢時“北邊自敦煌至遼東”已達“萬一千五百余裡”(《漢書?趙充國傳》),遼東以東,又有玄菟、樂浪二郡。東漢時江南道路的建設又有發展,比較著名的有零陵、桂陽交通干線的開通。
秦漢時代,重要的交通干線已通達各主要經濟區,由東向西在彭城、荥陽、長安結成交通樞紐,此外,又有疏密交錯的交通支線結織成網,形成全國規模的交通系統,其中有的支線在歷史演進中又發展為重要的干線。
秦漢陸路交通網的形成,不僅對於當時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而且為後世交通道路的規劃和建設,確定了大致的格局。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實現統一之後,分天下以為36郡,為了鞏固統一,急需加強交通。於是立即致力於全國交通網的建立,在戰國交通的基礎上,“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史記?秦始皇本紀》),經過修整與溝通,將全國道路納入以全國為規模的交通系統之中。
1. 秦直道
《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五年,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六國年表》: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為直道,道九原,通甘泉”。《蒙恬列傳》:“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裡。道未就。”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蒙恬督師修築自雲陽直抵長城腳下九原郡治的道路,全長1800裡,合今約751公裡(漢制每裡折今417.5米,以下同)。修築道路時,逢山開山,遇溝填平,大體南北相直,一般道寬20米以上,是京城鹹陽至北部邊塞九原最接近的道路,故稱“直道”。
直道南起雲陽林光宮(今陝西淳化縣梁武帝村),沿子午嶺北行,經今陝西淳化縣鬼門口、旬邑縣石門關、黃陵縣艾蒿店沮源關、古道嶺、富縣槐樹莊、張家灣西側、甘泉縣橋鎮鄉方家河村、志丹縣安條林場、侯氏鄉等地進入安塞縣境,又沿橫山南麓經今子長縣北境、子洲、米脂、榆林等縣西境,穿過毛烏素沙漠,進入鄂爾多斯高原,過內蒙古自治區烏審旗北,東勝縣西側,在昭君墳東側渡過黃河,達九原郡(郡治九原,今內蒙古包頭市西孟家灣)。這條直道一半修築在山嶺上,一半修築在平原草地上。其中蜿蜒在子午嶺山巅的一段路線,完全沿山脊直行,遇到河川切斷山嶺處,下了嶺坡,旋即上梁,很少在川道中盤桓,敷設別具一格,是名副其實的“山脊線”。
直道為什麼以雲陽為起點呢?因為雲陽距國都鹹陽不遠,其間有往來方便的交通大道。鹹陽至雲陽之間修有馳道,道的兩旁都築起了垣牆,又稱甬道,車輛駛過如同穿行巷中。雲陽縣北有座甘泉山,峰巒起伏,雲高氣爽,風景十分秀麗,是避暑的勝地。山上建有林光宮,秦始皇經常去那裡游幸。戰國時期,甘泉是子午嶺下的一個顯要關隘,起著屏蔽鹹陽的作用,秦始皇常去林光宮,也包含著一定的軍事意義,所以直道也從這裡為起點。
直道的修築主要是從戰略上考慮的。匈奴長期以來活動於陰山南北,早在秦統一六國之前,就經常向南進攻。秦國以及東部的趙、燕諸國經常受到匈奴的侵擾,首當其沖的又是秦國。匈奴控制的地區,南邊可到寧夏固原、陝西榆林一線,即戰國時的秦長城以北的鄂爾多斯草原和六盤山、橫山北麓,距鹹陽最近處僅250公裡。匈奴的輕裝騎兵疾行一晝夜就可到達。秦始皇以前的秦國,一般都對匈奴采取消極防御的戰略,征發民眾修築長城,但長城並沒有也不可能完全保障北方的安寧。秦始皇統一全國後,就派遣蒙恬率領30萬大軍北征,把匈奴驅逐到了陰山以北。秦王朝在新統一的地區建立了34座縣城,從內地遷徙了大批民眾到這些地方定居,並在今包頭市以西設置了九原郡進行統籌管理。在驅逐匈奴的第二年(公元前212年)下令修築直道,以便有效地統治這一片國土。據史料記載,秦直道修通以後,秦始皇的鐵甲騎兵,從林光宮軍事指揮地出發,三天三夜就可以抵達陰山腳下,與長城構成“T”形戰略防御體系,使匈奴“不敢南下而牧馬”。
直道是一條軍事要道,也是發展商業貿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道路。從多年來直道沿途出土的文物來看,有秦漢的貨幣、銅鏡、車馬器、戈矛,北魏以至明清各代的石窟、摩崖石刻、寺廟碑文等,說明直道長期為商旅所行。
直道於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基本建成,總共用了兩年半時間。其工程之浩大,工期之短促,鑿山之艱巨,填溝之困難,實屬中國古代築路史上勞動人民創造的奇跡。
無情的歷史似乎作了一個有意的安排:秦始皇三十七年,他最後一次出游東方,在山東德州患病,七月死於河北巨鹿的趙國故苑沙丘宮。根據中東府令趙高的安排秘不發喪,載屍的辒辌車經井陉而抵達九原,即是從剛剛修好的直道急速返回鹹陽。
直道從林光宮(又名甘泉宮)北行900公裡直抵邊防重鎮九原。秦代經營的交通大道多利用戰國原有道路,只有直道是在秦統一後規劃施工,開拓出可以體現秦帝國行政效率的南北大通道。司馬遷行經直道全程,曾經發感慨說:“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史記?蒙恬列傳》)
清代嘉慶年間文獻記載:“若夫南及臨潼,北通慶陽,車馬絡繹,冠蓋馳驅……”這表明秦直道的荒廢僅是近幾百年的事。從子午嶺上現存的直道遺跡看,直道是一直循著子午嶺主脈修築的。因為鄂爾多斯草原也散布著許多丘陵台地,所以直道經過草原時免不了一番“塹山堙谷”的工程。在現存的遺跡上,路面最寬處約50米,一般也有20米。歷盡兩千多年風雨滄桑,在山區間,有部分路基保存完好,垭口遺跡明顯,古道清晰可辨,驿站石基依然存在。在今內蒙古東勝縣城西南的漫賴鄉,曾發現一段直道遺跡,路面殘寬約22米,路基的斷面暴露極為明顯,用當地的紅色砂巖填築。由此向北和西南,均可以見到山岡上有當時開鑿的四個寬約50米的豁口。這四個豁口連成一線,向人們訴說著2000年來的風風雨雨。
2. 秦馳道
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馳道是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開始修築的。它以國都鹹陽為中心,通向全國各個重要地區,是專供秦始皇出巡時行駛車馬的道路,即御道。馳道的修築,是秦漢交通建設事業中最具時代特色的成就。通過秦始皇和秦二世出行的路線,可以知道馳道當時已經結成全國陸路交通網的基本要絡。
秦修馳道規模宏大,標准較高。據《漢書?賈山傳》所載:秦“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賈山為西漢政論家,他是反對秦王朝政策的,對於馳道侈麗的描述,不免有所誇張。考古工作者曾在陝西鹹陽市東北窯店鎮南側渭河北岸的東龍村以東150米處,發現一條南北向古道路遺跡,路寬50米,築於生土之上,兩側為漢代文化層。這條道路,北為秦都鹹陽的宮殿區,向南正與漢長安城的橫門相對。以秦宮布局“象天極”的規劃意圖分析,這條道路應當是南北溝通鹹陽宮與阿房宮的交通干道,當時自然當歸入馳道交通系統之中。據調查,陝西潼關以東的秦漢馳道遺跡,路面寬達45米以上。
馳道選線盡量追求平直,減緩坡度,擴大曲線半徑,以便於提高通行速度。馳道是區別於普通道路的高速道路。當時馳道是路面分劃為三的具有分隔帶的多車道道路。“中央三丈”是所謂“天子道”。經過特許的貴族官僚可行旁道。馳道就連皇太子也不得擅自通行,直到漢代仍是一條御用道路。《漢書?成帝紀》說漢武帝做太子時“不敢絕馳道”。他當上皇帝之後,特別優待他的****母,“有诏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不過,漢代的馳道已經不僅僅為皇帝所專用了。只要有皇帝或者太後、皇後的诏令,其他王室成員也可以行於馳道之上。這種交通道路規則固然充滿濃重的****色彩,體現出等級尊卑關系,然而在當時針對社會各階層所擁有交通工具質量、數量差別懸殊的現實,其存在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作為最早的具有分隔帶的道路,馳道在交通道路史上也具有值得重視的地位。
雖然馳道是御用道路,在戰爭年代馳道御用的規定就沒有那麼嚴格了。劉邦的部下周勃攻伐反叛的燕王臧荼,就利用了馳道的交通便利而迅速出兵,在易下消滅了敵軍。
馳道由鹹陽向東作扇形展開,東北通至今河北省北部一帶,東至今山東省一帶,東南通至今江蘇、浙江及湖北、湖南、安徽省一帶。
秦始皇完成統一事業第二年(公元前220年),在首次巡游鹹陽以西之後,下令開辟天子巡行天下的馳道。《史記?秦本紀?集解》引應劭注:“馳道,天子道也。道若今之中道。”《資治通鑒?漢紀》武帝太始三年條胡三省注引孔穎達說:“馳道,正道御路也,是天子馳走車馬之處,故曰馳道。”中道(御道)供皇帝使用,兩側旁道供臣民通行。“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記述了馳道的修築規則。中道寬三丈,種上青松,作為界標。“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是記述馳道的修築技術,意思是說,馳道加鋪路面,並用鐵椎夯實,使之隆高,以分流水。馳道標志著兩千多年前中國道路工程修築技術的進步。馳道建成後,秦始皇曾多次經馳道巡行郡縣。馳道的修成,對後來的交通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條件。漢朝繼承秦制,馳道仍然是皇帝的專用御道。10裡設亭,每30裡置驿,每驿設置官員掌管。
在秦始皇時代,大致由這樣一些主要交通干線縱橫交錯,結成了全國陸路交通網的大綱:
(1)三川東海道
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為秦東門”(《史記?秦始皇本紀》)。這條道路即從關中向東直達海濱,其與黃河並行的區段,曾被稱做“崤道”、“成皋道”。楚漢戰爭中劉邦和項羽的軍隊曾經在三川東海道反復爭奪。由於該道所聯系的地區經濟比較發達,人口也比較密集,因此成為秦漢時期承載運輸量最大的交通干線。
(2)南陽南郡道
這條道路出武關向東南延伸,經過南陽到達南郡,使關中平原與江漢平原溝通起來。還可以通過水陸交通的形式“南極吳楚”(《漢書?賈山傳》),與長江中下游的衡山、會稽地區相聯系。秦始皇東巡,曾三次經過此道。秦末,劉邦由這條道路先項羽入關。這條大道漢時又稱做“武關道”。
(3)邯鄲廣陽道
這條道路經過河東、上黨,或從河內北上至邯鄲、廣陽、右北平,通達燕趙。這條大道戰國時已經很重要。史念海先生曾經指出:“太行山東邊有一條主要道路,與太行山平行,縱貫南北,趙國都城邯鄲和燕國都城薊都是在這條交通線上。”
(4)隴西北地道
由關中通向西北,為著名的“絲綢之路”的東段。秦統一後,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第一次出巡即由此道西行,後來漢武帝出巡,也曾經經由這條道路。
(5)漢中巴蜀道
秦據有巴蜀,當以跨越秦嶺的暢通道路作為基本條件之一。秦嶺山路險惡,工程極其艱惡。開通之後又歷經拓修完善,形成故道、褒斜道、傥洛道、子午道數條南逾秦嶺的路線。蜀道南段諸線路中,較為艱險者又有著名的陰平道。
(6)北邊道
秦統一後,在戰國長城基礎上營建新的長城防線。因施工與布防的需要,沿長城出現了橫貫東西的交通大道。《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巡北邊,從上郡入”。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出巡途中病故,李斯、趙高秘不發喪,棺載辒辌車中,“從井陉抵九原”而後歸,特意繞行北邊,說明此次出行的既定路線是巡行北邊後回歸鹹陽。後來,漢武帝亦曾巡行北邊。顯然,北邊道自有可適應浩蕩的帝王乘輿車騎隊列通過的規模。
(7)並海道
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始皇統一天下後共出巡5次,其中4次行至海濱,往往並海而行。《史記?封禅書》說,漢武帝曾經從泰山“並海上,北至碣石”。顯然,沿渤海、黃海海濱,當時有一條交通大道。這條大道與三川東海道、邯鄲廣陽道相交,將富庶的齊楚之地與其他地區溝通,用以調集各種物資,具有直接支撐中央專制政權的重要作用。並海道北段在東漢時又被稱為“傍海道”(《三國志?魏書?武帝紀》)。
(8)井陉古驿道
河北省井陉縣城向東10裡,有一條長約100裡,貫穿太行山、建在山嶺溝谷中的古驿道,這條古驿道的歷史可追溯到秦代,曾是古代燕趙通向秦晉的交通要隘,控制晉冀兩省的咽喉所在。秦始皇統一中國後,修築了以鹹陽為中心的驿道,井陉古驿道就是當時的主干線上的重要一段。
沿著山溝中陡峭的石路上行,可以看到路邊有一些石馬、石獸,它們或立或臥,大多殘缺不全。另外還有許多明清時期文官武將的石像。繞過一個山口,一座雄關赫然出現在眼前,門額上是“西通秦晉”四個藍底金字,這就是扼守井陉驿道的關城東天門。關城分為東閣、西閣,踞守在南北兩峰之間,兩閣之間相距不足50米,如同兩把鐵鎖,牢牢地鎖住關隘。
關城的門洞下面有兩道又長又深的車轍痕,深達50厘米,深陷在光滑的基巖路面裡。淡青色的鋪路方石光滑如鏡,路面上每隔20米左右就砌有一道高凸而起、近30厘米厚的石檻,這些石檻是供重車上坡時停歇和沿坡緩慢下滑而設的。可見當年的辎重車通過這段路時有多麼艱難和危險。
由於清末修築正太路線,這條險惡、難行的地段從此少有車馬經過,漸漸被人遺忘。正因為如此,這條千年古驿道才幸免破壞,至今還保留著舊貌。
秦代形成的陸路交通網在漢時又歷經拓修完善,並隨疆土的擴展進一步延伸。由漢中巴蜀道向南,秦代有不能通車的“五尺道”,漢武帝時為加強西南地區的道路建設,“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余裡,以廣巴蜀”,“作者數萬人”(《史記?平准書》)。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南夷始置郵亭”(《史記?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隴西北地道再向西北,一支入青海羌人活動地區,一支經河西向西域,成為溝通中西文化的絲綢之路。北邊道也向東西拓展,秦時北邊“起臨洮,至遼東”(《史記?蒙恬列傳》),西漢時“北邊自敦煌至遼東”已達“萬一千五百余裡”(《漢書?趙充國傳》),遼東以東,又有玄菟、樂浪二郡。東漢時江南道路的建設又有發展,比較著名的有零陵、桂陽交通干線的開通。
秦漢時代,重要的交通干線已通達各主要經濟區,由東向西在彭城、荥陽、長安結成交通樞紐,此外,又有疏密交錯的交通支線結織成網,形成全國規模的交通系統,其中有的支線在歷史演進中又發展為重要的干線。
秦漢陸路交通網的形成,不僅對於當時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而且為後世交通道路的規劃和建設,確定了大致的格局。
- 上一頁:車塵馬跡尋古道(五)西南蜀布之路
- 下一頁:車塵馬跡尋古道(三)秦蜀棧道
熱門文章
熱門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