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鵬古城:大陸與海洋的對峙印記
日期:2016/12/14 0:05:18 編輯:古建築紀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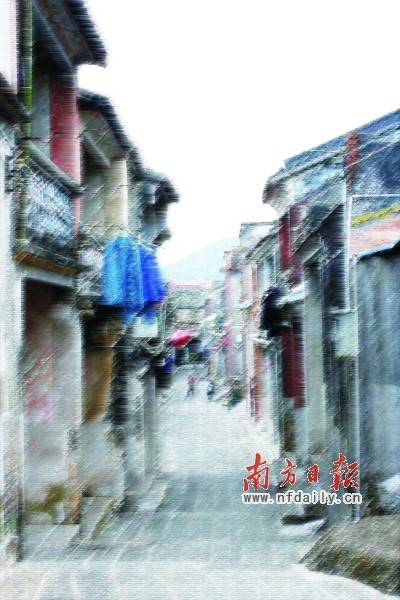
長年綠色氤氲的嶺南,人傑地靈,有著源遠流長的歷史文化。曾經,數百個姓氏的家族自北方遷徙到嶺南的山腳下,又從南嶺的珠玑巷遷徙到廣袤的珠江三角洲;曾經,1300年前的某個深夜,六祖慧能遵照祖師的囑咐,一路向南,直至抵達四會的新興,弘揚佛法;曾經,廣府人洪秀全、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在珠江三角洲出現,讓當時的朝廷痛恨不已;曾經,一場場亘古未有的革命產生於這個“南蠻之地”,令世人刮目相看……如今,嶺南已經迎來了新的世紀——在高樓大廈林立、物質富足的今天,懷想一下悠遠的、那曾經如此荒涼的嶺南大地的過去,或許有著一種特殊的意義。本報特別開辟一個專欄“田野上的史記”,刊登著名作家、廣東文學院院長熊育群寫的一組關於嶺南歷史文化獨特觀點的系列散文,或者能讓讀者在閱讀過程中體會到一種歷史的縱深感在眼前展開……
●熊育群
朱元璋把貿易視作洪水猛獸,而今天正是這猛獸一樣的貿易帶來了洪水般的財富。一個商業的社會,一個以市場經濟為標記的年代,把大鵬所城之地作為特區,只用30年的時間就建成了一座影響世界的大都市。它沿用這座600年古城的名字,稱作鵬城,想要嫁接歷史。
千戶是明朝的官銜,屬於軍隊中一個領導1000人馬的低級軍官。600多年前,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千戶,沒被時間抹去,藏在一個狹小范圍的文字裡,與今天的人相遇。這也算得上一個奇跡。
盡管我望向時間深處的目光恍惚得虛無,但這個人是真實的。他名叫張斌。他勞動的成果、他生活的場景仍在眼前呈現著,一眼望去,600年前的一樁事情仿佛剛剛過去,轉身的背影在某個清早的晨霧裡淡去,腳步的寂靜、喊聲的空洞、大地上無形的疲倦……都在一座舊城裡隱匿。
張斌干的事情就是領著一隊人馬建起一座城池。誰也想不到,這座城池保存到了今天。
相遇舊城,我開始了對張斌的尋覓。各種紙面記載,網絡虛擬世界裡的信息海洋,關於他的消息卻只是干巴巴的幾句。
然而,通過張斌,一項令人意想不到的事件浮現出來了——當發現這一秘密時,我不能不震驚!血在某一瞬間凝固——在南方,一個數萬人甚至幾十萬人參與的偉大工程,同時在1000裡的荒無人煙的海岸線上展開!南蠻絕地,卻輕易地將這一壯舉遺忘了!
明朝洪武二十七年,也許是八月的一天,火辣辣的陽光,照得天地亮晃晃,酷熱難當。張斌就是這樣的時刻帶著一隊人馬,從南頭烏石渡啟程去大鵬嶺。沿路古木參天,那些瘋長的榕樹、芭蕉、木棉,阻擋著去路。威猛的食肉動物吼聲從遠遠的山坡傳來,而沉默的動物如蟒蛇則只在密集的樹木後,死死盯著你。
張斌在某一個高地望見了大海,他也許並不在意。想象一下他的面龐、表情,甚至他的身高,對一個幾百年前的人也許並無意義。物質世界,生生滅滅,忽為人形,忽作塵埃,生命如大地之夢。只有面前的海岸線是恆定的綿長。只有前去做的這樁事情,穿越了時空,呈現了某種永恆的品質。
那時,一個新政權剛推翻了一個舊政權,廣東是南方最後歸降的地區。然而,海上並不安寧。南海奸宄出沒,那些被追捕的海上疍戶,附居海島,遇到官軍追捕,則詭稱是捕魚的,遇到倭賊就加入他們的行列,像台風一樣向著陸地的某個地方襲擊。倭寇到這個地區已經有14年了。那些南北朝混戰中失敗的日本武士,糾結土豪、奸商、流氓、海盜,來中國海岸走私、燒殺劫掠。這片荒涼絕地就是這些倭寇的藏身之所。
張斌望向大海的目光並不因遼闊而生舒坦,在腳下翻騰的波浪裡,有一絲驚疑陰翳般閃過。他走在南中國的海岸線上,他正要做的就是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一項春秋大業——也許連朱皇帝自己也沒想到,從這時開始,他在實施一項前無古人的圍困自己的計劃——修建長城,而這長城首先是從海上開始的。張斌與數以萬計的軍士和百姓加入到了這海上長城的修築。
廣東境內沿著曲折的海岸,朱元璋設置了廣州衛、潮州衛、南海衛、碣石衛等9衛29所。在張斌上路的同時,這條還算平直的海岸線上,許多個他這樣級別的武官也在上路,民工們浩浩蕩蕩向著海邊聚集,他們的任務就是修建海濱城堡與煙墩——平海所城、東莞所城、青藍所城、惠州所城、雙魚所城、海豐所城、寧川所城、甲子門所城、捷徑所城、河源所城、南山所城、大鵬所城——它們都在1394年同時動工。張斌領命修築的是大鵬所城。
赤貧出身的皇帝,夢想著“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簡樸農業社會。他甚至想廢除貨幣和商品交易:明朝每戶人家要承擔實物稅和徭役,這徭役很可能就是從千裡之外押運征收的幾百塊城磚或幾千張紙,從水路或是陸路運抵南京。建南京城牆時,每一塊城磚都是從全國各地燒制好後運來的。輪到這一任務的家庭,只能與當年的朱元璋一樣陷入赤貧。軍隊也是這樣,實行衛所制,官兵在駐地自耕自食,亦農亦兵。
一到大鵬半島,張斌就忙著勘察地形,最初選址在大鵬半島最南端的南澳鎮西湧海邊。於是,一隊隊兵丁開始在這裡安營扎寨,被動員來的百姓也紛紛伐木搭棚。難見人煙的半島上,升起了滾滾濃煙,那些磚瓦窯前,紅泥滿地,堆滿了山上砍來的樹枝,紅色粘土做的磚瓦一排排如列隊的軍士,熊熊火焰從一條條窄長的門洞透出桔紅色光芒,映亮了官兵百姓們黧黑的臉龐。
三個月,城牆開始從大地上站立起來。這時,寇盜騷動起來了,像海潮一樣襲來,官兵們不得不停下砌刀,拿起刀槍,投入一場場圍剿的血戰。
窯火再度升起來時,一切又都重來。張斌也許犯了一個選址不當的錯誤,城堡不得不在另一個地方重建。當一座占地11萬平方米的城池在大鵬山麓建起來時,它的規模是那樣宏偉:平面呈方形布局,城牆由麻石和青磚砌成,牆基寬5米、牆寬2米、高6米,城牆總長約1200米,城牆上有雉堞654個,並辟有馬道,有東、西、南、北四個城門,每個城門上有一座敵樓,兩邊設四個警鋪。城外東南西三面環繞著一條深3米、寬5米的護城河。而城內建起了南門街、東門街和正街三條主要街道。
一座軍事化的城堡出現了街道,這是不尋常的。城牆是一種戰爭行為,街道卻是生活的場地,兩者奇妙的結合,在空間上呈現了明朝一種特殊的軍隊制度——衛所制。
“衛”、“所”是基層軍事單位,軍隊軍官世襲,稱“世官”。軍士也世襲。他們兵農合一,既當兵又種田。軍士和家屬有特殊的社會身份,有專門的軍籍,由五軍都督府直接管理。
剛剛建立的明朝,改朝換代的戰爭打得國家千瘡百孔,朱元璋無力籌措龐大軍隊的糧饷,於是,邊軍三分守城,七分屯田,國家供給土地、耕牛、種子、農具。軍糧、官兵俸祿就靠田裡的收入了。城堡既是軍事堡壘,也是一座生活之城。正是這樣,有的衛所如威海衛、天津衛、海參衛,後來慢慢衍變成了一座座生活的城市。
大鵬所城四周地勢險要,臨海處又設置了11處煙墩。這些煙墩就是北方長城的烽火台,圓台形磚土結構,台底直徑10米,上部有一直徑2米多的圓坑,西北向一米的缺口作為風門。發現敵情,白天以煙傳訊,夜晚以火光報警。大坑煙墩至今保存完好,它南臨大亞灣海濱,東北為大亞灣核電站。墩台築於高約百米的山崗上,可觀察整個龍岐澳。
城堡、煙墩沿嶺南海岸線一路北上,直到北方的靈山衛、威海衛、天津衛、海參衛……海上“長城”就這樣一座連一座建成了。
海上似乎可以太平了。
張斌踏著明朝的時間而來,做著看家護院的差事。舊的陽光,在600年前的歲月裡照耀著,這陽光是屬於南蠻絕地的陽光,與寂寞與殺戮一樣,也屬於張斌。在這海邊只聞濤聲的寂寞時光裡,張斌做夢也想不到,有朝一日,這樣的邊地也可以繁華如京都,那曲折起伏的小道會變成高速公路,箭一樣穿透這一空間。現在,張斌的屍骨,早已化作了塵泥。而他所建的城池,來到了現在的世界,他因此又走進了人群的生活與記憶。
建在深圳龍崗區的大鵬所城被保護起來了。來這裡參觀的人越來越多。紅男綠女,開著寶馬、凌志、雅閣,輕輕一踩油門就到了。
朱元璋把貿易視作洪水猛獸,而今天正是這猛獸一樣的貿易帶來了洪水般的財富。一個商業的社會,一個以市場經濟為標記的年代,把大鵬所城之地作為特區,只用30年的時間就建成了一座影響世界的大都市。它沿用這座600年古城的名字,稱作鵬城,想要嫁接歷史。
取名者也許沒想到他具有反諷的天才,同一個名字兩座城池,一個是明朝為閉關鎖國而建的,一座卻是為打開國門、為開放而建的。面對南海,朱元璋以片甲不得下海的禁令,讓波濤翻騰不息的大海洋變成一片死海。而深圳,卻讓這片大海運載來了滾滾財富。600年後,中國人真正看到了大海!
這期間,鄭和七下西洋,他的船隊就從這座古城不遠的海面駛過並停泊過,他看到了海洋的遼闊、偉大,但沿岸一座座兵營城堡,這些農民的子弟,把刀槍指向海洋,就已經注定了他船隊的短命。
大海又沉寂了100多年,從地球另一面的大海洋駛來了一支葡萄牙人的船隊,他們在屯門試探性登陸時,遭到了中國軍隊的打擊。大鵬所城的軍士參加了第一次對西方人的戰斗。葡萄牙人於是改變策略,他們在澳門半島悄悄登陸,借口貢物打濕需要上岸翻曬,租借海島一用。
南蠻絕地,誰也不在意之中,一座魔術一般繁華的城市澳門建起來了。
大鵬所城的軍士們仍然住在自己的城堡裡面,白天外出種地,夜裡持刀槍巡邏。當然,遠在天邊的船只還是有的,那些裝著絲綢、瓷器的商船,偶爾駛過,白帆一點,羽毛一片,於浪尖風口上行走。許多時候,這些飄揚的風帆是由官方控制的貿易。作為國策,海洋是被封鎖的。一條海上絲綢之路,在大陸目光難以企及的大海中,白帆一閃就被波浪抹去了航行的蹤跡。
又是200多年過去,與大鵬所城相距只有幾十裡的尖沙咀,英國人的艦隊出現了。這一次,來者不善,海上的戰爭無可避免,東西方第一次海戰在此打響。
帶頭反擊入侵的一位將軍賴恩爵,是大鵬所城人,軍人的後代。賴氏滿門英雄,三代出了五位將軍。九龍海戰,惡戰五個小時,他竟然靠智慧打退了英國的洋船洋炮,逼使入侵者狼狽逃竄。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賴氏後人燃放炮竹時,喜極而泣,跪在祖堂前,喃喃告慰先人:南京條約已洗雪了,今天這一個日子終於可以還報祖願了。
大鵬所城歷經了如此之多的世界性大事,它仍然在大地上矗立。
古城人經歷了如此多的朝代更替,而守土有責的精神也留在了城堡之中,像古榕樹一般根深葉茂,逾600年而不易。這是人類精神的一個奇跡!
張斌搬動過的青磚與麻石在這裡沉默了6個世紀。張斌站在6米高的城牆上張眼望向大海,這個令人興奮的高度還在,只是他的目光沒有了,換上了我的目光。我感覺到我在重復他眺望的動作,就像我代替他活在這個世上。他那個時候這麼年輕,血氣方剛,皮膚下藍色血管暴凸,血液喧騰,勞動起來,健步如飛。他不會想自己也會成為先人。誰年輕的時候也不會想祖先與自己有什麼關系。張斌仿佛一瞬之間就成為了遙遠的祖先。歷史長河裡,600年也僅是瞬息即逝。
我爬上北面的一座山頭,遠遠地打量著古城,南風習習,大地蔥茏,時間又回到了從前。城牆山下矗立,我看到一個封閉的空間,對外,它用大門打開自己,與東南西北荒野連通並以自己的氣勢制約著周邊的連綿山嶺、浩蕩海洋;對內,它的城牆之後是街牆,街牆之後是院牆,院牆之後是門牆,密密麻麻,一步一步走向私密的空間,甚至沒有窗戶,它們都開向了院內。沒有人面桃花的驚喜,甚至也沒有紅杏出牆的绯聞,一切生活的秩序都由建築規范著,井然之中顯現的是宗法的肅然,無人敢於挑戰。人面對曠野而起的野心,在這個局促的小小空間裡消逝殆盡。每個人看到的只是自己的生活,集體的困頓、枯燥轉變成個人的處境。懷念、夢想、欲望和不甘也在這小小空間裡轉寰。城堡與居所,猶如大國與寡民,是一種空間生態也是一種政治生態。
白天,一道一道大門在吱呀聲中打開,一個個軍士走出家門,進入公共的空間,成為一支隊伍,成為城堡裡面生發出來的氣與勢。晚上,一道一道大門又在吱呀聲中關閉,一隊隊巡邏的軍士分散開來,走到了一扇扇門後,進入他們私密的空間。這空間裡有愛情、親情、性,有柴米油鹽,有苦樂年華。
門的啟合有著自己時間的節律。時間在古城是能夠傾聽的,它是城堡向山河海洋發出的聲音——鐘與鼓。鼓如果是私人的時間,它在城樓之上,那麼鐘就是公共的時間,它在寺廟裡面。皇帝當過小沙彌,他自然熱衷於建寺院,城堡也不能例外。城堡裡缭繞的香火常常與南方的霧混在了一起。大鵬所城現在還保存了侯王廟、天後宮、趙公祠。從寺廟裡傳出來的鐘聲總是陽光一樣悅耳,新一天的開始是充滿銳氣的,是沉厚的、公共的。鮮紅如血的霞光正在東方噴薄。鐘聲嘹亮、振蕩,充滿朝露一樣的清新、喜悅,也充滿了人間煙火味。
而城樓上,當那輪由白轉紅的太陽欲向茫茫大海沉落,總有一雙有力的手臂攥緊了桃木的鼓槌,一下一下掄起,鼓點就在這一起一落間響起,像撕裂了沉默,又像繃緊的心弦在剎那間放下,在鼓聲掀動的空氣裡,那黑壓壓密麻麻的瓦屋頂掠過一片灰色的暗影,那是天地進入沉寂的前奏。而當更鼓一次次響起,人們知道那是在為他們打開一個又一個夢的通道。夜的安谧、恬靜全在那不急不緩的鼓點裡,塵土一樣沉沉落下,恍如時間的遲滯。
大鵬所城卻是寂寞的,位於半島邊地,經常的訪客只有風。最激越的時候就是從海上惡魔一樣飄來的戰爭。大海上來的風,既有溫柔輕快的,又有狂暴猛烈的。鹹腥的氣息總帶來海的體味,某個清晨或者黃昏刺人鼻息,某個時刻又讓人與不祥相聯。海在中國人的集體記憶裡總是充滿了恐懼。它與西部大漠一樣,是大陸中央的人想極力遺忘的部分。小農經濟,農耕文明,養成了中國人強烈的家園意識,對大海、大漠波動不安、飄忽不定的環境,是那麼陌生與抗拒。
高聳的城堡,代表的就是大陸與海洋的一種對峙。
城牆內外的榕樹、木棉、楊柳……它們或高高升向天空,或左右橫生,四季裡都在綠著、生長著。軍士們的命運與樹木也是一樣的。在猖獗的倭寇面前,城牆就是他們與大地相連的根,只有伸展出又長又高的牆壁,才不會被海上來的盜寇當作樹木一樣拔掉。
大鵬所城終究沒有被海盜倭寇所滅,也沒有被時間抹去。嶺南沿海的城堡在歲月中一座一座敗去時,大鵬所城依然不敗。它不敗的原因不是城牆而是精神,這是時間開放出的花束,是穿越朝代的永續之力。
明朝軍士世襲制,已經內化成古城人的一種精神,世襲制猶如滾動的車輪,別人無法進入,自己也難以出來,恰如血脈、傳統,當兵成了天職,代代相傳,跨越了朝代,直至今天。
另一座留存下來的城堡平海所城,離它兩百裡,它悄悄融入了四方客商,成為一座商城。它因商而留存,就如山東煙台市,以前不過是一座烽火台。這些是一座城市生存最隱秘的血液。
四月,暴雨說來就來,連天雨水傾盆而下,水的響聲盈溢天地,這是來自南海的雨水。
春天,總是在這樣的雨水中上路,心事浩茫,汪洋一片都不見,知向誰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