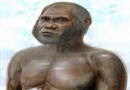拆完了建築 我們還剩下什麼
日期:2016/12/13 22:26:31 編輯:古建築紀錄黑格爾曾經說過,“建築是凝固的音符”。而我們生活的城市,則正是由這些音符所組合而成的美妙的樂曲。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舊的建築就如同舊的音樂一般,都需要接受時代的沖擊。就如同這個年代流行的是流行樂而不是交響曲,這個時代的代表建築是高樓大廈,而不是院落民居。
但與音樂不同的是,你可以創作無數的新音樂而不影響舊音樂的存在,因為舊音樂並不占用什麼資源。舊音樂也不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出現諸如老化之類的問題。而建築會受到風雨的侵蝕,人為的破壞,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逐漸老去。更大的問題是,舊建築占用著一項寶貴的資源:土地。也許在寸土寸金的市中心,赫然出現在你眼前的不是高聳的大樓,不是繁華的商業廣場,而是一片年齡比你爺爺的爺爺還要大上幾十上百歲的老建築群。這,在開發商的眼裡絕對是種資源浪費。於是,在這個GDP至上的時代,對這些老建築拆還是留,成了擺在政府面前的一道難題。
古城的名與實
有時候,我很難理解一些政府的行為。比如有的城市地方政府一邊希望獲得“歷史名城”“千年古城”之類的美名,一邊卻在大肆的拆毀那些古建築,破壞古建築這一城市歷史的載體,毀壞古城之實。
2011年7月前後,國家文物局的專家到寧波做“歷史文化名城”回訪時,看到月湖西區成為一片廢墟後,一位文物局官員當場丟下狠話:寧波這樣拆下去,“歷史文化名城”的牌子遲早摘掉。這不是一句危言聳聽,而是我們當前面臨的嚴峻問題:我們的祖先為我們造了一座城,我們卻一手抹去了它曾經存在過的痕跡。面對著鱗次栉比的高樓大廈,我們也許會贊歎這個城市的繁華與現代化,但絕不會想到這是座擁有千年歷史的城市。或者說,那座古城早已被後來建造的新城掩埋在了黃沙之下。
拆舊城造新城的事,並不是最近才發生,也不是只有地方才有,就連我們引以為傲的首都北京也面臨著“破舊立新”的尴尬。袁騰飛曾說過,北京沒有一點古都的樣子,都是近三十年來新造的。你可以說故宮是古跡,但不能說北京是古城。關於這個問題,著名的建築學家梁思成也早就提過,並深感惋惜。京津戰役都沒能毀掉的老北京,在解放後卻幾乎被拆了個干淨,空留古都之名,卻早已沒有了古都的樣子。
也許梁思成沒有想到的是,他非但沒能保住老北京,就連他和林徽因的故居,居然在幾十年後也被“維修性拆除”了。
失落的城市記憶
前幾日筆者去探訪了下月湖西區,月湖盛園,郡廟街區等寧波老街區。當看到月湖西區只剩幾座孤單的破舊房子矗立在一片廢墟中時,還是一陣酸楚。
筆者三歲時搬到月湖邊上的縣學街,月湖西區,月湖盛園,郡廟街區都是在筆者家的周圍。可以說,這些舊街區都承載了筆者的回憶。
小時候在天封塔邊上大沙泥街和大來街之間的那片小巷內的某個幼兒園念書。雖然筆者已經記不起那個幼兒園的名字,但依然會記得母親騎著自行車帶著幼小的筆者在狹窄的小巷中穿梭的情景。而如今,記憶中的小巷早已變成了富茂廣場。月湖西區則是筆者小時候經常經過玩耍的地方,邊上的月湖公園裡的某塊草坪是筆者初中時和同學踢足球的固定場地。前幾日去探訪時,還指著那條路對同行的朋友說:我以前每天上學都經過這兒。可惜如今,月湖西區早已成了一片廢墟,只有幾幢掛著文保建築牌子的老屋子孤零零的立在那兒。而那些得以幸存的文保建築,也破損嚴重,不難看出後期被改造過的痕跡。至於月湖盛園,剛開園的時候還帶著一絲興奮去看,看完後卻大失所望。曾經幽靜的冷靜街變成了商業區,拓寬的巷道失去了小巷的古樸與滄桑感。在原本應是庭院深深的院落裡甚至開出了KTV和夜店,而始建於唐朝的靈應廟則成一家商業味濃重,向著私家會所發展的書吧,從前的郁家巷早已不復存在。
筆者的失落,是童年的記憶載體突然消失,也許以後都無法再帶著友人指著那些小巷街道和建築告訴他們筆者的童年故事。也許,筆者個人的記憶載體不算什麼的,但如果那是一個城市的記憶載體,那就非同小可了。不知道提起月湖盛園,還有多少人會知道那裡有近代寧波第一買辦楊坊故居、建於唐朝重修於民國的靈應廟、中國麻將發明者陳魚門故居、區級文保單位盛氏花廳、浙東學派李氏宗祠,甬籍旅滬商人李坎虞房、紡織廠老板董梅生宅、民國時期郵電局局長陳炳恆宅等體現了這個城市歷史的老建築,而不是只知道那裡有什麼餐館,有什麼酒吧,有什麼KTV…
建築是一個城市文化的載體,是城市歷史的直接體現和證據,是我們的祖宗留給我們的實體和文化財富。我們能去羅馬古城區體驗古羅馬的強盛,能去佛羅倫薩的老城體會文藝復興時的文化繁榮。那是否在很多年以後,我們只能對著泛黃的照片哀歎那已不存在的老寧波和逝去的歲月。
我們都希望,那一天永遠不會到來。
- 上一頁:今天,為什麼要保護城市遺產?
- 下一頁:國內多個地震遺址申報國家A級景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