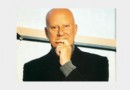古建工程中的項目管理思想
日期:2016/12/15 2:01:37 編輯:古建築結構我國古代工程建設中所體現出來的早期項目管理思想,是我國幾千年來建築實踐活動中所形成的優良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
文/何成旗
系統思想
古代早已存在系統認識。公元前四世紀古希臘哲人亞裡士多德已天才地認識到“整體大於它的各部分的總和”。系統方法著眼於整體,照顧全局,相互協調,注重定量的分析和統計,在項目管理中向來作為重要工具被廣泛應用。我國古代工程建設中已經懂得並成功實踐了系統的思想。公元前三世紀戰國時代蜀郡守李冰父子主持設計修建的四川都江堰水利工程和古代建築奇跡之一的萬裡長城就是兩個突出的范例.
都江堰的整體思想。都江堰水利樞紐工程由分水導流工程、溢流排沙工程和引水口工程組成.。分水導流工程為利用江心洲建成的分水魚嘴、百丈堤和金剛堤,它們把岷江分為內外兩江。內江一側建有由平水槽、飛沙堰以及具有護岸溢流功能的人字堤等組成的溢流排沙工程.內江水流由上述導流和溢洪排沙工程控制並經寶瓶口流向川西平原,汛期內江水挾沙從飛沙堰頂溢入外江,保證灌區不成災。寶瓶口是控制內江流量的
引水通道,由飛沙堰作為內江分洪減沙入外江的設施,外江又設有江安堰、石牛堰和黑石堰三大引水口。整個工程的規劃、設計和施工都十分合理,通過魚嘴分水、寶瓶口引水、飛沙堰溢洪,形成—個完整的功效宏大的“引水以灌田,分洪以減災”的分洪灌溉系統。
萬裡長城的系統思路。萬裡長城的總長度達6700多公裡,如此浩大工程,離不開系統思路。在設計和規劃的整體性上,古代把匈奴等游牧民族的騷擾當作環境因素,從中華民族疆土的整體性出發而設計和建構出這樣一個龐大的整體性防御體系。在結構上,雖綿延六千多公裡,地勢又復雜多變,仍“五裡—燧,十裡—墩,卅裡一堡,百裡一城”,井然有序,在結構規劃上體現了嚴密的有機性;在施工方法上,整個長城借助
於地形特點,就地取材,防鹼夾層設計,使施工方便,且牆身堅固,體現了施工過程的優化思路;在整體效能上,每隔一段距離設置一個烽火台,形成快捷的信息傳遞聯系體系,成為整個防御體系的神經系統。萬裡長城從設計規劃、修築施工到使用過程都生動地體現了系統的思路。
如上所述,我國古代重大工程的施工管理已經注意到把工如上所述,我國古代重大工程的施工管理已經注意到把工程項目當作一個整體系統來對待,一方面注重系統整體中各個部分的相互聯系和制約,另一方面又忽略從環境的角度來觀察、分析以至規劃、協調和控制系統的變化,力求達到最好地處理—切問題。這種認識和處理事物的思路與方法,正是今天項目管理的基本特點。
“最優化學”是當今世界一門新興學科,它研究怎樣從所有可能的方案中選擇最合理的一種,以達到目標最優.
我國古代雖然還不懂得“最優化學”這個概念,卻在工程項目管理實踐中時時、處處體現出優化的思想。宋代水工高超在黃河治堤工程中首創的“三節下埽合龍法”即是一例.
黃河治堤。北宋慶歷八年(公元1048年)六月,黃河在澶州(今河南濮陽)決口,大約折合今天850米左右。以當時的技術條件,堵口工程非常艱巨,特別是最後的“合龍”是堵口工程成敗的關鍵。當時合龍用“埽”,即用秸桿、土、石等卷成大圓捆,直徑從1米到4米不等,長度約100米。由於龍門水深流急,幾次合龍都未成功。水工高超認為,失敗的原因是埽身大長,不易壓到底,不但起不到斷流作用,反而把繩索拉
斷了。於是提出把60步(約100米)埽分為3節,每節20步,彼此用繩索連起來,先下第一節,壓到底再下第二節,然後再下第三節。有人不相信這個方案,高超說:“第一節20步埽下去後,水雖未斷,但水勢已削弱一半,壓第二節埽就省力多了,下第三節埽時,由於已有了前兩節,就基本上等於平地施工了。第三節埽處理好之後,前兩節埽自然被濁泥淤塞,用不著多費人力了。”按高超優化後的方案去做,終於巧合龍門,勝
利地堵住了決口。北宋科學家沈括的《夢溪筆談》記錄了這個生動的故事。
都江堰工程。我國古代工程建設中優化設計和施工的思路主要體現在先進適用的科學技術的運用上。例如馳名中外的趙州橋,淨跨達37米多的主拱圈拱頂同橋面的填土只有極薄的—層,經用現代力學原理對其進行計算和驗核,發現由於4個小拱和采用拱頂薄面造成拱圈拱軸線與恆載壓力線貼近的效果,這正是使趙州橋千年不圮的主要原因。據考證和分析,這樣高明而精心的設計運用了當時數學家劉焯的“內插二項式”。
這項工程的主持者李春還創造性地采用縱向並列砌置的辦法施工全橋的28道拱圈,每—道拱圈都能獨立存在,施工時可以一道道地砌,使橋逐漸地加寬,還可以節省拱型木架,同一拱架可以重復多次使用,拱圈如有損壞,可以局部補修,不致影響整個橋身的安全.
現代意義的統籌思想是根據項目的要求,通過數學分析和運算作出綜合性合理安排,以達到經濟、有效地使用人力、物力。這也正是項目管理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之一。而我國早在幾百年前就已出色地運用統籌思想與方法解決工程實踐中的難題了。
通惠河修浚。公元十三世紀的元代科學家郭守敬修浚京城附近的通惠河時,有二萬以上的軍、匠、水手與囚徒參加施工。為了加快工程進度,郭守敬反復勘察地勢和水源,精心設計河道走向和施工程序。他先在京城大都西北修建—條長達30公裡的白浮堰,把昌平以南神山白浮泉水西引,再利用天然地勢使其折而南流,與西山山麓大體平行,並沿途截匯西山諸泉水,注入甕山泊(即今頤和園昆明湖),再入大都城,這樣既充分利用了地形環境,減輕了勞動強度,又解決了自古以來始終未能解決的水源問題,整個工程僅1年多時間便告完成。據歷史記載,當時積水潭上“舢舻蔽水”,可見這條運河效用之大。
北運河改造。清代康熙年間著名治黃專家陳璜改造北運河時,有計劃地利用修築北岸“遙堤”開挖土方,形成一條施工過程中可以利用的運料小河,然後在此基礎上挖深開寬,“所費不多”,修成了上接北運河、下迄清口對岸的“中河”。行駛在運河的船舶,出清口以後,直接橫波黃河而進入中河,也就是北運河了。這就避開了行駛黃河中的“風波之險”和“牽挽之勞”,漕運暢通,商旅無阻。
一舉而三役濟。更令人拍案叫絕的是北宋科學家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記載的“一舉而三役濟”的事例:北宋祥符年間(公元1008~1016年)大臣丁渭受命修復皇宮,遇到三個主要矛盾:一是取土太遠,二是運進建築材料困難,三是建築垃圾難以處理。丁渭深入現場踏勘,進行方案對比,把通向汴水河的道路挖成溝渠,與汴水河連通,既就近取了土,又形成運輸建築材料的水道,工程完工後將灰土、瓦礫等建築垃圾傾入這條溝渠,填平,復成道路,就這樣,三個難題都巧妙地解決了。“一舉而三役濟”“省費以億萬計”。僅此一端,可見我國古代工程項目管理達到的水平。
“規矩先定”
計劃組織施工。十九世紀初期以前,建築師就是總營造師,負責設計工程、購買材料、雇用工匠,並組織工程的施工。建築師所面臨的是較為簡單的施工工藝和種類很少的建築材料,因此,對於進度計劃、成本核算等—般不大重視。然而,我國古代卻不盡然,許多著名的建築師對於工程的計劃和施工組織都給予了足夠的重視。據《左傳》記載,春秋時代楚國築城工程在令尹孫叔教領導下,按照周密的計劃進行:“……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干,稱畚築,程土物,議遠近,略基趾,具鍭糧,度有司……”(見《左傳·宣公十—年》)。可見早在兩千多年前我國建築施工中就十分重視工程的計劃與施工組織:主築城者“封人”,既要任命“司徒”掌役,又要根據工程量對工程資金、材料、工具、民工口糧等作出周密計算和安排,還要聘用“有司”作監工。結果“事三旬而成,不愆於素”,完全實現預期效果。
造城工程。這種“規矩先定”,即經過詳細籌劃再組織施工的方法在我國歷史上延續了幾千年,成為我國古代工程建設項目管理思想的重要內容並不斷給工程建設實踐以指導,特別是在一些規模宏大、技術比較復雜的工程上體現得更加突出,效果也更加明顯。如前述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對城的建造就有很周密的工程計劃。不僅測量計算了城牆的長、寬、高以及溝洫在內的土石方總量,連所需人工材料、從各地征調人力、往返道路裡程、人員所需口糧、各地區負擔的任務等,也都計劃周詳,分配明確。唐代改建大明宮,包括十余座殿堂,工期僅用了一年。公元700年河南嵩山建造三陽宮,也只用了幾個月時間。明代改建北京城時,紫禁城內工程浩大的宮殿群和宮城前的太廟,以及包括有8350間房屋的10個王邸,僅用4年時間便全部告竣。
- 上一頁:山西:民間古建保護喜憂參半
- 下一頁:關於古建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