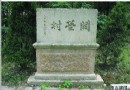打磨沖:造“硔”字的母腹
日期:2016/12/14 9:48:01 編輯:古代建築史
廢棄的石碾

賴慶國一行,專門對“打磨沖”進行歷史追溯和文化探訪
個舊的傳奇人物沙積高以及他的兒子沙積秀、孫子沙榮南三代石匠的故事。早些年,個舊錫礦山是使用一種古老的石臼來舂礦、碎礦的,人稱“碓窩”,生產效率極低,晚清以後,個舊出現了石碾和石磨等生產工具,錫工業隨之進入了規模化生產的“新石器時代”,拖動石碾和石磨的獸力,將人力大大解放出來。據民間流傳的因“古臼”而得名個舊的錫都,又因為這種石碾、石磨大規模生產制造基地的形成,而誕生了一個曾經遠近聞名的“打磨沖”。
“銀子五兩五,出土又入土,石完山歸主……”而今,“中國錫工業的末代石匠”沙榮南老人也永遠地走了,這些以各種形式散落於錫文化各個角落裡的石器,又怎麼樣了呢?
大師看見:石匠走了 石磨還在
不久前,個舊市的中國工藝美術大師賴慶國先生一行10余人,專門對白馬寨的“打磨沖”進行一次歷史追溯和文化探訪。賴慶國先生說,現在,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有這樣的認識——打磨沖是錫文化重要的遺址,當年到打磨沖挑過柴、打過豬草的老錫都人,說到打磨沖,仍然精神煥發。但是,如果缺少足夠的重視、保和開發利用,這些錫工業的‘新石器’可能慢慢就被大自然的流沙淹沒,現實的打磨沖就難免在一種不經意的疏忽中變成一個遙不可及的歷史文化符號。
隨著世間滄海桑田的變遷,而今,出個元公路仙人洞隧道200米以下,便可探訪到當年的“打磨沖”遺跡。6年前,記者曾經陪同“中國錫工業的末代石匠”沙榮南,以及沙榮南失明的兒子,在當地向導解定生、馬忠指引下,找到了打磨沖一道攔河壩下方集中填放著的數十套已經打好的石磨,它們靜靜地與荒草為伴,俨然眨眼間就會消失的瑪雅文明。向導解定生、馬忠介紹,遇到下雨,還會有石磨從山上滾下來,村民們放牛,沿河一路走,可見到一些清晰的石磨和廢棄的石碾,修個元公路時,施工人員還搬來一些現成的石磨築壩打牆。“打磨沖”當年生產的宏大氣勢,可見一斑。
不久前,中國工藝美術大師賴慶國先生一行,在打磨沖方圓數平方公裡探尋,依然要忍受著穿越叢林時皮膚被剮傷的疼痛,當年沙石匠家野外作業的艱辛感同身受。遺憾的是,6年前能夠見到的石磨子,現在少了很多,但是大家都說,還能感覺到當年沙榮南念著他爺爺和父親與當地村民簽訂的一份契約:“銀子五兩五,出土又入土,石完山歸主……”似乎還在打磨沖回蕩。
然而,石頭沒有完,打磨沖河谷裡散落的一些石磨對這些探訪者進行著無聲的交流,一片盛開的油菜花地裡,還靜靜地躺著打造錫礦碾子的原料巨石。
對於這批“突然出現”的探訪者,白馬寨的村民一時間議論紛紛,有的認為是“尋寶”,有的認為是“探礦”,有的略知來意,誤認為打磨沖遺留的石磨子和那些半成的石碾子可能“開始值錢了”。事實上,對於粉碎錫礦的石碾子,當年人稱“碾粑粑”, 沙榮南曾經介紹,在他印象中,個舊民間至少應保存有6套,分別是礦老板蘇鑫龍、張三爛眼、李聘購買的,一套大約600塊銀元。寶豐隆附近曾出土過“碾粑粑”,1995年個舊市獸醫站附近挖地基,沙榮南還發現過配套的碾槽。現在雲廟裡保存的石碾,應該是當年李聘買走的兩套之一,其價值,顯而易見受當年落後的生產條件限制。所以,當年沙石匠家的手藝聲名遠播,刻碑字時,刻下多少石碴,買家就要給多少手工錢,而且還要包著吃住。
賴慶國與隨行的村民們交談,置身於漫漫歷史長河,沙石匠家致力於從“碓窩”中脫穎而出的“新石器時代”,而今所保留和體現的主要是文化價值了。
打磨沖:造出會意字“硔”
在打磨沖探訪的過程中,賴慶國先生召集大家在一片沙灘上小憩,各抒己見,探討如何對打磨沖進行“文化包裝”,有人從它的功能想到了“造字”。
造字法不外乎是“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假借”和“轉注”,石磨之和石碾子是用來碎礦的,而舊時原礦習慣被人們稱為“硔”。打磨沖,與金湖文化廣場石壁上那個彤紅的“硔”字,自然而然聯系在了一起。
在個舊的那些老四合院裡,爐坊中碎礦的石磨,隨著歲月的流逝,變成了婦女的洗衣板,變成了天井中水龍頭下的墊腳石。大家談笑風生,真的只有到打磨沖,人們才可以直觀感受到,石磨子和石碾子是石頭做的,錫金屬也是藏在石頭裡的,石頭磨子和碾子,將藏著錫金屬的礦石磨碎,這一過程都是不同形態和狀態的石頭們共同完成的,完成的結果,最終就是“石”、“共”這一產品,就形成一個會意字“硔”,從這個意義上,出自老陰山腹地的錫礦,從“塃”的原始狀態,通過老陽山打磨沖的石磨和石碾的“共同參與”,完成了對“硔”字的創造,打磨沖也就成了創造這個會意字的母腹,這種創造其實是一種文化的暗合與升華。陰山腳下的金湖文化廣場,陽山河谷裡的打磨沖,也就從歷史文化的意義上連為一條渾然天成的旅游路線。
賴慶國感慨,我現在理解一位雲南作家對打磨沖遺址的描寫了:一盤盤石磨像大山的鈕扣正在“呼呼”大睡。我突然覺得它們是有了名字的石頭,但它們又一次也沒有用過自己的力量,曾被石匠撫摸過,曾被告知就要嶄露頭角,它們一直還在默默地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