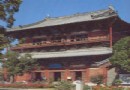禅文化領略漢唐古韻風
日期:2016/12/14 22:01:17 編輯:古代建築史宗教在發展的過程中,借文學藝術廣為傳播,不斷深入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建築藝術、門窗镂雕、飲食文化、服飾、儀式,在老百姓筷子上,灶房裡,房梁、房檐上,桌椅刻雕上,衣服上,褲腰帶上,都會出現帶有宗教色彩的裝飾印記。
眾所周知,作為文學的始源,神話的產生是原始人依據自己的宗教信仰創造出來的。馬克思在《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中指出,在人類的童年時代,由於認識水平低下,人們不可能用抽象思維對周圍世界作科學說明,只能通過宗教的想象和幻想,作形象化的解釋。他們信仰“萬物有靈”論,把自然界想象成同人一樣有意志、有感情。於是產生了關於自然界的各種各樣的神話。這是原始人“用一種不自覺的藝術方式”,對周圍世界所做出的藝術概括。
文學藝術的發展直接影響了戲劇藝術。佛教與戲劇佛教傳入中國後,在唐、五代時,為使佛教經典的內容平易通俗,直接以說唱方式演說佛經故事,慢慢發展出各種戲劇形式與唱白兼用的特色。現今流傳的著名戲劇如“三藏取經”、“目連救母”等,在戲劇藝術表現手法、素材來源、思想教益內涵等各方面,都與佛教的流傳關聯而產生。將佛教中的人物戲劇化,不但為戲劇的誕生提供了豐富故事題材,也為社會廣泛傳播了忠孝節義的觀念,達到了推動佛教教化的意義。
中國說唱藝術專家經過長期的考證,認定古代的“變文”為曲藝藝術的起源之一。變文,是唐朝受佛教影響而興起的一種文學體裁,是一種佛教通俗化、佛經再翻譯的運動。由於佛經經文過於晦澀,一般民眾仍難接受。僧侶為了傳講佛經,將佛經中的道理和佛經中的故事用講唱的方式表現,這些故事內容通俗易懂,寫成稿本後即是變文,19世紀末才發現於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僧侶留下的底本稱之為“講經稿”。稿中每每穿插許多故事,遇到人名地名更是極力描繪,故事部分畸形膨脹,後來逐漸演變,趨向於以故事為主題的方向發展,佛經本身則變成了故事的素材。近代學者多用變文的名稱概舉俗講經文及俗賦、詞文、話本等說唱文學。盡管學者對其“變”字之謂,多有釋疑,變文實質上都是通俗的敘事文學,並以說唱相間為其主要藝術特征,應當視為戲曲和通俗小說的重要淵源之一。曲藝中的評書、評話甚至類似西藏的《格薩爾王》史詩類藝術形式也應該源於此,應該是沒有什麼爭議的。一些曲藝專家認為,中國佛教歷史上的這些特殊的“演說家”,他們同時又必須是一批虔誠而勤勉的口若懸河的“傳教士”,他們要堅定地圍繞著“先明三世因果,卻辯一齋大意”的基本宗旨,施展出超越兩晉名士的語言功力,進鄉問俗,深入淺出,旁征博引,辯才無礙,與說唱藝人無異。
人類圖騰崇拜原始宗教。美術在原始社會,伴隨文字誕生、發展。魯迅先生說,原始人“畫一只牛,是有緣故的,為的是關於野牛,或者獵取野牛,禁咒野牛的事”(《且介亭雜文·門外文談》)。可以看出原始人畫動物,帶有一定的實用目的,他們用巫術“禁咒”野獸達到狩獵成功的願望,也反映人類通過美術產生審美快感體驗。可宗教的體驗是嚴格正統的,在本質上是嚴格禁止和壓抑一切人間感覺的享樂。佛教在早期禁止描繪佛陀,伊斯蘭教則自始至終禁止將一切人的形態來作寫實性描繪。但,歷史上佛教在圖像上首先突破,以大量雕塑和繪畫促進了佛教的傳播。以精美的壁畫和塑像聞名於世的敦煌莫高窟被譽為“東方盧浮宮”,是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大、內容最豐富的佛教藝術聖地,美術與佛教的結合在這裡有精美的展現。
隨著佛教的盛行,佛像雕塑成為中國古代雕塑藝術的主流。雕塑藝術發展繁榮的過程,可以充分證明,在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中,佛教是最具有藝術性的。藝術與佛教在認識、掌握世界的方式上有某些共同之處的認知,形成了著名的雲岡、敦煌、龍門、麥積山四大石窟的經典佛教藝術塑像的生成。這些雕塑均開鑿於魏晉南北朝時代。北魏時期的造像,南北朝的佛教雕刻,風格各異,或莊嚴、或渾樸、或靜穆,佛的偉力與藝術魅力,相映成輝。
關於音樂,根據可考歷史文獻,音樂專家們認為,我國的佛教音樂創作來自於三國時期的曹操之子曹植。傳說中他在游覽魚山時,忽然聽到空中有一種巖谷水聲,聲音清揚哀婉,良久細聽後,深有所悟,於是便摹其音節,根據《瑞應本起經》作曲作詞,終成音樂,即是後世傳誦的《魚山梵》。曹植將古典樂曲與佛法宣揚的文字相結合,在傳統民間樂曲的基礎上創作了佛曲。在民間,文人們描寫佛教音樂的傳播:唐代姚合“仍聞開講日,湖上少漁船”描寫普通民眾對俗講趨之若鹜,“遠近持齋來谛聽,酒坊魚市盡無人”,以及韓愈“街東街西講佛經,撞鐘吹螺鬧宮庭”的詩句,描繪了當時佛教俗講僧們對社會各階層的巨大影響。
佛教在書法藝術的傳承方面功德無量。中國書法家協會顧問鐘明善說:“佛教傳入中國之前,以漢字為載體的中國書法已經歷了幾千年的歷史。佛教傳入後,佛教經典要用漢字翻譯。對於翻譯家,不管是外域的還是本土的,都涉及對佛法的理解,以及對漢字形、音、義的進一步理解。文字首先是作為書寫經文的載體,記錄佛法佛理。由此開始,中國書法和佛經的傳播密切相連,和佛教的傳播也密切相連。”為了傳播佛法,一些僧人幾乎一生都在抄經;長期以來以經文形式留下的書法瀚如煙海。就其書法藝術而論,比較有代表性的就有王羲之抄寫的《遺教經》、柳公權抄寫的《金剛般若經》、蘇東坡抄寫的《華嚴經破地獄偈》、黃庭堅抄寫的《文益禅師語錄》、趙孟頫抄寫的《佛說四十二章經》、弘一法師抄寫的《華嚴經》,它們都是我國書法藝術中的珍品。
舞蹈是人類歷史上產生最早的藝術形式,借用舞蹈形式來傳播宗教,這已成為宗教傳播的一個普遍規律。原始宗教舞蹈幾乎都是神靈形象。藏族的舞蹈、薩滿教的舞蹈都是典型代表。《洛陽伽藍記》裡,記載南北朝時佛教在節慶時舉行樂舞的盛況:“景明寺在八日節中,梵樂法音,聒動天地,百戲騰骧”,景興寺“飛天伎樂,望之雲表”,“舞袖徐轉,絲竹寥亮,諸妙入神”。描寫了隨著佛教傳入中國,佛寺除了繼承南北朝時代民俗歌舞的活動之外,還舉辦廟會、戲場,將各種民間流行的節目匯集於此。我們現在欣賞到的舞蹈家們,以“反彈琵琶”為代表性動作的“霓裳羽衣舞”,傳說就是由擅於歌舞的唐明皇創作的將婆羅門舞曲、西域舞曲及漢族舞蹈熔於一爐的作品,堪稱為中國舞蹈史上的一顆明珠。
宗教在發展的過程中,借文學藝術廣為傳播,不斷深入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建築藝術、門窗镂雕、飲食文化、服飾、儀式,在老百姓筷子上,灶房裡,房梁、房檐上,桌椅刻雕上,衣服上,褲腰帶上,都會出現帶有宗教色彩的裝飾印記。
在佛教對於中國文化藝術的影響的印記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宗教依賴於藝術宣揚弘法,藝術依賴於宗教發展的這段歷史。
- 上一頁:中國式傳統古建園林藝術
- 下一頁:買新房中式裝修必知的幾條禁忌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