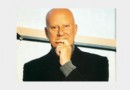古建空間停滯變革的深層原因
日期:2016/12/15 2:01:24 編輯:古建築結構 引言
尊崇漢人最古老的典籍規章來築城,使王朝在倫理體系上坐上“正統”的位子,來獲取世俗認可。直到今
中國傳統空間以“院”為單位,通過把該單元天,新中國成立後的幾十年間,北京市內城東西長安進行組合來增加面積和空間的變化。從倫理上講,街以北的街道胡同,也還都沿襲元大都街巷的布局,這種院落可無限延伸,在空間的等級上也不會產生東西向平行的胡同排列的很有規律。混亂。因為每個“院”中的幾幢房屋各自有獨立的元大都未必代表當時的最高水平,也無法與前結構體系,互不干擾。該形式普遍通行於華文化影朝的繁華昌明一脈相承。但就是這樣一個城市,最響下的所有地區,雖有高矮、大小和裝飾的差異,最忠實地體現了統治者的心態——利用“正統”和但結構和組合方式大致相同。其千年來保持一致,“崇古”觀念,尊崇最古老的典籍規章築城,以此絕非巧合。來為自己的統治加上“正義”的砝碼,鞏固地位。元以前是數千余年的儒家文化浸霪(儒家崇古,上

1. 文化上
推堯舜禹為文化范本),祖訓總被視為正統。這正如同典籍之與中國空間的意義和束縛一樣。
1.1 上古的一脈相承修葺之風,遠不及重建之盛,歷代素不重原物中國人有種“正統”和“崇古”的觀念。即使是之保存,唯珍其舊址及創新年代而已。「2」墳墓工外來民族元朝,建造的元大都是體現《考工記》規劃程倒有鞏固永保之觀念,然隱於地底之磚券室,與思想最為徹底的。「1」統治者搬來漢人的先祖聖賢,地面木構建築,其原則互異,除少數外,並未因磚券應用於墓室之經驗,致改變中國木構空間而改用磚石疊砌制,正是崇古、不求原物長存、及對石質力學缺乏了解等綜合因素,導致建築空間難有突破,反而,墓室間或以磚石模仿地面建築結構。這正如佛塔來到中國後的變化。
1.2 包袱和慣性
文化是力量也是障礙。近代工業革命率先發生在英國,近現代建築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第一座鋼鐵龐然大物——水晶宮也出現在英國,但現代的工業設計卻非源自於此,且這個轟轟烈烈進行工業革命的國家中,還形成了對工業社會帶有深深懷疑的學術流派和設計潮流——如以莫裡斯為代表的“藝術與手工業活動”。而“西方歷史上最後一個民族”——日耳曼反而成為生產、政治、戰爭領域乃至設計領域的個中翹楚。
人類史上的許多早期帝國,雖大興土木,但並沒有產生相應成熟的空間美學理論。如,至文藝復興及以後,歐洲才開始在空間理論上大做文章,雖然那是因為城邦、領土間試圖以此來顯示自己的武力和財力。「3」而中國傳統空間的建設中,幾乎從未進入這個領域。可將之歸因於文化和歷史的慣性,但具體是文化中的那些方面、社會制度的哪種特征使得這種進入未能全面完成呢?考慮到明清江南地區商品經濟的高度發展和文化倫理觀念與資本主義早期的歐洲社會很相似,不禁對中國古代未能在空間建設 的意義上有所變革、理
的意義上有所變革、理
論上未能深化更為好奇。也許,大一統的集權國家對效率的追求可能是重要原因。正是對帝國統治之穩固和長久的追求,使社會生活和文化發展都圍繞這一點打轉而難以甩開包袱,自由前進。因為新王朝總是忙於對舊王朝的空間方式和建造技藝進行模仿,加上工匠的地位低、創作自由少,技藝大多未能積累,其技藝總是隨著朝代的更迭而載浮載沉。
2. 倫理上
2.1 “房”“人”關系
在中國古代讀書人的心目中,人與人、物與物間疏密適當的關系是個人修為的體現,而傳統空間疏密適當、四平八穩的節奏方式正好與之相符。他們以房屋形式指代人際關系,現實的空間位置是自己在宗族關系中地位的體現。“房”字的一項意義為“指家族的分枝”,「4」家庭、房、家族、宗族、村落,它們在中國人的觀念裡根深蒂固。只要該倫理關系被認可,這種空間形式就會一直存在。當然如果這種倫理觀念遭受重創,其空間形態亦難以保存。從另一方面來說,也是國家家族化,但其政治目的並非讓全國人像一家人般相親相愛,而是使其馴順,方便統治。這種空間是倫理政治的必然產物,並反過來為這種制度服務。而中國傳統空間在理論上也有無限的生長余地,只需在原家族院落外再建一院,整體格局依然成立。中國傳統社會的等級運作基本不是世襲制的,而是按照流動性來實現人們想改變身份的意願。每一個人(或家族)有一種在現有制度中改變自己處境的途徑——科舉考試。「5」而每一個新來者在獲得成功後只要“繼承”原有的、與社會結構相符的空間模式即可,任何對空間的具體變更都不需要, 甚至因其表現了對傳統的不敬,還可能招致禍害。這可能是長久以來空間形態未能突破的社會倫理原因。也因為這強大的倫理制度,高等級的和家族式的住宅與都城的布局幾乎是同構的,而傳統民居的堂屋擺設也幾乎是相同的,無論是高等級的王府,還是普通人家的堂屋,甚至南北方的差異亦不大。差異只存在於開間的大小、院落的進深、裝飾和陳設是否講究等細節上。我們今天所見的中國鄉間的村莊小鎮的隽永靈秀,不完全是建築家或藝術家們的藝術作品,更大程度上是封建王朝的一代代護衛者們逐漸構築起來的,是不變的倫理觀念的體現。倫理觀念力量的強大,是現在世界上任何法律法規都無法比擬的。
甚至因其表現了對傳統的不敬,還可能招致禍害。這可能是長久以來空間形態未能突破的社會倫理原因。也因為這強大的倫理制度,高等級的和家族式的住宅與都城的布局幾乎是同構的,而傳統民居的堂屋擺設也幾乎是相同的,無論是高等級的王府,還是普通人家的堂屋,甚至南北方的差異亦不大。差異只存在於開間的大小、院落的進深、裝飾和陳設是否講究等細節上。我們今天所見的中國鄉間的村莊小鎮的隽永靈秀,不完全是建築家或藝術家們的藝術作品,更大程度上是封建王朝的一代代護衛者們逐漸構築起來的,是不變的倫理觀念的體現。倫理觀念力量的強大,是現在世界上任何法律法規都無法比擬的。
2.2 通用化和標准化營造
宗教禮制的等級居住,客觀上需要住居的單體和細部構件標准化,否則就缺少可比性。即以相同或相似的單體構成元素之間相互比較,顯示出等級性。自古以來,對物品的設計不外乎兩種:①通用式:綜合眾多要求,定出標准的形式,供選擇采用。②特殊式:按照個別不同的情況和要求進行特殊的個別設計……「6」歷史上,西方建築采用的是後者,中國古建采用的是前者:房屋就是房屋,不管什麼用途幾乎都希望合乎使用。標准化的建築設計已成為宗教禮制下的使用者、營造者的自覺的共識,但其自覺的營造行為的背後驅動因素仍是宗教禮制。通用式和標准化使建造成為匠人的事,不需要建築師設計。沒有了設計階層,古代住居和各類建築標准化空間就又缺少了一個客觀的變動因素。工匠階層在古代營造中的作用很大,但他們暗於文字,師徒傳承,至多只能對建築形式和結構做些小改動,是限制下的創新,而不能撼及或動搖宗法禮制,是其空間未能創新的又一因素。
2.3 倫理的調味劑
與倫理中心越遠的民間宅院和園林,其空間設計自由度雖較宮殿高,但它也只是文人氣質和浪漫色彩在等級森嚴的倫理社會的補充,“我們的傳統和社會結構雖有同構色彩,但其中往往有自由呼吸的小空間”,「7」它並沒有一直走下去,最終走向繁瑣。且園林對“美”的討論僅限於“好古”和“儒雅”的范圍,統治階級當然不會干預,甚至樂見其成,因為這些人然是維護王朝統一者,因為只有龐大的國家才能給這些小群體提供足夠的、成本低廉的資源和有效途徑;而且文化上的優越感還會使他們中的一部分成為王朝及制度的擁護者。那種以頌揚人的自由和對宗教的反抗精神而生發出的空間藝術的新理念,在中國古代社會是不可能存在的。
3. 時空觀
3.1 時間觀與歷史觀
中國古人的時間觀和歷史觀不是線形的、向前的,不是起始於一確定的時間(如上帝之子誕生於伯利恆的馬槽裡),而是被描繪成起於無始無終的混沌世界。既然如此,也便不會有對永恆的追求。中國人以甲子(6年一輪回)為時間觀,尤其重視“代”的相繼,代代相傳、四時更替的輪回觀幾乎涵蓋了中國人日常生活的大致范圍。並且他們發現自己的人生經驗是對古人的人生經驗的一種重復(即使有不同,也是很小的改
變),他們更崇尚從小說、戲劇中來體驗歷史,從前人的經驗中來發現人生的意義。他們知道再怎麼變也超不過歷史的人生經驗,知道這一點,對“變”的追求就不迫切了。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歷史總是無限膨脹的,足以填滿現實世界;而現實則是干癟的,因為它永遠是歷史的一部分。如果歷史並不按照線性的時間軸而前進,那麼世俗生活中的所有內容都只是曾有過的生活狀態的不同摹本。永恆並不體現在巨大的石塊中,而在一代代的摹本中延續。注釋所以即使是每朝每代的開國之君,也很清楚他的王朝不會永存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雖然他渴望他的子孫比前朝優秀,每個王朝創始者都會給自己的王朝起一個名字,這種現象不是很有趣嗎?若某位開國之君真的認為其王朝會“千秋萬代”,又為什麼要取個名字呢?一部二十四史記載了二十四個時間段的輪回,每個王朝都是“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8」於是人們亦不需要通過宏偉修建來追求永生,因為他們很清楚世上沒有“永生”。甲子是一種輪回,人生經驗和歷史是一種輪回,導致他們並不重視居住空間的變化。甚至於,還很滿足目前的生存空間現狀。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雖然他渴望他的子孫比前朝優秀,每個王朝創始者都會給自己的王朝起一個名字,這種現象不是很有趣嗎?若某位開國之君真的認為其王朝會“千秋萬代”,又為什麼要取個名字呢?一部二十四史記載了二十四個時間段的輪回,每個王朝都是“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8」於是人們亦不需要通過宏偉修建來追求永生,因為他們很清楚世上沒有“永生”。甲子是一種輪回,人生經驗和歷史是一種輪回,導致他們並不重視居住空間的變化。甚至於,還很滿足目前的生存空間現狀。
3.2 時間觀與空間觀
卡斯騰·哈利斯主張:建築不僅僅是定居在空間中,從空無的空間中拉扯、塑造出一個生活的地方。對時間流逝的恐懼和無奈仍然保留著,其對“永恆”形式的追求仍然被看成是建築美感產生的重要來源。「9」在建築中將時間進行空間化,這是西方人追求永恆的方式。而中國傳統空間則在較少變化的空間形態中獲得了“時間的空間化”。更因為將時間凝固是強化某種倫理和思想意識的最好方式,也是人們在歷史中沉思的絕佳場所。聲稱以造化為師的中國人總是嘗試依照自然的法則進行創造,這些法則包括空間布置等的變異、
突變、變化,隨時隨地的不斷增加來創造一種新的形態,但整體的空間構架不變,因為他們認為:如同自然界一樣,萬物蘊藏玄機,變化將自行湧出,不需刻意求變。易系辭言:“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天指時間,地指空間,時間尊於空間。錢穆先生言:正因重時間,屬虛屬動(虛為抽象,動衍變),故中國人求常不求變。西方人重空間,屬實屬靜,故求變求新。「10」可謂中國五千年乃其民族生命之綿延,而西方則自埃及、希臘以至今日之英、法、美、蘇,民族相異,生命亦變。
- 上一頁:平順龍門寺
- 下一頁:單座古建與現代城市的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