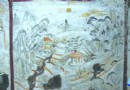六旬老人30年的堅守這座祠堂所講述的五百年過往
日期:2016/12/14 10:51:46 編輯:古建築工藝67歲的沙國佳住在寧波市區,但每周都要回一趟位於鄞州塘溪鎮梅溪水庫邊的沙村老家。從他家的小樓再往上走幾步,就是沙村人的精神家園沙氏宗祠。這座有著500多年歷史的沙氏宗祠,沙國佳守護了它30多年。 吱呀一聲,門開了,陽光下輕塵飛舞。沙國佳轉了一圈,開始了重復多年的工作:掃掃院子,撣撣灰塵,檢查線路,更換燈泡…… 沙氏宗祠是沙村輝煌與榮光的歷史見證,這個偏僻的小小村莊,經過數百年歲月積澱,孕育不少名人:有以當代書法泰斗沙孟海為首的“沙氏五傑”,有傳奇畫家沙耆…… 如今,沙氏後人散落在天涯海角,沙國佳老人希望,守護好這座見證沙村歷史的宗祠,留住代代相傳的沙氏榮耀和一脈鄉愁。 沙氏宗祠的紅色印記 沙村的沙氏宗祠,遠非普通意義的家族祠堂。今天的沙氏宗祠,曾是當年鄞縣第一個農村黨支部——中共沙村支部舊址。那段烽火歲月,給這座百年祠堂刻上了深深的紅色烙印,而“沙氏五傑”事跡的陳列,更加豐富了這裡的紅色記憶。 “沙氏五傑”說的是沙孟海、沙文求、沙文漢、沙文威、沙文度五兄弟。老大沙孟海被尊為當代書法泰斗;老二沙文求乃大革命期的廣州市委秘書長,廣州起義時同陳鐵軍烈士一道壯烈犧牲;老三沙文漢是共產國際的紅色間諜,長期從事對國民黨軍隊的策反,解放後出任浙江省第一任省長;老四沙文威是李克農、潘漢年手下的諜海干才,以國民黨專員的身份在國民黨陣營中隱匿18年,利用沙孟海的掩護為革命做了許多貢獻;老五沙文度是革命藝術家。 1900年出生的沙孟海自幼愛好書法、篆刻,少時家境窘迫,幾個弟弟先後辍學。19歲師范畢業後,他便設法把幾個弟弟一個個接到外地讀書。 高昂的學費逼著他在上海過起了鬻文賣字的生涯。當時上海灘仕宦商貿每遇婚喪壽宴,多喜歡饋贈書畫作品,雅而不俗。那陣子,他的書法在上海灘已小有名氣,又只有二十幾歲,出手快,有急需趕時間的活計,人們總喜歡找他,生意日漸紅火。 憑借其越來越大的名氣,沙孟海開始涉足政界,曾任國民政府總統府秘書,與蔣介石、蔣經國、朱家骅等國民黨上層人物都有過許多交往。 今天的沙村,上了年紀的老人,很多都還能說出沙孟海當年兩篇電文定亂局的故事。 這個故事說的是武漢會戰後,抗日戰火迅速蔓延。日本軍部特派一個叫川本芳太郎的大佐專赴北平,敦促吳佩孚出山。川本為接觸吳佩孚,還拜吳為師,伺機相勸。一時間,“大帥府”熱鬧起來,來自全國各地“擁吳出山”“挽救大局”的電報紛至沓來。 此事在國民黨政府中引起震動,朱家骅緊急求見蔣介石,蔣介石聽後一臉陰沉。朱家骅獻策,以他中央委員會秘書長的名義給吳佩孚發封電報,曉以大義,阻止他出山。蔣介石點頭同意。 當時,沙孟海經同鄉陳布雷介紹,已在朱家骅手下當秘書,起草電文的任務自然也就落在了他的頭上,沙孟海深知這個擔子有多重。 當晚,他泡了杯濃茶,凝筆靜思。一篇五百余字的四六骈文讓朱家骅極為滿意。電文聲明“春秋大義”,敦促吳佩孚千萬以民族為重,不要“一失足而成千古恨”。 當時吳佩孚正就“出山”之事同川本商定程序,見到電文,這位戎馬一生的將軍仿佛遭到了電擊,強烈的自責令其做出放棄出山的決定。 時隔不久,汪精衛公開投敵,派人欲拉吳佩孚下水。朱家骅得到情報後,又叫沙孟海起草了第二封致吳佩孚的電文。隨後,朱家骅便收到吳佩孚的電報:僕雖武人,亦知大義,此心安如泰山。 沙孟海的特殊身份為弟弟的革命行動起到了很好的掩護作用,早在沙孟海任職浙江省政府時,其二弟沙文求就已回鄉從事農民運動,在沙氏宗祠成立了中共沙村支部,這是寧波地區最早的農村黨支部之一。 烽火歲月已成歷史,但歷史是不能遺忘的,這正是沙國佳這些年守護宗祠,收集先賢遺跡的原動力。他希望有更多的年輕人來挑起管理祠堂的擔子,把沙氏祖先留下的遺產代代相傳。 神馬找到的福地 地處沙村中心地段的沙氏宗祠,經歷500多年的風風雨雨,傳統木結構的四合院建築,散發著古樸雍容的氣息。 匾額是沙孟海的手筆,冬日的暖陽下,“沙氏宗祠”四個金色大字熠熠生輝。年老的村民坐在宗祠的門庭前,曬著太陽聊天,享受著山村的閒散和安逸。 宗祠入口處2米高的大戲台,粉牆黛瓦,木門廊檐,書寫著這裡曾經的顯赫與榮光。 宗祠中堂擺放著三尊沙氏祖先的坐像。家譜記載,他們就是沙村始祖沙丙祖孫三代,皆為當朝高官。當年,這裡曾是文官下轎、武官下馬的令人景仰之地。 梅溪沙村的歷史可追溯到南宋初年,至今有900多年的歷史。 據記載,沙丙乃南宋高宗皇帝趙構身邊的將軍。南宋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金兀術率大軍南下,當時還是小康王的趙構帶著沙丙等人逃出金陵城,一路逃至明州(今天的寧波)。 幾經搏殺,趙構身邊的護衛越來越少,遂令沙丙斷後,阻金兵於姚江渡口。後因兵力懸殊太大,沙丙戰敗,被金兀術斬首。 趙構建立南宋後,感念沙丙救駕有功,特封其為定國公,並賜金頭一個。沙丙的墓就在鄞州五鄉匯纖橋,遺憾的是,“大躍進”年代被拆毀。 沙丙子孫盡孝守墓,便在此定居開枝散葉。至第四代孫沙用明時,為避戰亂,便遷到了今天的塘溪鎮。 塘溪地名源於兩條溪流。很久以前,這裡曾是一片汪洋大海,象山港海水經大嵩江而來,為防海水進入築塘御之,梅溪水與沙河塘水交匯,故得名塘溪。古鎮興起於唐宋,發展於明清。 沙氏遷居於此,歷史上還有段美麗的傳說。當年,沙氏族人從甬江口乘船順流而下,經過鎮海口,穿過大嵩江,到達塘溪的沙河塘。這裡有片陸地,遂搭帳篷而居。 隨行的那匹白馬每天早上放到塘溪後岙,一天傍晚去牽它回家時,那匹馬卻不見影蹤,最後在距離後岙不到1公裡的地方找到。接下來幾天,天天如此。 白馬的行蹤引起了沙氏族人的好奇,前往考察。那地方不大,卻背山靠水,實乃建房棲居的不二選地。前面的小溪就是梅溪,溪水清澈見底。梅溪水庫建成之前,梅溪水一直是遷居到此的沙氏後人世代飲用的生活用水。 “一帆風順進嵩江,神馬引路到梅溪。”說的就是這段傳說。白馬因此受到了神一般的敬仰,它死後,沙氏後人還為它修了座廟,取名白馬廟。如今,因為梅溪水庫的修建,該廟已成了深埋水庫的歷史遺跡。 沙村走出的天才畫家 白馬引路雖只是個傳說,卻注定了這片土地的神奇。數百年間,沙村這片土地孕育了一個又一個名人志士,留下了許多傳奇。 如今的沙氏宗祠,東西兩廂房俨然成了藝術的殿堂:沙孟海的書法,沙耆的油畫、報紙畫……雖是復印件,卻都是他們藝術生涯的再現。 收集這些復印件並不容易。上世紀80年代,沙國佳出任村支書,萌生了傳承沙氏文化的念頭,歷經周折復印了曾遭毀損的沙氏家譜,並開始致力於祠堂的保護。 今天的廂房裡,沙耆的油畫照片和他晚年生活潦倒時留下的報紙畫復印件,翔實地記錄了這位天才畫家傳奇的一生。 生於1914年的沙耆原名引年,字吉留,幼年多病,上私塾時成績平平,生性內向,唯愛畫畫,自小就有繪畫天賦。11歲那年,他隨父到上海,就讀於寧波同鄉會小學。第二年因病休學返家,後隨家遷居杭州。當時,29歲的沙孟海已在浙江省政府任職,將沙耆送進中學讀書,後又介紹其入讀上海昌明藝術專科學校。 受沙孟海三弟沙文漢影響,沙耆1933年參加抗日救亡活動時被捕,獲刑一年,後保釋出獄,轉入杭州西湖藝專求學。 沙耆的人生轉折發生在20歲那年。經沙孟海推薦,他得以師從徐悲鴻學畫,從此進入真正意義上的藝術殿堂。 沙耆以其繪畫方面的天賦和勤奮,得到了徐悲鴻的賞識,被其推薦到比利時皇家美術學院。旅歐十年,他在油畫藝術方面取得了驚人成就。 長期身處異鄉,又與家人無法聯系,內心的憂郁苦悶竟使其患上了精神分裂症,1946年抱病回國。 曾有傳聞,沙耆因為妻子離他而去導致精神疾病。沙國佳說這絕對是誤傳,他所知道的是,沙耆留學比利時,不知什麼原因,十年沒一封家書。沙耆父母擔心有什麼意外,怕耽誤了媳婦,便勸說媳婦離開沙家。 在沙國佳記憶裡,晚年的沙耆雖然窮困潦倒,卻依然是村裡最受人尊敬的賢人。不論哪家有紅白喜事,沙耆都是座上賓,不過他從不用帶禮金,能做的,就是在報紙上那麼信手一抹。這就是他晚年獨具特色的報紙畫。 近年來,沙國佳一直在尋找那些散落在民間的油畫和報紙畫。近7年來,他搜集了包括沙耆在內的沙氏名人作品幾百幅,自掏腰包加以裝裱。 (來源:東南商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