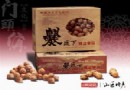尋找“張家口的猶太人”
日期:2016/12/14 18:41:08 編輯:古代建築史
洛克菲勒、摩根、格林斯潘、萊曼兄弟這些曾經主宰全球財富命運的商界奇才,有著共同的猶太背景。起源於阿拉伯半島的猶太人,被認為是世界上最會賺錢的民族。而在中國北方的一個小縣,當地百姓竟有“張家口的猶太人”之稱。他們是誰?這殊榮又緣何而起呢?
一座黃土牆,高聳而厚重,在我眼前巍然屹立。它如城垣般護衛著裡面的子民,在春日的晨曦中,顯得格外威武。
這,就是河北蔚縣赫赫有名的暖泉鎮西古堡村。
倒退百余年,暖泉鎮是個連接河北、山西、北京的商業重鎮。歷史在這裡留下的痕跡,現已成為一處獨特的景致。
穿過北堡門,一腳邁進堡子裡,我頓時吃了一驚:街衢整齊,縱橫有致,勾勒出棋盤格一般的布局;沿街不少民居,青磚灰瓦,門面講究,透露出曾經的富有與殷實。
“暖泉鎮,真是臥虎藏龍啊,”我心想。這時,陪同我的本地人劉聰明先生領著我拐進了一條安靜的胡同,“走,帶你看看喬致庸式的大商人的宅子。”
暖泉鎮的“喬致庸”
這是一片號稱“九連環”的古建築群,分作東西兩路,每路各四進院落,院院相連。正房、廂房、繡樓、祠堂、賬房、長工屋、馬廄、車庫、倉庫,連同供秋後米面加工的碾房,應有盡有。這場面,和山西祁縣的喬家大院頗有幾分相似。
“這宅子中的一部分,原是建於明隆慶年間的總兵府,其後幾次易主,到了清朝初年,被一個新興的富商重金買下,並擴建宅院。此人姓董,名汝翠,人稱‘董大澤’。”小劉說。
“董大澤”是何許人也?小劉講述了一段故事:
明末一個清冷的冬日,暖泉鎮的郭員外在家門口遇到一位乞討的少年,他赤著雙腳,衣不蔽體,在寒風中瑟瑟發抖。然而,仔細端詳,在少年那張清瘦黧黑的面龐上,卻透著與年齡不相稱的堅毅與成熟。郭員外覺得少年定會不凡,連忙叫人把他接進家門,好生照顧。
少年就是董汝翠,來自蔚縣南部山區,15歲時父母雙亡,被嫂子趕出家門,輾轉流落至此。董汝翠被留在郭家的酒作坊和糧鋪裡做活兒。一年後,郭員外認為他“笨而不拙,為人可靠”,遂將唯一的女兒嫁給他,小董也成為郭家的“倒插門”女婿。郭員外叮囑他:“將來郭家的百畝良田,全部家業,都由你來繼承!一定要好好珍惜!”董汝翠淚流滿面,跪著叩頭:“請岳丈大人放心!今日的百畝良田,將來定會變為千頃之地!”
此言不虛,因為幾年後,董汝翠果真使郭氏的家業猛增數倍,資財萬貫,富極一時。富到什麼程度呢?有例為證。
幾番尋訪,我找到了一些有趣的線索:
明朝時,蔚縣稱蔚州,由於鄰近邊塞,“素為臨邊用武之地”,在中原政權與游牧民族的歷次交鋒中屢遭兵亂。出於軍事防備的需要,明朝實行衛所制度,上至京師,下達郡縣,皆設立衛所,依據防區重要程度的不同配置兵力。洪武七年(1374年),朝廷置蔚州衛,有三千戶所,1.68萬人。洪武十五年(1382年),又建蔚州驿鋪站點,由北京經昌平、延慶、懷來、土木至蔚州,使北京與蔚州有了關聯。
新朝初立,百廢待興,剛剛登上皇帝寶座的朱元璋,對蒙古殘余勢力采取了“來則御之,去則勿追”的防御政策。為應對隨時可能南下反撲的蒙古騎兵,他下令在軍事要隘修築堡寨,“屯兵帶甲四十萬,據大險以制諸夷”。蔚縣也不例外,從明初洪武年間開始修建,明中期以後則有“八百城堡”之多。如今依然可見的一處處保留在蔚縣堡門上的題字,記錄了這一史實:上蘇莊堡的堡門上刻著“嘉靖二十二年仲秋吉日建立”,卜家莊北堡的堡門題有:“正德十一年□立,嘉靖二十七年□□□□”的字樣。而在崔家寨堡,我從堡門上方漫漶不清的題刻中,依稀辨認出“大明國山西大同□□□”,“崔家寨堡,嘉靖二十□□□”幾個字。難道說地處冀北的蔚縣,和山西大同有關?
……
馱金載銀的塞外絲路
兩排險峻的高山,像是凌空降下,一邊重巒青翠,一邊峰巖暗紫,只在中間留出一道小徑,蜿蜒向前。
這裡是飛狐峪,位於蔚縣城南約13公裡處,是穿越太行山的一條古通道。明朝崇祯年間(1628年?1644年),兵部尚書、大學士楊嗣昌曾形容它“千夫拔劍,露立星攢”,山路“回首萬變”,如“珠曲蟻穿”,高處“有如天門”,險處“令人旋踵轉足”。
飛狐峪為拱衛京畿之鎖鑰。由此處向南,過河北涞源、紫荊關,便是華北大平原;由此地向北,穿過壺流河盆地北行,則可至張家口和蒙古草原,向西可達山西。明時,如果北方的瓦剌、鞑靼企圖入侵京畿,可由山西大同經居庸關長驅直入,但明廷在居庸關一帶布下重兵,加之山勢險峻,不易突破。因此,南下的蒙古人就選擇先從大同進入河北,再經飛狐峪向東南,越過太行山,迂回突襲北京的西南側。飛狐峪的戰略意義,由此可見一斑。
不過,這條通達四方的軍事要隘,即便在明代守備森嚴的時期,也不乏求財若渴的來往商人。
老話常說,但凡貧瘠之地,最常出現的人有兩種:唱戲的和經商的。山西境內“八分山丘二分田”,北部地瘠民貧,明清時,即便遇上豐年,畝產糧食尚不滿斗。中、南部雖土質稍好,無奈地狹人滿,百姓依舊困苦不堪。為生計所迫,不少農民放下鋤頭,扛起扁擔,挑著晉東南的絲綢、解州的鹽、晉北的明礬和省內各地出產的藥材、羊皮、干果、土布,踏上了離鄉背井的經商路。
……
商路上的镖師
繁榮的商路,必然帶來連鎖效應。一行富,行行富。
在宋家莊古堡,我就意外地“邂逅”了一座因保衛商路而致富的大院人家——“韓家镖局”。韓家大院門口有個石墩,刻著“一百七”三個字。聽村裡的老人說,它是以前镖師用來練武的,作用類似於現在的啞鈴。
如今,這裡住的只是普通村民,镖局不復存在了。不過走進去,我還是大吃一驚:好大個院!這裡的一進院落,足有一個籃球場那麼大!據說,當年韓家镖局白天接镖,晚上習武,都在這裡進行。
韓家镖局的創始人,叫做韓瑛,是土生土長的蔚縣人。他自幼習武,生得高大魁梧,氣力過人,以善使鋼刀著稱。清道光二年(1822年),韓瑛藝壓群雄,在武科舉鄉試中名列第一,同年便在宋家莊創辦镖局,給人押镖為生。他平時常走的路線,就是從保定穿飛狐峪至蔚縣經張家口至庫倫(今蒙古國首都烏蘭巴托)的那條近5000裡長的商路。
那是一個並不遙遠的年代。
那是蔚縣商業的全盛時期。
……
天下十三省,能不過蔚縣人
歷史的車輪,駛向民國十四年(1925年)。此時的蔚縣,有缸行(制酒)、當行(當鋪)、雜貨行、藥行、鹽行、油行、鞋行、氈帽行、餅面行、山貨行、京馃行(熟食)、木料行、綢緞行、瓷器行、文具行22種行業、687家商號,僅縣城內的毛皮商號就有百余家之多。
當時的張家口是響當當的“皮都”,由裘皮、白皮、制革、蒙靴等12個行業組成嚴密的生產鏈條。精明干練的蔚縣人,就是張家口毛皮市場上的“領頭羊”——近八百家毛皮商號中,一半以上的老板是蔚縣人,三萬多從事毛皮業的人員,近三分之二來自蔚縣!
……
有人說,蔚縣人經商的本事,是骨子裡長出來的。或許吧。歷史上與山西的淵源,似乎使蔚縣人天生就有一副經商的頭腦。但若要把自家生意做大做強,僅靠祖上傳下來的基因顯然是不夠的。如果沒有王樸的遠見卓識,沒有文德源、福遠缸坊對品質的苛求,蔚縣商人注定無法在這荒寒的彈丸之地上,開拓出一片廣闊天地。在我看來,這就是他們代代相傳的智慧精髓。
當京張鐵路來了之後
路上,我一度試圖尋覓那些明清商號的影子,但它們卻像是躲進了時間隧道,徹底逃遁到另一個時空之中,不留下一丁點痕跡。那昔日的繁盛,那曾經的歷史,究竟到哪裡去了?
蔚縣傳統商業的蓬勃興起,最初並非完全仰賴北邊的張家口,而它的衰敗,卻與後者息息相關。
……
1909年,京張鐵路通車,考慮到時間的成本,很多商人選擇通過華北平原到北京,在北京的西直門乘火車,經沙河、南口、居庸關、八達嶺、懷來、雞鳴驿、宣化,到張家口,進入張庫商道。這樣一來,曾經的落腳地——蔚縣被繞過了,不再是客商的必經之地。1924年,蒙古共和國獨立。1929年,國民黨政府與前蘇聯斷交,當時在庫倫、恰克圖經商的400余家中國商號全部被當地沒收。自此,張庫商道結束了近4個世紀的繁華,而蔚縣的飛狐峪也隨之逐漸沉寂。
繁華事散逐香塵,流水無情草自春。
昔日車馬輻辏的飛狐峪,最終渺無人蹤,甚至被人們淡忘;暖泉等八大集鎮,也空留大宅門。
在這個清冷的春日,漫步於飛狐古道,我默然無語。
它,曾為蔚縣帶來了勃勃生機;
它,已經這樣寂寥了百年。
我把手放在耳後,靜靜聆聽:誰的鈴聲,清脆而細碎,穿越時空,從歷史的深處傳來?恍恍惚惚,眼前浮現出一隊長長的騾幫,騾子馱著沉重的行李,商旅們步履蹒跚,行進在古道之上…
一座黃土牆,高聳而厚重,在我眼前巍然屹立。它如城垣般護衛著裡面的子民,在春日的晨曦中,顯得格外威武。
這,就是河北蔚縣赫赫有名的暖泉鎮西古堡村。
倒退百余年,暖泉鎮是個連接河北、山西、北京的商業重鎮。歷史在這裡留下的痕跡,現已成為一處獨特的景致。
穿過北堡門,一腳邁進堡子裡,我頓時吃了一驚:街衢整齊,縱橫有致,勾勒出棋盤格一般的布局;沿街不少民居,青磚灰瓦,門面講究,透露出曾經的富有與殷實。
“暖泉鎮,真是臥虎藏龍啊,”我心想。這時,陪同我的本地人劉聰明先生領著我拐進了一條安靜的胡同,“走,帶你看看喬致庸式的大商人的宅子。”
暖泉鎮的“喬致庸”
這是一片號稱“九連環”的古建築群,分作東西兩路,每路各四進院落,院院相連。正房、廂房、繡樓、祠堂、賬房、長工屋、馬廄、車庫、倉庫,連同供秋後米面加工的碾房,應有盡有。這場面,和山西祁縣的喬家大院頗有幾分相似。
“這宅子中的一部分,原是建於明隆慶年間的總兵府,其後幾次易主,到了清朝初年,被一個新興的富商重金買下,並擴建宅院。此人姓董,名汝翠,人稱‘董大澤’。”小劉說。
“董大澤”是何許人也?小劉講述了一段故事:
明末一個清冷的冬日,暖泉鎮的郭員外在家門口遇到一位乞討的少年,他赤著雙腳,衣不蔽體,在寒風中瑟瑟發抖。然而,仔細端詳,在少年那張清瘦黧黑的面龐上,卻透著與年齡不相稱的堅毅與成熟。郭員外覺得少年定會不凡,連忙叫人把他接進家門,好生照顧。
少年就是董汝翠,來自蔚縣南部山區,15歲時父母雙亡,被嫂子趕出家門,輾轉流落至此。董汝翠被留在郭家的酒作坊和糧鋪裡做活兒。一年後,郭員外認為他“笨而不拙,為人可靠”,遂將唯一的女兒嫁給他,小董也成為郭家的“倒插門”女婿。郭員外叮囑他:“將來郭家的百畝良田,全部家業,都由你來繼承!一定要好好珍惜!”董汝翠淚流滿面,跪著叩頭:“請岳丈大人放心!今日的百畝良田,將來定會變為千頃之地!”
此言不虛,因為幾年後,董汝翠果真使郭氏的家業猛增數倍,資財萬貫,富極一時。富到什麼程度呢?有例為證。
幾番尋訪,我找到了一些有趣的線索:
明朝時,蔚縣稱蔚州,由於鄰近邊塞,“素為臨邊用武之地”,在中原政權與游牧民族的歷次交鋒中屢遭兵亂。出於軍事防備的需要,明朝實行衛所制度,上至京師,下達郡縣,皆設立衛所,依據防區重要程度的不同配置兵力。洪武七年(1374年),朝廷置蔚州衛,有三千戶所,1.68萬人。洪武十五年(1382年),又建蔚州驿鋪站點,由北京經昌平、延慶、懷來、土木至蔚州,使北京與蔚州有了關聯。
新朝初立,百廢待興,剛剛登上皇帝寶座的朱元璋,對蒙古殘余勢力采取了“來則御之,去則勿追”的防御政策。為應對隨時可能南下反撲的蒙古騎兵,他下令在軍事要隘修築堡寨,“屯兵帶甲四十萬,據大險以制諸夷”。蔚縣也不例外,從明初洪武年間開始修建,明中期以後則有“八百城堡”之多。如今依然可見的一處處保留在蔚縣堡門上的題字,記錄了這一史實:上蘇莊堡的堡門上刻著“嘉靖二十二年仲秋吉日建立”,卜家莊北堡的堡門題有:“正德十一年□立,嘉靖二十七年□□□□”的字樣。而在崔家寨堡,我從堡門上方漫漶不清的題刻中,依稀辨認出“大明國山西大同□□□”,“崔家寨堡,嘉靖二十□□□”幾個字。難道說地處冀北的蔚縣,和山西大同有關?
……
馱金載銀的塞外絲路
兩排險峻的高山,像是凌空降下,一邊重巒青翠,一邊峰巖暗紫,只在中間留出一道小徑,蜿蜒向前。
這裡是飛狐峪,位於蔚縣城南約13公裡處,是穿越太行山的一條古通道。明朝崇祯年間(1628年?1644年),兵部尚書、大學士楊嗣昌曾形容它“千夫拔劍,露立星攢”,山路“回首萬變”,如“珠曲蟻穿”,高處“有如天門”,險處“令人旋踵轉足”。
飛狐峪為拱衛京畿之鎖鑰。由此處向南,過河北涞源、紫荊關,便是華北大平原;由此地向北,穿過壺流河盆地北行,則可至張家口和蒙古草原,向西可達山西。明時,如果北方的瓦剌、鞑靼企圖入侵京畿,可由山西大同經居庸關長驅直入,但明廷在居庸關一帶布下重兵,加之山勢險峻,不易突破。因此,南下的蒙古人就選擇先從大同進入河北,再經飛狐峪向東南,越過太行山,迂回突襲北京的西南側。飛狐峪的戰略意義,由此可見一斑。
不過,這條通達四方的軍事要隘,即便在明代守備森嚴的時期,也不乏求財若渴的來往商人。
老話常說,但凡貧瘠之地,最常出現的人有兩種:唱戲的和經商的。山西境內“八分山丘二分田”,北部地瘠民貧,明清時,即便遇上豐年,畝產糧食尚不滿斗。中、南部雖土質稍好,無奈地狹人滿,百姓依舊困苦不堪。為生計所迫,不少農民放下鋤頭,扛起扁擔,挑著晉東南的絲綢、解州的鹽、晉北的明礬和省內各地出產的藥材、羊皮、干果、土布,踏上了離鄉背井的經商路。
……
商路上的镖師
繁榮的商路,必然帶來連鎖效應。一行富,行行富。
在宋家莊古堡,我就意外地“邂逅”了一座因保衛商路而致富的大院人家——“韓家镖局”。韓家大院門口有個石墩,刻著“一百七”三個字。聽村裡的老人說,它是以前镖師用來練武的,作用類似於現在的啞鈴。
如今,這裡住的只是普通村民,镖局不復存在了。不過走進去,我還是大吃一驚:好大個院!這裡的一進院落,足有一個籃球場那麼大!據說,當年韓家镖局白天接镖,晚上習武,都在這裡進行。
韓家镖局的創始人,叫做韓瑛,是土生土長的蔚縣人。他自幼習武,生得高大魁梧,氣力過人,以善使鋼刀著稱。清道光二年(1822年),韓瑛藝壓群雄,在武科舉鄉試中名列第一,同年便在宋家莊創辦镖局,給人押镖為生。他平時常走的路線,就是從保定穿飛狐峪至蔚縣經張家口至庫倫(今蒙古國首都烏蘭巴托)的那條近5000裡長的商路。
那是一個並不遙遠的年代。
那是蔚縣商業的全盛時期。
……
天下十三省,能不過蔚縣人
歷史的車輪,駛向民國十四年(1925年)。此時的蔚縣,有缸行(制酒)、當行(當鋪)、雜貨行、藥行、鹽行、油行、鞋行、氈帽行、餅面行、山貨行、京馃行(熟食)、木料行、綢緞行、瓷器行、文具行22種行業、687家商號,僅縣城內的毛皮商號就有百余家之多。
當時的張家口是響當當的“皮都”,由裘皮、白皮、制革、蒙靴等12個行業組成嚴密的生產鏈條。精明干練的蔚縣人,就是張家口毛皮市場上的“領頭羊”——近八百家毛皮商號中,一半以上的老板是蔚縣人,三萬多從事毛皮業的人員,近三分之二來自蔚縣!
……
有人說,蔚縣人經商的本事,是骨子裡長出來的。或許吧。歷史上與山西的淵源,似乎使蔚縣人天生就有一副經商的頭腦。但若要把自家生意做大做強,僅靠祖上傳下來的基因顯然是不夠的。如果沒有王樸的遠見卓識,沒有文德源、福遠缸坊對品質的苛求,蔚縣商人注定無法在這荒寒的彈丸之地上,開拓出一片廣闊天地。在我看來,這就是他們代代相傳的智慧精髓。
當京張鐵路來了之後
路上,我一度試圖尋覓那些明清商號的影子,但它們卻像是躲進了時間隧道,徹底逃遁到另一個時空之中,不留下一丁點痕跡。那昔日的繁盛,那曾經的歷史,究竟到哪裡去了?
蔚縣傳統商業的蓬勃興起,最初並非完全仰賴北邊的張家口,而它的衰敗,卻與後者息息相關。
……
1909年,京張鐵路通車,考慮到時間的成本,很多商人選擇通過華北平原到北京,在北京的西直門乘火車,經沙河、南口、居庸關、八達嶺、懷來、雞鳴驿、宣化,到張家口,進入張庫商道。這樣一來,曾經的落腳地——蔚縣被繞過了,不再是客商的必經之地。1924年,蒙古共和國獨立。1929年,國民黨政府與前蘇聯斷交,當時在庫倫、恰克圖經商的400余家中國商號全部被當地沒收。自此,張庫商道結束了近4個世紀的繁華,而蔚縣的飛狐峪也隨之逐漸沉寂。
繁華事散逐香塵,流水無情草自春。
昔日車馬輻辏的飛狐峪,最終渺無人蹤,甚至被人們淡忘;暖泉等八大集鎮,也空留大宅門。
在這個清冷的春日,漫步於飛狐古道,我默然無語。
它,曾為蔚縣帶來了勃勃生機;
它,已經這樣寂寥了百年。
我把手放在耳後,靜靜聆聽:誰的鈴聲,清脆而細碎,穿越時空,從歷史的深處傳來?恍恍惚惚,眼前浮現出一隊長長的騾幫,騾子馱著沉重的行李,商旅們步履蹒跚,行進在古道之上…
- 上一頁:詩意村莊
- 下一頁:紀念古潮州義安郡建制1600周年
熱門文章
熱門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