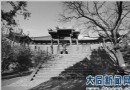二十世紀中國遼金史研究
日期:2016/12/14 9:47:57 編輯:古代建築史一、20世紀上半葉的遼金史研究
在評述這個時期遼金史研究之前,先將本世紀以前的遼金史學狀況作一簡要介紹。
遼朝初年阿保機時代即設“監修國史”,後來正式設國史院,置監修國史、史館學士、史館修撰、修國史等職。遼朝國史有起居注、日歷、實錄等。金滅遼後,先後有蕭永祺撰遼史和陳大任撰遼史,但均未刊行。元朝中統二年(1261年)和至元元年(1264年)曾議修遼金二史。南宋滅亡後,又議修遼金宋三史,均因 “正統”問題長期議而不決。直至元末至正三年(1343年),脫脫任纂修三史的都總裁,決定遼、金、宋“各與正統,各系其年號”,解決了爭議不休的正閏問題,僅用一年時間倉促修成《遼史》116卷。《遼史》主要依據耶律俨實錄、陳大任遼史,參考《契丹國志》及諸史契丹傳等編排而成,當時能夠見到的許多重要史料均未采用(參見馮家昇《〈遼史〉源流考》),載《馮家昇論著輯粹》,中華書局,1987年)。《遼史》雖然缺點甚多,但它畢竟是研究遼史的最基本史料。因此,脫脫纂修《遼史》的出現,在遼史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在《遼史》出現後的約300年間,此書及遼朝史沒有引起史家的多大重視。有明一代,僅有楊循吉撰《遼小史》1卷。這是同明王朝以漢族為正統的傳統觀念相聯系的。
到了清代,情況有所變化,陸續有關於《遼史》補正、考訂之類撰述問世。
(一)拾遺補阙。如厲鹗撰《遼史拾遺》24卷。該書廣采博搜,征引書籍358種,或注或補,將有關紀事系於《遼史》紀、志、傳文之下。此書雖未臻完善,有許多史料如李焘《續資治通鑒長編》、鄭麟趾《高麗史》等,厲鹗都未見過全本,但它還是給後來治遼史者以很大方便。梁啟超說:“遼金元三史最為世诟病。清儒治遼史者莫勤於厲樊榭(鹗)之《遼史拾遺》二十四卷”(《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294頁,中國書店,1987年)。後來,楊復吉又撰《遼史拾遺補》5 卷,采厲鄂未見書及散見他書中有關遼事400條,與厲書相輔流行。厲、楊兩書是研究遼史的重要參考書。
(二)增補表志。補表有萬斯同《遼大臣年表》、汪遠孫《遼史紀年表》等。補藝文志尤多,如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吳骞《四朝經籍志補》、厲鄂《遼史拾遺》補經籍志、楊復吉《遼史拾遺補》經籍志、倪燦和盧文弨《補遼金元藝文志》、金門诏《補三史藝文志》、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附遼代部分、《續文獻通考·經籍考》、缪荃孫《遼藝文志》等,分別含有或專補遼藝文。
(三)紀事本末體史書編撰。李有棠《遼史紀事本末》40卷。分正文與考異兩部分。正文以《遼史》為主,參之以五代與宋、金諸史及各傳記,“區別條流,各從其類”;考異占全書大半,凡與他史及各傳記事有異同,詞有詳細,兼仿裴松之補注《三國志》及胡三省之注《通鑒》,並取司馬光所著《考異》30卷散入各條例,分載每條之下。本書對人名、地名、職官、年代等多所考證,征引書目達600多種。有光緒十九年(1893年)初刻和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重刻本。
(四)詩文輯錄。由於遼代“書禁甚嚴”,所印書籍不許流至境外,“傳入中國(指北宋)者法皆死”(沈括《夢溪筆談》卷一五),加之以後的散佚,所以遼人著作流傳下來者甚少。因此遼人詩文輯錄工作受到學者的關注。清周春撰《遼詩話》1卷,後來增補為2卷,定名為《增訂遼詩話》(1797年)。書中除收錄遼人詩作外,還有宋人使遼詩以及後人詠遼代遺跡的詩。光緒中葉,缪荃孫輯《遼文存》6卷,所收資料以金石碑刻居多。
總之,從元人修《遼史》出現到19世紀末,有關遼史的著述不多。
以下轉入對20世紀上半葉遼史研究的評述。這個時期的遼史學,一方面是繼續就《遼史》進行補正、校勘及遼人著作的輯錄;另一方面是開始用近代史學方法研究遼史。
先談關於《遼史》補正、校勘和遼人著作輯錄。
進入本世紀以來,有關這方面的撰述相繼問世。有李慎儒《遼史地理志考》5卷,這應是本世紀最早出現的《遼史》考訂之作。是書“於遼五京州縣山川悉為考核,標明今之某處,凡舛錯者逐一駁正,疑者阙之”。此外,將四捺缽,五國部,南北各三關,散見於紀、志、傳中者為《遼地附錄》二篇,《天祚播遷處考》、《西遼地考》各一篇,並附於書後。本書以《遼史》正文為本體,中加小字,詳為考證。丁謙《遼史各外國地理考證》1卷(浙江圖書館叢書第一集,1915 年),“就百官志中所標王府者,計四十余國為主,有遺采他條補之”。吳廷燮《遼方鎮年表》,為氏所著《歷代方鎮年表》之一卷。黃任恆《遼代年表》1卷(1915年),以遼為主,與“中國”(五代、宋)、西夏、高麗紀年相對照。譚其骧《遼史地理志補正》、《遼史訂補三種》(《浙江大學文學院集刊》第二集,1942年),後者包括“訂正皇子表”、“補皇子傳”、“訂正皇族表”三日。羅繼祖《遼漢臣世系年表》1卷(1937年)。作者因《遼史》中“漢臣有傳者僅二十余人,漏略滋多”,於是采摭有關史書、文集,編成此表,“凡得族三十有九,得姓二十有五”。張亮采《補遼史交聘表》5卷(有中華書局1958年本)。因《金史》有交聘表而《遼史》無之,作者乃“鉤核群籍,綴補阙遺,以備研史者考覽”。傅樂煥《宋遼聘使表稿》(《史語所集刊》14本,1949年;後收入《遼史叢考》,中華書局,1984年),主要據李焘《長編》,參照《遼史》、《宋會要》、《宋史》以及宋人筆記文集等,編成此表,並有“附考”及“ 使名索引”。王仁俊《遼史藝文志補證》1卷、黃任恆《補遼史藝文志》1卷等,是繼前人所作有關遼代藝文志的補殘綴拾之作。尤其是王仁俊《遼史藝文志補證》將以前諸家所有,悉皆標注,又補30余種,統加考證,並附“宋金人談遼事書目”及清人談遼書目凡26種,與以前同類補志相比最為完備。後收入《遼海叢書》第6集。陳漢章《遼史索隱》8卷(綴學堂叢書初集本,1936年;中華書局本,1960年),作者“采摭故典,探求異聞”,“探頤索隱”,將有關紀事系於《遼史》紀、志、傳文之下。此書重在考證地理。
《遼史》校勘成果可觀,是本時期遼史學取得進展的一個重要標志。《遼史》的缺略、訛誤勘稱二十四史之最。對於《遼史》的缺略,如前所述,從清代以來就不斷有學者為之拾補;而對其訛誤的校勘,到本世紀才有較大進展。主要有:馮家昇《遼史初校》。馮氏自1931年秋起,遍閱所能見到的《遼史》各種版本,凡23種,歷時2年,撰成《遼史初校》。以同文書局本為底本,以“百衲”、“南監”、北監 ”各本互校。此書後來收入《〈遼史〉誤證三種》(中華書局1959年)。羅繼祖《遼史校勘記》8卷。作者在序中指出,《遼史》“缪戾非偻指所可計”,撮其要者約為四端:一曰姓名之異,二曰名字互稱致稱歧誤,三曰記事矛盾,四曰疏漏。於是依清武英殿本,而參以元刊及明南北監本校之。此書撰成於1938年。 195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重版。張元濟《遼史校勘記》(稿本)也是這方面的重要著述。此外,馮家昇《〈遼史〉與〈金史〉〈新舊五代史〉互證舉例》(《史學年報》2卷1期,1934年;後收入《馮家昇論著輯粹》),傅樂煥《遼史復文舉例》(收入《遼史叢考》),也屬《遼史》校勘方面的著作。這些校勘成果,為後來中華書局出版的校點本所采用。
本時期,遼人著作輯錄有較大進展。光緒間,王仁俊輯《遼文萃》7卷。自序稱,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曾輯《遼史》14卷,未刊行,後見缪荃孫《遼文存》6卷,遂將缪氏已刊者悉予刪除。所收范圍,包括詩、诏冊、表、奏疏、上書、銘、序、書、文、碑碣、塔記、幢記等,凡105篇,編為5卷,另附“作者考”、“逸目考”各一卷。王氏在述例中稱有九不收,即史載诏書約文申義者,有史載表奏止錄大意者,有诏止二三語者,有佚句僅存者,有似文實為口說者,有文字太俚者,有記事太質者,有遼人使命為對偶文字者,有石刻太殘泐者,“凡屬此類,概從割愛”。這一原則不僅有悖廣泛搜求史料的宗旨,而且書中亦有“止二三語者”,是自亂其例。此書編成於光緒三十年十二月。收入《遼海叢書》第6集。
民國初年,黃任恆輯《遼文補錄》1卷。後來,黃氏將此書與《遼代紀年表》1卷、《補遼史藝文志》1卷、《遼代文學考》2卷、《遼代金石錄》4卷,合為《遼痕五種》(1925年)。羅福頤輯《遼文續拾》2卷、《遼文續拾補遺》1卷(1935)。金毓黻輯《遼陵石刻集錄》6卷。羅福頤輯《滿洲金石志》3卷(1937年)亦著錄有遼代石刻。
以上有關《遼史》考證、校勘和遼人著作輯錄等,均屬史料整理的范疇。
用近代史學方法研究遼史,是本時期遼史學取得重大進展的標志。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史學界出現了革新思潮。王國維是新史學方法的倡導者之一,主張結合近代西方學術方法發展出新史學方法。他的最大貢獻是“二重證據法”,即史學研究除了使用“紙上之材料”(文獻)外,還要重視“地下之新材料”(見《古史新證》第一章總論)。王國維利用新方法從事古史研究,涉及遼史者有《遼金時蒙古考》、《鞑靼考》、《西遼都城虎思斡耳朵考》等(均見《觀堂集林》),分別就遼金部族、西遼地理等問題作了探索。
馮家昇《〈遼史〉源流考》(收入《馮家昇論著輯萃》)論述歷代修遼史之經過和未成之原因,以及今本《遼史》史源。羅繼祖說,“全面研究《遼史》,並從校勘入手應該說馮書是第一部”(《〈遼史〉概述》,《社會科學輯刊》1979年第1期)。馮家昇還撰文多篇,主要有《太陽契丹考釋》(《史學年報》第3 期,1931年)、《契丹祀天之俗與其宗教神話風俗之關系》(《史學年報》第4期,1932年)、《契丹名號考釋》(《燕京學報》第13期,1933年)等,分別就契丹的信仰及契丹名號之起源、釋義等進行考證與論述。從中可以看出作者廣博的學識和深厚的功力。
傅樂煥《遼代四時捺缽考》(收入《遼史叢考》)是這個時期遼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它不僅對了解遼朝疆域和地理極有價值,並且揭示了遼朝制度的特色及其對後來金、元、清三代的影響。
陳述著《契丹史論證稿》(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1939年)是第一部從多方面研究契丹政治制度的專著。它論述了契丹民族之構成、選汗制度和帝位繼承、統治政策以及西遼的建立等遼朝政治史上的重要問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明確指出,“契丹為中華民族之一支,故契丹威名之廣溢,亦吾中華民族之光榮”。這一提法同那種視契丹等少數民族為“外族”、“異族”的傳統觀點相比是一大進步。日本學者鳥居龍藏評價該書說:“此書乃近代契丹史中之深具興味者,讀之對著者之高見不勝欽佩。此書乃莊重之出版品,系最有價值之一編政事史。”(《燕京學報》第40期)陳述在三四十年代,還發表論文多篇,研究范圍涉及契丹民族、政治、軍事等重大問題。
金毓黻著《東北通史》上編(三台東北大學,1941年),其中有“契丹之統一東北”、“東丹國及渤海遺族”和 “宋使入遼金之行程”3節述及遼史,有頗見功力的考證。金氏還撰有《宋遼金史》(商務印書館,1946年),凡第9章,其中有一半章節述及遼史。關於這兩部著作,以下詳述。
這個時期,還有一些散篇論文,就某個具體問題進行論述、考辨。如姚從吾《說阿保機時代的漢城》(《國學季刊》5卷 1期,1935年),指出“漢城”並非一個城市的名稱,而是由“漢人聚居的城寨”而得名;進而指出,凡兩種文化不同的民族,無論是語言不同,生活習慣不同,宗教不同,或者人種不同,互相接觸,都可發生“聚族別居”的現象。歐洲18世紀以前的猶太街、猶太城,美國城市內的唐人街,清代北京分內外城等都是如此。方壯猷《契丹民族考》(《北師大學術季刊》第2、3期)利用多學科知識對契丹國號、宮名、王號、官號、地名等作了考證。楊志玖《阿保機即位考辨》(《史語所集刊》17本,1948年)對史書中關於這個問題的不同記載予以辨析,判定契丹的分部和帝位推舉制不可靠。谷霁光《遼金糺軍史料試釋》(《史語所集刊》15本,1948年)、陳述《乣軍考釋初稿》(《史語所集刊》20本,1948年)是就乣軍問題同日人箭內亘所撰《遼金乣軍及金代兵制考》進行討論的文章,分別對“乣”的讀音、釋義、乣軍等作了考辨。劉銘恕對契丹習俗進行研究,撰《契丹民族喪葬制度之變遷及其特點》(《中國文化研究匯編》第1期,1941年)、《遼代之頭鵝宴與頭魚宴》(《中國文化研究匯刊》第7期)等。傅衣凌《遼代奴隸考》(《食貨半月刊》1卷2期)概括地考察了遼代奴隸的來源、種類、使用狀況、身分等。張亮采《遼代漢人樞密院之研究》(《東北集刊》第1期,1941年)論述遼代漢人樞密院建置和執掌,並據以試改《遼史·百官志》之南面官漢人樞密院條。
慶陵哀冊的發現,極大地推動了契丹字的識別與研究。遼代契丹人先後創制了契丹大小字,行於遼金,直至元初尚偶有使用,以後廢棄,也無契丹文書籍傳世。明清以來,陸續發現若干契丹文碑刻等,引起中外學者的興趣。1922年在遼慶陵中發現哀冊,1925年日本羽田亨推定慶陵哀冊與以往被認為是女真文的《大金皇弟都統郎君行記》同是契丹小字。羅福成等則認為慶陵哀冊文字為契丹大字。從30年代起,國內一些學者如羅福成、王靜如、厲鼎煃、羅福頤等,開始從事契丹字研究,其中以羅福成的成就最大,撰有《遼宣懿皇後哀冊釋文》(《滿洲學報》第2 期,1933年)等文。在當時資料有限又無其他輔助條件可供借鑒的情況下,竟然將遼帝廟號、年、月、日、干支和虛詞考證出來,而且多數正確無誤,可謂獨具契眼(見賈敬顏《契丹文》,載《中國民族古文字》,北京,1982年)。此外,還有柳翼謀《契丹大小字考》(《史地學報》2卷6期,1923年),孟森《遼碑九種》附跋尾(《國學季刊》3卷3期,1932年),厲鼎煃《熱河契丹國書碑考》(《國學季刊》3卷4期,1932年),王靜如《遼道宗及宣懿皇後契丹國字哀冊初釋》(《史語所集刊》3本4分,1933年)、《契丹國字再釋》(《史語所集刊》5本4分,1935年),李文信《契丹小字〈故太師銘石記〉之研究》(1942年),羅福頤《契丹國書管窺》(《燕京學報》第37期,1949年)等。其中羅福頤文較全面地敘述契丹大小字歷史,並匯錄了所能見到的契丹字,捨其重文,得1040余字,並據形分類,分別注其出處,為以後的契丹字研究提供了方便。
本時期對遼代文學也有研究。蘇雪林《遼金元文學》(商務印書館,1933年)、吳梅《遼金元文學史》(商務印書館,1934年),是最早的有關三代文學史的專書。論文有蘇雪林《遼文學概述》(《珞珈月刊》1卷1期,1933年)、顧敦鍒《遼文學》(《之江學報》1卷3期,1934年)等。此外,還有陳衍輯《遼詩紀事》(商務印書館)。
以上是20世紀上半葉的遼史研究,下面評述金史研究。
在敘述這個時期的金史研究之前,先對本世紀前的金中編纂與研究略作介紹。
金朝重視修史,設國史院,置監修國史、修國史、同修國史、編修官等職,還有記注院,掌修起居注。金朝官修國史有實錄、起居注等。私人著述有劉祁《歸潛志》,元好問《壬辰雜編》、《野史》等。元至正三年(1343年),脫脫為都總裁,主持修纂遼金宋三史,次年十一月修成《金史》,歷時不到二年。此次《金史》因有金朝實錄、劉祁和元好問書以及中統間王鹗所撰《金史》等為基礎,有良史之譽。趙翼說:“《金史》敘事最詳核,文筆亦老潔,迥出宋元二史之上 ”(《廿二史札記》卷二七“金史”)。
從元人修成《金史》至19世紀末的500年間,金史學大體與遼史相近。有明一代,僅有楊循吉撰《金小史》8卷(後收入《遼海叢書》,敘述金朝歷史發展大略。清朝乾嘉至19世紀末,相繼有關於《金史》考訂、補正、校勘和金代詩文輯錄等撰述問世。
(一)考訂補正。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十駕齋養新錄》,趙翼《廿二史札記》、《陔余叢考》等都有對《金史》的考訂。《金史》補正之作,有萬斯同《金諸帝系統圖》、《金將相大臣年表》、《金衍慶宮功臣表》,黃大華《金宰輔年表》,錢大昕《宋遼金元四史朔閏考》,倪燦、盧文弨《補遼金元藝文志》,金門诏《補三史藝文志》等。此外,杭世駿曾仿厲鹗《遼史拾遺》例撰《金史補》,惜未能成書(參見金毓黻《中國史學史》第172頁,商務印書館,1957年)。
(二)校勘。施國祁《金史詳校》10卷(會稽章氏刊本,1880年)是這方面的力著。施氏稱,雖然《金史》“文筆甚簡,非《宋史》之繁蕪;載述稍備,非《遼史》之阙略;敘次得實,非《元史》之訛謬”,但是仍有許多不足,於是以20余年之力,讀凡十余過,為之“辨體裁,考事實,訂字句”,共得4000余條。因其卷帙繁多,乃列舉條目,為《金源札記》(有“叢書集成初編”本)。梁啟超說,清儒“治金史者莫勤於施北研(國祁)之《金史詳校》十卷”(《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294頁)。
(三)紀事本末體編纂。李有棠撰《金史紀事本末》52卷。體例與《遼史紀事本末》相同,征引書目達500多種,對史實、人名異同、地理沿革等多所考訂,足資參考。
(四)詩文輯錄。最早對金詩進行全面搜集整理者應屬金末元好問,編有金源詩歌總集《中州集》10卷,共收詩1980首,作者240余人。附《中州樂府》 1卷,收詞115首,作者36人。每人各系小傳,述其轶事。“好問之意,在於借詩以存史,故於詩不甚求全,未能赅備。”(《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而且《中州集》不收時人作品,因此金末許多詩作未能收入此集。清初郭元釪在《中州集》基礎上,增補元好問、劉祁等人的詩作,並從“天下郡縣志中采輯遺逸”,還將“金人入元不仕者”一並收入。郭元釪稿本上呈後,康熙帝“遂命更加搜輯,凡金人集之斷簡殘篇有可存者皆令附以入,及山經地志川澤之紀聞,綴摭荟叢,巨細不遺”(《聖祖仁皇帝御制全金詩序》,“四庫全書”本),名為《全金詩增補中州集》,凡74卷。據統計實收358人,詩5544首(見薛瑞兆、郭明志編纂《全金詩》,南開大學出版社,1995年)。
清莊仲方輯《金文雅》16卷,應是流傳下來的最早的金代文總集。早在金末元好問編纂《中州集》時,有馮清甫輯金文至百余卷,惜竟不傳。莊仲方從金人諸文集、《中州集》和《金史》、《元文類》、《玉堂嘉話》以及其他地志等輯出詩文,按賦、詩、诏令、奏疏、墓碑等文體分類編排,附有作者考略,書前有編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序,稱所收詩文,經“文搜嚴遴,汰其粗率,取其雅馴”,因名《金文雅》。通行本有光緒辛卯(十七年,1891年)七月江蘇書局重刊本。
張金吾編《金文最》120卷,所收金文遠遠超過《金文雅》,是金文輯錄之集大成者。《金文最》成書過程和版本比較復雜。編者廣搜博采,除專集外,如《金史》、《大金集禮》、《大金吊伐錄》、《三朝北盟會編》等書,暨地志、金石、醫書、譜錄,乃至外國之書,“無不甄錄”。積12年之工,三易其稿,於道光二年(1822年)編成此書。按文體編排,不收歌詩。《金文最》編成後久未刊行,至光緒八年(1882年)始有粵雅堂本。通行本為光緒乙未(二十一年,1895年)蘇州書局60卷本,刪去了《金文雅》已著錄者,只存篇目。《金文最》收羅廣泛,是金史研究者的必備之書。
從上可見,本世紀以前的金史學尚停留在史料編纂整理、考訂補遺及遺文輯錄階段上。
20世紀上半葉,在史料整理、考訂補遺方面繼續有所進展,與此同時也出現了用近代史學方法研究金史的論著。
先說史料整理、考訂補遺。有吳廷燮《金方鎮年表》,為氏所撰《歷代方鎮年表》之一卷(後收入《二十五史補編》)。陳述《金史氏族表初稿》(《史語所集刊》5本3分,1935年),譜列金源族姓和人物。此前,《續通考·氏族略》曾錄遼金元姓氏,阿桂等撰《金史姓氏考》,均未系人物,只列姓氏,且有訛漏。此稿搜集遼金元史和當時碑志、詩文等史料中有關金代氏族的史實,按族系譜,是研究金史的重要工具書。還有朱希祖《偽楚錄輯補》、《偽齊錄校證》和毛汶《南遷錄糾缪》(《國學論衡》第5期,1935年)以及馮家昇《〈遼史〉與〈金史〉〈新舊五代史〉互證舉例》等。在這方面值得重視者還有陳樂素《三朝北盟會編考》(《史語所集刊》6本2分、3分,1936年),洋洋15萬言,分撰者、內容、全書引用書目、《宣和乙巳奉使行程錄》、宋金史帝紀會編舉異等10個部分,進行考證,是一部網羅宏富、考訂詳實、為史家所公認的力作,迄今國內外研治或評價《三朝北盟會編》者“莫不資藉於此”(見徐規為陳樂素《求是集》所撰序言,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年)。
再說專題研究。
歷史地理與民族。有王國維《金界壕考》、《遼金時蒙古考》等,朱希祖《完顏姓氏考》(《文學史研究所月刊》2卷3期,1934年),宋文炳《女真漢化考略》(《海天》1卷2期,1934年),陳述《契丹女真漢姓考》(《東北集刊》第2期,1941年)等。
女真文字。關於女真文字的記述,最早見於宋周密《癸辛雜識》,稱汴梁“有大金登科題名,女真進士題名,其字類漢篆而不可識”。清人劉師陸於19世紀30 年代撰《女直字碑考》、《女直字碑續考》(後收入《考古社刊》第5期,1936年),可謂女真文字研究的開拓者。此後,國外有學者陸續撰文,研究女真文字。至20世紀三四十年代,羅福成、毛汶、王靜如、柳翼謀、卞宗孟、羅福頤、金梁、羅繼祖、金毓黻等,相繼關注女真文字研究。其中以羅福成的成就最大,撰《宴台金源國書碑考》(《國學季刊》1卷4期,1923年)、《宴台金源國書碑釋文》(《考古》第5期,1923年)、《女真國書碑考釋》(《支那學》5 卷4號,1929年)、《女真國書碑跋尾》(《北平國立圖書館月刊》3卷4號,1929年)、《女真國書碑摩崖》(《東北叢镌》第5期,1930年)、《金泰和題名殘石(釋文)》(《東北叢镌》第17期,1931年)、《〈華夷譯語〉中女真語音義》(《國學季刊》1卷4號,1932年)、《明努兒干永寧寺碑女真國書圖釋》(《滿洲學報》第5輯,1937年)等,分別對傳世女真文刻石及《華夷譯語》中的女真字予以著錄、考釋、擬定音義。王靜如《宴台女真文進士題名碑初釋》(《史學集刊》第3期,1937年),對羅福成《宴台金源國書碑考》所釋文字又有所增益。
宋金關系與宗教。本時期這兩方面研究取得的進展,是同當時特定的歷史背景相聯系的。三四十年代,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一些愛國學者以古況今,把歷史上宋金戰爭與當時的戰爭相比附,這是當時關注宋金關系研究的重要原因及特點。如陳樂素《宋徽宗謀復燕雲之失敗》(《輔仁學志》4卷1期,1933年)、缪鳳林《宋高宗與女真議和論》(《國風》8卷2期,1936年)、翦伯贊《兩宋時代漢奸及傀儡組織》(《中蘇文化》6卷2期,1940年)、聶崇歧《北宋——中國政治史上南北勢力消長之關鍵》(《大中》1卷6期,1946年)等。這些文章雖多系有感而發,但其中亦有頗具學術價值者,陳樂素文即是宋金關系史研究的力作。陳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也是在上述背景下撰寫出版的重要著作。書中所述全真、大道、太一三教,本金元時事,作者說,之所以系之南宋初,是因“三教祖皆生於北宋,而創教於宋南渡後,義不仕金,系之以宋,從其志也”。顯然,這也是同作者堅定地反對日本侵略的愛國精神和民族氣節相一致的。不過,今天我們仍將新道教作為金代宗教看待。本書對三教之起源、發展及活動情況,根據散見於碑刻和諸家文集資料,加以考論,是研究金元道教的重要著作。當時孫楷第評論此書說,“三道教有史,自先生始”。並稱是書有不可及者三,“一曰真積力久,二曰心解神契,三曰诠敘有方”。“然余尤服先生議論之正也。真積力久是學,心解神契是識,诠敘有方是才,議論之正則是德也。”(1947年2月15日天津《大公報》)這一評論是中肯的。此外,還有姚從吾《金元全真教的民族思想與救亡思想》(《治史雜志》第2期,1939年)等。
斷代史編撰。前面談到的金毓黻撰《東北通史》(三台東北大學,1941年)和《宋遼金史》(商務印書館,1946年)是論及金史的地方史和斷代史的重要著作。作者編印《東北通史》的緣起,是因他流寓四川時對故土的懷念及對日本侵略者的仇恨,而將舊稿整理出版。此書有4節敘述金史,即“女真之興”、“女真之經略東北”、“宋使入遼金之行程錄”、“蒲鮮萬奴之東夏國”。書中對史事和地理沿革考證較詳。它與略早於此書的傅斯年著《東北史綱》同為我國東北地方史研究的奠基之作。《宋遼金史》全書9章,有5章敘及金史。在宋遼金史地位問題上,金氏提出“三史兼治 ”,摒棄以宋為正統,“斥遼金史為不足觀”的“偏狹之見”,主張三史並重;在治本期史方法上,提倡“三史互證”。這些見解,至今仍值得治宋遼金史者重視。
二、20世紀下半葉的遼史研究
本世紀下半葉,遼史研究取得長足進展。無論是專題研究與斷代史編撰,還是文獻整理與考訂,都有許多成果問世。其數量超過以往任何時期,其范圍幾乎涉及各個領域,至於文物考古的收獲更令人矚目。
遼朝斷代史著作(含通史著作中以較多篇幅和設專章敘述遼史者)主要有蔡美彪等《中國通史》第6冊(人民出版社,1979年),分3章敘述遼、西夏、金三朝歷史。這是通史著作中最早以較多篇幅(約8萬字)把遼朝作為一個斷代進行完整敘述的。張正明著《契丹史略》(中華書局,1979年),作者在“後記 ”(1978年)中說,是書完成於15年前。“引言”說,本書試圖對契丹社會制度——主要是遼代契丹的社會制度作初步的探討。“談談契丹的勃興,遼朝的創立、發展、衰敗和滅亡,遼與五代、北宋的關系,金、元兩代的契丹,以及其他密切相關的問題。”實際上,此書還涉及遼代社會經濟、政治制度,乃至科學文化、民族關系等,可視為第一部簡明遼朝斷代史。楊樹森《遼史簡編》(遼寧人民出版社,1984年)和舒焚《遼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是兩部通行的遼朝斷代史。前者較為簡明;後者資料翔實,但大段引文過多,閱讀起來難免沉悶,文化部分比重嫌輕。兩書對考古材料利用較少。此外還有《中華文明史》遼宋夏金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遼代部分主要執筆者有韓志遠、王宏治、劉慶、宋德金等。李桂芝撰有《遼金簡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有關遼代的其他專門史著作,將於以下各相關部分介紹。
(一)社會性質與經濟
關於遼朝社會經濟方面的專著有陳述《契丹社會經濟史稿》(三聯書店,1963年),該書由5篇文章組成,主要討論契丹國家的性質、社會經濟結構和階級問題。這是作者運用唯物史觀研究契丹社會經濟的重要成果,是遼代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拓荒之作。葛金芳《宋遼夏金經濟研析》(武漢出版社,1991年),作者稱本書是把宋遼夏金時期經濟運動視作一個整體來考察的。這一宗旨是可取的。漆俠、喬幼梅《遼夏金經濟史》(河北大學出版社,1994年),全書分3篇22章,第一編共9章,為“契丹遼國經濟史 ”。這是一部對整個遼夏金時期中國北方經濟進行全面深入研究之作,提出許多新見。
關於社會性質。這是五六十年代遼史研究中頗受關注和分歧較大的一個問題。有以下幾種說法:
1.認為契丹由原始公社制直接過渡到封建制。尚钺說,阿保機建國前契丹社會處在氏族家長制階段,由於阿保機接受漢族文化,加速了由氏族家長制向封建化飛躍發展的過程(《中國歷史綱要》,人民出版社,1954年)。張正明也持此說(見《契丹史略》第一、四章)。張廣志認為“奴隸制在遼代的任何時期,在遼境的任何地區,都不曾成為占主導地位的剝削方式,遼代奴隸社會論殆難成說”(《奴隸社會並非人類歷史發展必經階段研究》第300元,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李錫厚指出,契丹人立國前後還處在氏族社會末期階段,阿保機時代的契丹王朝仍然是一個徒有王朝之名的部落聯盟。隨著頭下、漢城的大量出現,標志著封建土地私有制已經逐步確立起來,隨之而來的則是導致契丹氏族、部落內部出現了剝削階級,擁有頭下、漢城的契丹權貴成了封建主(《遼金時期契丹及女真族社會性質的演變》,《歷史研究》1994年第5期)。
2.認為阿保機稱帝前契丹的部落大酋長民主推選制早已破壞,國家制度的萌芽早已在發展著,到阿保機時代正式建立起半漢化的封建國家制度。華山持此說(《阿保機建國前契丹社會試探》,《宋史論集》,齊魯書社,1982年)。
3.認為契丹是以奴隸占有制為基礎的各部落聯合。陳述說,就全國范圍看,契丹的社會形態是復雜的,還沒有完成統一的經濟基礎。南部農區封建經濟帶動著全國,北境部族的內部一般還處在氏族階段。在封建經濟發生發展的同時,契丹的家庭奴隸制形式仍然存在。國內主要部分向封建制過渡雖接近完成,有的甚至剛剛起步,這一軍事政治的聯合體便瓦解了(《契丹社會經濟史稿》第28、44頁)。
4.認為阿保機政權是在部落制度基礎上建立的奴隸主的國家。趙衛邦說,契丹國家是在部落制度的廢墟上形成的。從契丹的整個歷史發展看,契丹奴隸占有制沒有超出早期階段。盡管奴隸制的發展曾有超出父權奴隸制的傾向,但在外來影響下,奴隸占有制的貴族轉變為形成中的封建土地所有者(《契丹國家的形成》,《四川大學學報》1958年第2期)。蔡美彪說,遼朝大約在景宗到聖宗時期由奴隸制過渡到封建制(《契丹的部落組織和國家的產生》,《歷史研究》1964年第5-6期)。
5.認為阿保機建國前契丹已進入奴隸制社會,而且已經包容了奴隸制和封建制兩種經濟成分。至聖宗時,具體地說是在澶淵之盟以後,是奴隸制衰落、封建制興盛的關節線,封建制因素超過了奴隸制而居主導地位。漆俠持此說(《遼夏金經濟史》第4、180頁。)
關於階級結構。陳述說,契丹皇室、諸王、貴戚以及宰相節度使等世官和漢、渤海人中的上層、地主等構成汗國的統治剝削階級,以大汗(皇帝)為首的契丹貴族是這個階級的核心;國內的宮戶、部曲、農奴、部民和領屬人民,屬於被統治階級,奴隸是其中最低的一層(《契丹社會經濟史稿》第45頁)。楊樹森持類似觀點(《遼史簡編》第138頁)。張正明則認為,遼朝全體臣民的社會身分和法律地位分為三類,即貴族,平民(庶民),賤民(奴婢)。這是等級,它與階級不完全吻合,但大體上是一致的。其中平民的分化比較駁雜,包容著從地主一直到有上中下三等及自耕、佃耕等區別的農奴民(《契丹史略》第99頁)。
一些論者對宮戶、頭下戶、蕃漢轉戶等展開討論。
1.論為宮戶、頭下戶是封建制度下的農奴。張正明說,宮戶(亦稱宮分戶)分正戶和蕃漢轉戶,都是皇室的農奴以及地位與農奴無異的牧民、獵民和工匠(《契丹史略》第105頁)。費國慶也認為斡魯朵戶與頭下戶是農奴(《遼代斡魯朵探索》,《歷史學》1979年第3期;《遼代的頭下軍州》,《曲阜師范學院學報》1963年第1期)。
2.認為宮戶和頭下戶是奴隸制下的奴隸戶。陳述說,雖然頭下軍州和斡魯朵領地的俘戶們仍過自己的家庭生活,單身的也“使各有配偶”,但並沒有擺脫奴主關系,他們仍是奴隸(《契丹社會經濟史稿》第19、20頁)。
3.認為隸屬於斡魯朵(宮衛)的州縣並非宮分戶。楊若薇說,隸屬於斡魯朵的州縣並非由私城而來,隸屬於斡魯朵的州縣戶與宮分戶是迥然不同的。隸屬宮州縣的民戶與斡魯朵沒有身分上的隸屬關系。斡魯朵擁有扈從皇帝的宮分戶、州縣民戶和介於宮分戶與州縣民戶之間的蕃漢轉戶。因此,說這些州縣和人戶是“皇室領地 ”,是一種誤解(《契丹王朝政治軍事制度研究》第一編“斡魯朵制度”,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
4.認為在斡魯朵經濟實體中,既有奴隸制,又有封建制因素。漆俠說,斡魯朵(宮分)是由契丹正戶和蕃漢轉戶組成的。契丹正戶中一部分“上戶”,具有奴隸主的身分;一部分則是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斡魯朵戶中,還包括奴隸。至於蕃漢轉戶是具有封建因素的農奴(漆俠等《遼夏金經濟史》第134-139頁)。
關於各業經濟的發展。陳述、張正明、楊樹森、舒焚、漆俠等書中都對遼朝各經濟門類的發展狀況作了敘述。此外,還有一些專題史和散篇論文論述這方面的問題。王育民《中國人口史》(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五章第六節為“遼代人口”。考察了遼朝各類人口,估計總數不會少於150萬戶,以每戶平均6口計算,約900 萬人,較《遼史·地理志》的記載增加2倍多。李俠、曉峰《中國北方民族貨幣史》(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二章為“遼(契丹)貨幣”,第三章為“ 西遼,喀喇汗(黑汗回鹘)王朝貨幣”。還有周錦章《遼代貨幣制度管見》(《昭烏達蒙族師專學報》1987年第1期)、田廣林《遼代貨幣經濟述略》(《昭烏達蒙族師專學報》1987年第2期)等。
(二)政治與制度
關於遼朝政治與制度研究的專著有:陳述《契丹政治史稿》(人民出版社,1986年),此書系據《契丹史論證稿》修改增補而成。原第一篇“亞洲之游牧民族”改為“契丹在祖國歷史中的地位”,又增加一篇“遼廷瓦解以後的契丹人”。楊若薇《契丹王朝政治軍事制度研究》,分“斡魯朵制度”、“官制及行政制度”、“軍事制度”三篇。鄧廣銘在序言中稱贊作者“勇於去開拓前人不曾墾辟過的領域,也敢於對前此似乎已成定論的問題,或者已由富權威性的學者所做出的結論提出懷疑”。李錫厚、白濱《中國政治制度通史》遼金西夏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比較系統地論述了遼朝政治制度。“前言”說,這套通史的“學術思想體系和總體結構的設計,旨在突出對歷代的皇帝制度、中央決策體制及政體運行機制的探索”,力求“貼近政治學的規范”。遼代部分也體現了這一宗旨。本部分不囿陳說,有所創新,表明遼朝政治制度史研究取得進展。對於本書的某些觀點,容或尚有不同看法,這是學術研究的應有之義。李錫厚還撰有《中國封建王朝興亡史》遼金卷(廣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以下就遼朝政治與制度研究中涉及較多的問題略作介紹。
1.皇位繼承、國體政體。漆俠《契丹遼國建國初期的皇位繼承問題》(《河北師院學報》1989年第3期)論述契丹遼國初期皇位從兄終弟及制到父死子繼制的演變及其根源。《從對〈遼史〉列傳的分析看遼國家體制》(《歷史研究》1994年第1期)論述了遼國的國體與政體。蔡美彪《遼代後族與遼季後妃三案》(《歷史研究》1994年第2期)指出遼朝衰亡非由宗室與外威、帝黨與後黨之爭,而是由於後家兩大族的爭奪。此外,還有任愛君《阿保機時期契丹國家的歷史特點》(《昭烏達蒙族師專學報》1991年第1期)、《應當重新認識契丹遼朝的“一國兩制”》(《昭烏達蒙族師專學報》1992年第2期)等。
2.職官。關於遼朝職官制度,六七十年代日本學者島田正郎發表系列文章,有《遼朝北面中央官制的特色》、《遼朝監察官考》、《遼朝林牙、翰林考》、《遼朝鞫獄官考》、《遼朝於越考》、《遼朝宰相考》、《遼朝惕隱考》等(見楊家駱主編《遼史匯編》第9冊,鼎文書局,1973年)。我國學者對遼朝職官的研究,唐統天用力較勤,發表文章多篇,有《契丹“於越”考——兼與島田正郎及威特夫先生商榷》(《東北地方史研究》1988年第1期)、《遼代漢官散階制》(《社會科學輯刊》1988年第3期)、《關於契丹北、南宰相府的幾個問題》(《民族研究》1988年第5期)、《遼代鞫獄官機構研究》(《遼金史論集》第4輯)、《遼代宰相制度的研究》(《東北地方史研究》1992年第1期)等。何天明撰《遼代翰林院探討》(《內蒙古大學學報》1991年第2期)、《遼代中書省若干問題探討》(《內蒙古師大學報》1992年第2期),指出以往有關這兩個官署“虛設”之說不完全符合歷史實際,或根本不能成立。他還撰有《試探遼代的北面朝官》(《昭烏達蒙族師專學報》1992年增刊)、《遼代契丹北樞密院的設立、職官設置及其特色》(《社會科學輯刊》1995年第3 期)。王曾瑜《遼朝官員的實職和虛銜初探》(《文史》第34輯)除據傳世很少的遼朝史料外,還以五代、宋、金等官制作參照並進行比較,探討了這個問題。此外,上述楊若薇《契丹王朝政治軍事制度研究》和李錫厚《中國政治制度通史》遼代部分等也都用較多篇幅探討遼朝官制。
3.科舉。朱子方、黃鳳岐《遼代科舉制度述略》(《遼金史論集》第3輯),朱子方《遼代進士題名錄》(《黑龍江文物叢刊》1983年第4期)、楊若薇《遼朝科舉制度的幾個問題》(《史學月刊》1989年第2期)、都興智《有關遼代科舉的幾個問題》(《北方文物》1991年第2期),分別就遼代初開貢舉年代、考試科目等問題進行論述。
4.法制。嵇訓傑撰有《遼代刑法概述》(《民族研究》1982年第1期)。陳述《遼代(契丹)刑法史論證》(《遼金史論集》第2輯)認為,有遼一代由於農耕與游牧社會的不同,以及社會發展的不一致,致使法律未能擺脫二元。
5.軍事。劉慶、毛元佑《中國宋遼金夏軍事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就這個時期的軍事制度、戰爭、武器裝備和國防設施、兵學等問題作了論述。還有王曾瑜《試論遼朝軍隊的征集和編組系統》(《中華文史論叢》1986年第4輯)等。
(三)社會生活與文化
1.社會生活與禮制
關於遼代社會生活研究,張國慶用力最勤,發表論文多篇,並在此基礎上撰成《遼代契丹習俗史》(遼寧民族出版社,1997年),全面敘述遼代契丹人習俗並揭示出構成這些習俗的文化淵源,展示了這些習俗在中國古代少數民族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有關遼代社會生活研究的論文很多,如朱子方《從出土墓志看遼代社會》(《社會科學輯刊》1979年第2期)、佟柱臣《遼墓畫反映的契丹人生活》(《遼金史論集》第5輯)、陳述《圍繞寺廟的邑、會、社——我國歷史上的一種民間組織》(《北方文物》1985年第1期)、武玉環《試論遼代婦女崇佛》(《遼金史論集》第5輯)、《略論契丹人的衣食住行》(《北方文物》1991 年第3期)、宋德金《遼金婦女的社會地位》(《中國史研究》1995年第3期)、金啟孮《中國式摔跤源出契丹、蒙古考》(《中國蒙古史學會成立大會紀念集刊》,1979年)、景愛《契丹遺風述略》(《遼金西夏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等。
禮制也是受到關注的課題。朱子方《遼代的柴冊禮》(《社會科學輯刊》1985年第1期),謂柴冊禮本是契丹舊俗推選大汗的遺跡,但是隨著封建進程的深入,逐漸變成了象征性的儀式。朱氏還撰有《遼代復誕禮管窺》(《遼金史論集》第1輯)、《遼朝契丹統治者的宗廟制度》(《中國民族史研究》第4輯,改革出版社,1992年)等。陳述《談遼金元“燒飯”之俗》(《歷史研究》1980年第5期)、賈敬顏《“燒飯”之俗小議》(《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2年第1期)、宋德金《“燒飯”瑣議》(《中國史研究》1983年第2期)、王承禮《契丹的瑟瑟儀和射柳》(《民族研究》1988年第3期)、《契丹祭黑山的考察》(《社會科學戰線》 1990年第2期)、舒焚《遼帝的柴冊儀》(《遼金史論集》第4輯)、李逸友《遼代契丹人墓葬制度概說》(《內蒙古東部區考古學文化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1991年)、田廣林《契丹葬俗研究》(《北方民族文化》,1992年)、《契丹祭祖禮俗研究》(《北方民族文化》增刊,1993年)等。
2.文化
張碧波、董國堯主編《中國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民族文化卷(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設“契丹文化(附奚族文化)”一章,由馮繼欽、黃鳳岐、孟廣耀、杜承武執筆。前三位作者另撰《契丹族文化史》(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他們分別曾就有關專題發表過多篇論文,在此基礎上加以綜合提高,因而使本書的深度和廣度有了保證。馬赫《遼代文化與“華夷同風”》(《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孟廣耀《試論遼代漢族儒士的“華夷之辨”觀念》(《北方文物》1990年第4期)分別論述遼文化特點和歷史地位及遼代華夷之辨觀念淡化和消失過程。宋德金《遼朝正統觀念的形成與發展》(《傳統文化與現代化》 1996年第1期)認為,通過對這一問題的考察,充分反映了契丹對我國傳統文化的借鑒和吸收。任愛君《契丹遼朝文化總體整合說》(《昭烏達蒙族師專學報》 1991年增刊)分析了契丹文化的發展脈絡。
以下介紹關於遼代文化研究中涉及較多的問題。
宗教。朱子方撰文多篇,有《遼代的薩滿教》(《社會科學輯刊》1986年第6期)、《遼代佛教的主要宗派和學僧》(《世界宗教研究》1990年第1期)、《遼代佛教著作譯考》(《遼金史論集》第2輯)等。游俠《遼代佛教》(《中國佛教》之一節,知識出版社,1980年)、黃震雲《遼代的宗教文化》(《民族研究》1996年第2、3期)。
文學。向來比較沉寂的近代文學研究取得進展。周惠泉、米治國《遼金文學作品選》(時代文學出版社,1986年)分詩、民歌、樂府、散文四目選錄30多首(篇),作了注釋,並附作者小傳。蔣祖怡、張滌雲整理《全遼詩話》(岳麓書社,1992年)是對清人周春《增訂全遼詩話》二卷本的增補本。本書包括對周春《增訂全遼詩話》的校點、箋注及整理者《新補遼詩話》,其篇幅較周書大為增加。此書在補遺、糾缪、考訂上做了大量工作,征引書目達436種,不僅為研究遼代文學提供了豐贍的資料,而且對研究遼代社會生活也有裨益。張晶《遼金詩史》(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是遼金文學研究的重要著作。張松如在序中高度評價此書,稱“論點明晰,邏輯嚴謹,資料詳實,斷案公允”。作者著意從遼金兩代的文化環境來說明遼金詩歌的特質,這是本書的一個重要特點。全書37萬字。如果減少一些鋪陳和枝蔓,會更精當。張松如主編《遼金元詩歌史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論及遼詩。散篇論文有米治國《遼代文學初論》(《社會科學戰線》1985年第2期)、舒焚《古典通俗文學中的遼朝》(《遼金史論集》第2輯)等。
史學。有楊樹森《遼代史學述略》(《遼金史論集》第2輯)、吳懷祺《遼文化中的史學價值再認識》(《遼金西夏史研究》)等。
語言文字。關於契丹字研究,本時期取得重大進展。從20年代至50年代,陸續出土了兩種不同形式的契丹文石刻,為識別契丹大小字提供了條件。一種意見認為慶陵哀冊文字為大字,蕭孝忠墓志為小字。閻萬章《錦西西孤山出土契丹文墓志研究》(《考古學報》1957年第2期)主張此說。另一種意見則相反。金光平、曾毅公《錦西西孤山契丹文墓志試釋》(附上引閻萬章文之後)斷定蕭墓志為大字,慶陵哀冊為小字。厲鼎煃、王靜如、劉鳳翥、陳述等支持此說,為目前通行說法。關於契丹字淵源,有源於突厥文、回鹘文及漢字三說。關於契丹小字的解讀,近20年來取得突破性進展。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清格爾泰、劉鳳翥、陳乃雄、於寶林、邢茀裡的《關於契丹小字研究》(《內蒙古大學學報》1977年第4期)。他們總結了半個多世紀以來國內外關於契丹小字的研究狀況,確定377個原字標准形,合並異體字後,約為350個,還把他們認為以前國內外學者擬對或接近擬對的原字數從32個增加到130多個,占原字總數三分之一強,把前人釋對的不到百條語詞,提高到400多條,還分析了幾十個語法成分,找出契丹語的元音和諧律,標志我國契丹字研究取得了重大進展。此文後經修訂,定名為《契丹小字研究》,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1985年)。除上述作者外,賈敬顏、黃振華、沈匯、巴圖等也有契丹字研究文章發表。
(四)民族、民族關系、遼宋關系
本時期民族史研究活躍,中國民族史與區域民族史專著相當之多,其中述及契丹民族及民族關系、遼宋關系者,有翁獨健主編《中國民族關系史綱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王锺翰主編《中國民族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干志耿、孫秀仁著《黑龍江古代民族史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孫進己《東北各民族文化交流史》(春風文藝出版社,1992年)、張碧波、董國堯主編《中國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民族文化卷(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等。
1.民族
趙光遠《試論契丹族的青牛白馬傳說》(《北方文物》1987年第2期)分析了青牛白馬傳說與契丹族歷史的關系。王禹浪《契丹稱號的含義與民族精神》(《中國北方古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文史出版社,1995年)、嵇訓傑《關於契丹名稱、部落組織和源流的若干問題》(《中國史研究》1985年第2期)分別就契丹稱號、契丹與其他族同化等問題進行探討。陳述《阿保機營建四樓說證誤》(收入《契丹社會經濟史稿》),王樹民《略論契丹建國初期營建的四樓》)(《文史》第16輯),任愛君《契丹四樓名號考述》(《昭烏達蒙族師專學報》1989年第3期)、《契丹四樓源流說》(《歷史研究》1996年第6期)等文,分別就其釋義、本源及對契丹歷史發展產生的重大影響等進行考述和探討。周建奇《遼代契丹半丁零——〈遼史〉中的迪辇為高車丁零異譯補證》(《內蒙古大學學報》1993年第3期)指出,遼代契丹的一些部族和姓氏名稱、人名與南北朝時期一些部族姓氏名稱有某種同源關系。趙振績《契丹捺缽文化的涵義》(《中國北方古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認為捺缽文化是動態文化,斡魯朵文化是靜態文化,二者互為因果,不是二元之文化,而是一而二、二而一之文化。陳述《大遼瓦解以後的契丹人》(《中國民族問題研究集刊》第5 期,1956年)探討了遼亡後契丹人的去向,指出很多契丹人在不同時期、不同條件下分別融合於漢人、蒙古人、回鹘(維吾爾)人、女真(滿)人、朝鮮人。而直接承襲契丹人的部分,是現在的達呼爾(達斡爾)。近年又傳出一個饒有興趣的消息,在雲南契丹發現了契丹人的後裔。達斡爾族學者孟志東(莫日根迪)經過數年實地調查,撰成《雲南契丹後裔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根據歷史文獻、族譜、碑文、傳說、語言文字等,綜合考察了元朝落籍雲南契丹將士後裔的歷史和現狀。這一成果的問世引起民族史界的極大興趣,並將推動契丹史的研究。
2.民族關系,遼與五代、北宋關系
如何評價遼宋、金宋關系,是50年代以來關於我國歷史上民族關系大討論中經常涉及的問題。對遼金在當時是中國還是外國的問題有兩種相反的意見。一種意見認為,契丹女真在當時是國內民族,遼金屬於中國。另一種意見認為,契丹、女真在當時是外族,遼金不是“中國”而是外國。與此相關聯,在遼金與兩宋戰爭的性質問題上存在三種意見。一是認為遼金與兩宋的戰爭是侵略與反侵略的戰爭,是外族、外國對中國的侵略。二是認為遼金與兩宋的戰爭是國內戰爭,不帶有侵略與反侵略的性質,只有反動與進步,非正義與正義之分。三是認為遼金與兩宋在當時作為敵對的民族與國家,經常進行戰爭,今天看來是兄弟阋於牆,家裡打架。女真滅北宋是合乎規律的事情,本身是一件好事。經過討論,已經很少有支持第一種意見者。
關於遼宋澶淵之盟,長期流行的觀點,認為當時在宋朝本可獲勝和收復燕雲的情況下,卻訂了一個投降的和約,對北宋來說是屈辱的結局。金石《重評“澶淵之盟”》(《民族研究》1981年第2期)認為,上述觀點不符合我國多民族自古以來共同締造祖國歷史的事實,也不能正確反映歷史上民族斗爭與民族關系的本質。澶淵之盟溝通了宋遼雙方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對當時的社會發展起了積極作用,應予肯定。李一氓《讀〈遼史〉——兼評〈四郎探母〉》(《文藝研究》1981年第4期)也支持這一觀點。漆俠《宋太宗雍熙北伐》一文(《河北學刊》1992年第2期)則認為,不管怎麼說,澶淵之盟對宋封建統治者來說也是一個城下之盟。
有關民族關系的論文,還有岑家梧《遼代契丹和漢族及其他民族的經濟文化聯系》(《歷史研究》1981年第1期)、任崇岳《略論遼朝與五代的關系》(《社會科學輯刊》1984年第4期)、孟古托力《宋遼“南北朝”說考論》(《學習與探索》1990年第3期)等。
(五)人物
關於人物研究的論著,李錫厚《耶律阿保機傳》(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是一本比較詳細的阿保機傳。羅繼祖《遼承天後與韓德讓》(《吉林大學人文科學學報》1962年第3期),最早從正面肯定承天後(蕭綽)與韓德讓的歷史功績。論述蕭綽的論文還有尹承琳、許曉秋《蕭綽評述》(《遼金史論集》第2 輯)、田禾《蕭綽與遼朝中興》(《社會科學戰線》1987年第3期)等。
(六)歷史地理與文物考古
關於遼朝歷史地理,歷來是受學者關注的課題,本世紀初有楊守敬《中國古代輿地圖》,其中包括《遼地理圖》。此後,劉師培、譚其骧、馮家昇、丁謙、傅樂煥、朱希祖等都有關涉遼朝地理考證之作。
本世紀下半葉,譚其骧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為中國歷史地圖史上的空前巨著。其中第6冊為宋遼金時期(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年)。參與此圖編撰的中央民族學院編輯組編輯出版了《〈中國歷史地圖集〉東北地區資料匯編》,後來公開發行,改名為《中國歷史地圖集釋文匯編·東北卷》(中國民族學院出版社,1988年)。郭毅生對《中國歷史地圖集》東北邊疆各圖花了大量精力進行編制和審定(見羅爾綱為郭毅生《山海集》所作序言),並撰《遼代通州與安州城址考實》(《山海集》,中國地圖出版社,1996年)等。李健才對東北及遼金地理研究用力甚勤,有《遼代寧江州考》、《續考》、《遼代賓、祥、益、威四州考》等,均收入氏所著《東北歷史地理考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張博泉、蘇金源、董玉瑛撰《東北歷代疆域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 年),有一章專論遼代東北疆域。
本時期遼代文物考古有許多重大發現,可謂美不勝收,已有不少論著介紹。如《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年)(文物出版社,1990年)、《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東北考古四十年》(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譚英傑等《黑龍江區域考古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馮永謙《建國以來遼代考古的重要發現》(《遼金史論集》第1輯)等,不再贅述。最近10多年出版的有關遼代考古著作有徐秉琨《遼墓遼塔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1983年)、項春松《遼代壁畫選》(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4年)、王健群、陳相偉《庫倫遼代壁畫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史樹青等《應縣木塔的遼代祕藏》(文物出版社,1991年)、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遼陳國公主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蓋之庸《叩開遼墓地宮之門》(山東畫報出版社,1997年)等。
這裡還要說明的是,東北、華北地區的一些文物考古工作者,如李文信、蘇赫、蘇天鈞、項春松、李逸友、鄭紹宗、徐秉琨、馮永謙、干志耿、孫秀仁、齊心、陳相偉等,長期從事以本地區為主的文物考古工作和歷史地理研究,為拓展遼金史料做出了重要貢獻。限於本文篇幅,不能一一備述。
(七)文獻整理及其他
文獻整理。有中華書局本《遼史》(1974年),初由馮家昇點校,繼由陳述完成,是迄今最好的本子。葉隆禮《契丹國志》,由賈敬顏、林榮貴點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李有棠《遼史紀事本末》(中華書局,1983年),初由孟默聞點畢,繼由崔文印復核、分段、校勘,並編“遼史人名清元異譯對照表”附於書名。陳述在《遼文匯》基礎上又經增益,改名《全遼文》(中華書局,1982年),是一部遼文總集。此書因存在疏漏舛誤而受到指摘,但它畢竟為研究者提供了很大方便,希望能有機會校勘重印。向南編《遼代石刻文編》(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是一部遼代石刻總集,收錄刻文300余篇,其數量超出以往所有文編。趙永春編注《奉使遼金行程錄》(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收五代兩宋奉使遼金行程錄37篇,其中使遼22篇,附有題解和注釋。陳高華輯校《遼金元宮詞》(北京古籍出版社,1988年),對研究三朝的帝王和宮眷生活及政治、歷史、風俗等提供了資料。補正表志之作,有陳述《遼史避諱表》(《遼金史論集》第4輯)、朱子方《新補〈遼史·藝文志〉稿》(《遼金史論集》第7輯)、閻萬章《遼史公主表補正》(《遼金史論集》第1輯)、楊若薇、向南《遼史百官志辨誤舉例》(《社會科學輯刊》1982年第3期),向南《遼史公主表補正》(《社會科學輯刊》1987年第6期)、《遼史地理志補正》(《社會科學輯刊》1990年第5 期)、《遼史皇族表補正》(《東北地方史研究》1991年第2期),馮永謙《遼史外戚表補證》(《社會科學輯刊》1979年第3、4期),蔡美彪《遼史外戚表新編》(《社會科學戰線》1994年第2期)等。
工具書。有《中國歷史大辭典》遼夏金元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6年)、鄧廣銘主編中國大百科全書《遼宋西夏金史》(中國大百科出版社,1988年),這是兩本比較好的斷代史辭書。曾贻芬、崔文印編《遼史人名索引》(中華書局,1982年)。
論文集。主要有歷史研究編輯部編《遼金史論文集》(遼寧人民出版社,1985年),中國遼金史學會主持編輯《遼金史論集》1-5輯、7-9輯,宋德金等編《遼金西夏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等,還有孫進己等編大型資料集《契丹史論著匯編》(1988年)等。
譯著。主要有王承禮主編《遼金契丹女真史譯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邢復禮譯愛宕松男《契丹古代史研究》(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等。
(八)西遼史
關於西遼史,從清代至本世紀40年代,我國學者在整理史料、考訂史實、譯注國外著作方面都做了一些工作。如清錢大昕撰《西遼紀年》(《十駕齋養新錄》卷八),丁謙《西遼立國本末考》、《西遼疆域考》、《西遼都城考》,王國維《西遼都城虎思斡耳朵考》、《長春真人西游記校注》,唐長孺《耶律大石年譜》(《國學論衡》1卷7、8期,1936年),岑仲勉《讀西遼史所見》(《金陵學報》4卷2期,1936年)等。梁國東《西遼史》據俄國布萊資須納德《中世紀研究》中有關西遼部分摘譯為中文,並詳加注釋,於30年代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中華書局於1955年再版,增加了新版前言和附錄)。
在此後的三四十年間,西遼史研究比較沉寂。僅見陳述《哈喇契丹說——兼論拓拔改姓和元代清代的國號》(《歷史研究》1956年第2期)述及西遼。至70 年代末80年代初以來,一些刊物陸續刊出文章,就西遼史若干具體問題進行討論。如趙俪生《西遼史新證》(《社會科學戰線》1978年第4期)、韓儒林《關於西遼的幾個地名》(《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4期,1980年)、鄧銳齡《西遼疆域淺釋》(《民族研究》1980年第2期)、周良霄《關於西遼史的幾個問題》(《中華文史論叢》1981年第3輯)、陳得芝《耶律大石北走史地雜考》(《歷史地理》第2輯,1982年)、余大鈞《耶律大石創建西遼帝國過程及紀年新探》(《遼金史論集》第1輯)、柴平《耶律大石北奔年代考》(《歷史研究》1994年第6期)、錢伯泉《大石、黑衣大石、喀喇汗王朝考實》(《民族研究》1995年第1期)、《大食與遼朝的關往和耶律大石的西征——遼朝與喀喇汗王朝關系史探微》(社會科學戰線)1995年第2期)等。此外,蔡美彪等《中國通史》第六冊、楊樹森《遼史簡編》、舒焚《遼史稿》等均有章節敘述西遼史。
對西遼史進行系統研究而且成就最大者是魏良弢,其成果集中反映在《西遼史研究》(寧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和《西遼史綱》(人民出版社,1991年)兩書中。前者梳理中外西遼史料、文獻及研究情況,考證紀年,敘述政治、經濟、疆域、民族、文化等問題,對許多史實有精心考釋。後者是在前書基礎上寫成的,著重闡述西遼歷史發展的基本過程,勾勒出西遼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輪廓。考證缜密,敘事詳實,標志西遼史研究取得了重大進展。魏良弢還撰有《喀喇汗王朝史稿》(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 年),對一度為西遼屬國的喀喇汗王朝作了全面論述。其體例與《西遼史研究》略同。紀宗安發表論文多篇,並著《西遼史論·耶律大石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
三、20世紀下半葉的金史研究
本世紀下半葉的金史研究同遼史研究一樣,取得了重大進展。關於金朝斷代史及以較大篇幅敘述金史者,有張博泉《金史簡編》(遼寧人民出版社,1984年),這是第一部全面系統敘述金源一代的斷代史專著。還有何俊哲等著《金朝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及前面提到的《中國通史》第6冊、《中華文明史》遼宋夏金卷、李桂芝《遼金史簡編》等。
以下分專題介紹。
(一)社會性質與經濟
張博泉著《金代經濟史略》(遼寧人民出版社,1981年)是金代經濟研究的第一部專著,對金史研究具有開拓性。此書全面論述了金代農業、工礦業、商業、土地制度、賦役制度、金制與遼宋元制的關系以及金代經濟在中國歷史發展中的地位諸問題。作者在許多重要問題上提出了看法,特別是糾正了以往論著多偏重女真族對中原北方經濟的破壞作用而忽視金代經濟恢復與發展的一面,因而有利於全面評價、認識金朝的歷史地位。此外,還有前已述及的漆俠、喬幼梅著《遼夏金經濟史》和《中華文明史》遼宋夏金卷(金代經濟部分由武玉環、程妮娜執筆)。
以下分別介紹有關社會性質及社會經濟中幾個具體方面的研究。
1.社會性質。關於女真社會性質的認識分歧較大,歸納起來可分三種,而每種之中又不盡相同。一是認為女真在建國前後處於奴隸制階段,於海陵、世宗、章宗時向封建制過渡。呂振羽《簡明中國通史》下冊(人民出版社,1959年)、張博泉《金史簡編》、蔡美彪《中國通史》第6冊等都認為女真族在章宗時或在海陵王到章宗時最後完成奴隸制向封建制的過渡。二是認為女真建國後未經奴隸制,而直接向封建制過渡。華山、王赓唐《略論女真氏族制度的解體和國家的形成》(《文史哲》1956年第6期)說,女真族在建國後不久,滅遼與北宋,受到其高度發展的封建文化影響,開始向封建制飛躍發展。張廣志《女真與奴隸制》(《青海師范大學學報》1985年第1期)認為,應把金初社會性質與金初女真族的社會性質加以區分。在女真人中,除少數高等權貴之外,奴婢數大大少於自由民,他們扮演不了社會生產主要承擔者的角色。熙宗、海陵、世宗、章宗四朝的改革,無一不是圍繞著消除原始的殘余影響,說不上是從奴隸制到封建制的過渡。三是認為主奴矛盾始終是金代的重要社會矛盾,從現存史料難以找到女真族何時基本完成封建化的時間。王曾瑜《宋朝的奴婢、人力、女使和金朝奴隸制》(《文史》第29輯)持此說。
2.人口與戶籍。高樹林《金代戶口問題初探》(《中國史研究》1986年第2期)指出,金朝是明朝以前各王朝戶口增長最快的王朝,戶數占宋金總數的43.81%,比遼時增長近一倍。張博泉、武玉環《金代的人口與戶籍》(《學習與探索》1989年第2 期)也認為金代的戶口同遼宋時期相比有很大增長。王育民《金朝戶口問題析疑》(《中國史研究》1990年第4期)則指出金朝實際戶口並不高於遼宋,南盛北衰的大勢並未改變。劉浦江《金代戶口研究》(《中國史研究》1994年第2期)也說,金朝戶口負增長和零增長的年份多於正常增長的年份。此外,論者對《金史·地理志》所載戶口數系年,有元光二年、天興三年及七年或八年三說。此外,王曾瑜《金朝戶口分類制度和階級結構》(《歷史研究》1993年第6期)、劉浦江《金代戶籍制度刍論》(《民族研究》1995年第3期)對有關問題作了深入探討和辨析。
3.二稅戶和驅口。二稅戶是遼金時期的戶名。有關二稅戶的最基本史料有兩條:一條見於元好問《中州集》卷二《李承旨晏》,一條見於《金史·食貨志一》。由於史料少且有歧異,加之論者理解不同,引起對二稅戶問題的爭議。關於二稅戶的涵義及其與頭下戶的關系:一種意見認為,對二稅戶的解釋應從《金史·食貨志一》,即指“分其稅一半輸官,一半輸寺”。羅繼祖《遼代經濟狀況及其賦稅制度簡述》(《歷史教學》1962年第10期)持此說。他又據《遼史·地理志一》所載“征稅各歸頭下,惟酒稅課納上京鹽鐵寺 ”判斷元好問是把“頭下”和寺院的二稅戶混為一談了。第二種意見認為,二稅戶應指《中州集》所說的“輸租為官,納課給其主”,並說不能將頭下戶與二稅戶截然區分開來。陳述《契丹社會經濟史稿》和張正明《契丹史略》基本主張此說。第三種意見認為,遼代有屬頭下軍州的二稅戶,有屬寺院的二稅戶,二者是有區別的。蔣松巖《遼金“二稅戶”及其演變》(《北方論叢》1981年第2期)、張博泉《遼金“二稅戶”研究》(《歷史研究》1983年第2期)持此說。關於遼代二稅戶社會地位,多認為是農奴。關於驅的身分與地位,有兩種看法。張博泉《遼金“二稅戶”研究》、《金代“驅”的身分與地位辨析》(《晉陽學刊》 1988年第2期)認為驅不是奴隸,其身分低於良民而高於農奴。而李涵、易學金《金代的“驅”不是奴婢嗎——與張博泉先生商榷》(《江漢論壇》1986年第11期)、賈敬顏《金代的“驅”及其相關的幾種人戶》(《社會科學輯刊》1987年第5期)、王曾瑜《金朝戶口分類制度和階級結構》、李錫厚《論驅口》(《中國史研究》1995年第2期)等認為金代驅即是奴隸。
4.通檢推排。通檢推排是金朝賦役制度中一項重要措施,從世宗延續到章宗時期,特別是世宗時多次推行。論者對其社會效果有不同評價。尚钺《中國史綱要》、張博泉《金代經濟史略》持否定意見,認為是以整理稅收為名而實行掠奪,前弊未革,後弊又生。趙光遠《試論金世宗對州縣民戶的通檢推排》(《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1年第2期)、《金代的通檢推排》(《學習與思考》 1982年第4期)、《再論金代的通檢推排》(《遼金史論集》第一輯)等文則肯定其積極作用及金世宗的改革精神。劉浦江《金代通檢推排探微》(《中國史研究》1995年第4期)認為,對通檢推排不能根本否定,但也存在弊端。
5.貨幣。李埏、林文勳撰《宋金楮幣史系年》(雲南民族出版社,1996年)是一部研究宋金時期紙幣的重要著述。前述李俠、曉峰著《中國北方民族貨幣史》有一章專敘金代貨幣。還有秦佩珩《金代貨幣史略論》(《鄭州大學學報》1982年第2期)、張博泉《金代的貨幣制研究》(《金史論稿》第2卷)、喬幼梅《宋金貿易中爭奪銅幣的斗爭》(《歷史研究》1982年第4 期)和《金代貨幣制度的演變及其對社會經濟的影響》(《中國史研究》1983年第3期)等文。
(二)政治與制度
關於這方面的專著有前已述及的《中國政治制度史》遼金西夏卷,其中“金朝的政治制度”(李錫厚執筆)系統敘述了金朝皇帝制度、中央決策體制、中央行政體制、地方行政機構、司法制度、監察制度、猛安謀克及民族事務管理制度、軍事制度、財政管理制度、人事管理制度等。《中華文明史》遼宋夏金卷的金代政治、法律、軍事部分,分別由程妮娜、王宏治、劉慶執筆。王可賓《女真國俗》(吉林大學出版社,1988年)探討遼金女真婚姻和家庭形態、社會制度(包括氏族制、軍事民主制、勃極烈制、猛安謀克制)及社會習俗。
1.猛安謀克制度。這是金代社會的一種特有的制度,在女真及金朝社會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一些通史著作提到這一制度大都語焉不詳,而且在對其涵義、性質等問題表述上存在很大分歧。關於這個問題,張博泉從60年代起發表一系列文章,包括猛安謀克制度的形成、發展及其破壞的原因;猛安謀克世官貴族與平民;金代東北猛安謀克分布;猛安謀克與民族關系;猛安謀克與頭下、八旗制度的比較觀;猛安謀克在女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等。這些文章,收在《金史論稿》第1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之中。
2.職官。程妮娜《金初勃極烈制度研究》(《金史論稿》第2卷)考察了金初中央官制——勃極烈制度的形成、發展及其特點,諸勃極烈的構成、分職以及其發展趨向等問題。趙冬晖《金初勃極烈官制的特點》(《遼金史論集》第1輯)指出這一制度帶有濃厚的血緣關系色彩,是一種帶有明顯貴族議事制度痕跡的官僚制度。譚其骧《金代路制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1輯)考述了金代諸路總管府,轉運司,按察司及招討司、統軍司的設置及其與遼宋制的關系。程妮娜《試論金初路制》(《社會科學戰線》 1989年第1期)認為金初路制分為三個系統:萬戶路屬奴隸制范疇,兵馬都總管府屬封建制,都統、軍帥司路介於二者之間。李涵《金初漢地樞密院試析》(《遼金史論集》第4輯)就金初樞密院的設置沿革、職能、機構、隸屬關系等進行探討。李錫厚《金朝實行南、北面官制度說質疑》(《社會科學戰線》 1989年第2期)認為金初尚未形成中央集權,無法實行南北面官制。蔣松巖《金代御史台初探》(《遼金史論集》第4輯)肯定了御史台在澄清吏治、平理冤獄、糾察不法官吏等方面發揮的積極作用;《金代提刑司與按察司初探》(《平原大學學報》1987年第3期)論述了兩司的產生、組成、職權、發展演變及其作用。孟繁清《金代的令史制度》(《宋遼金史論叢》第2輯,1991年)論述了金代令史的配置、選拔與出職等。武玉環《金朝中央官制的改革》(《北方文物》 1987年第2期)指出,金朝中央官制改革的過程,就是中央官制漢化、金代社會由奴隸制向封建制演變及中央集權制形成和鞏固的過程。
黑龍江文物考古工作隊編《黑龍江古代官印集》(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有一節專述“金代官印”。景愛著《金代官印集》(文物出版社,1992年),可據以補正《金史》的《百官志》、《地理志》,訂補某些年號、時間之誤和史實之阙。
3. 軍事及其他制度。王曾瑜《金朝軍制》(河北大學出版社,1996年)是這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本書對金代軍事機構、武裝力量體制、金軍編制、金軍組成、簽軍和募兵及若干重要制度作了論述。作者長期研究宋史,兼治遼金史,從中比較、互證,彌補遼金史料之單薄,多有獨到之處。乣軍是遼金元軍事史研究中眾說紛纭的一個問題。自清代以來,中外學者屢有考辨與論述。對乣字的形、音、義和乣軍涵義等都有不同見解。陳述《乣軍史實論證》(《史學集刊》第6期,1950 年),系據《乣軍考釋初稿》略加修改而成)、蔡美彪《乣與乣軍之演變》(《元史論叢》第2輯)、賈敬顏《糾軍問題刍議》(《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0年第1期)分別發表了不同看法。
其他制度研究,有傅百臣《金代法制研究》(《金史論稿》第2卷)、都興智《金代的科舉制度》(同上)、趙冬晖《金代科舉制度研究》(《遼金史論集》第4輯)和《金代科舉年表考訂》(《北方文物》1989年第2期)、劉慶《金代贖身制度研究》(《金史論稿》第2卷)等。
4.東夏史。王慎榮、趙鳴歧著《東夏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對蒲鮮萬奴所建東夏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及與蒙古、高麗的關系等進行系統論述。特別是對東夏的國名、年號、國都、官制以及疆域等存在較大分歧的問題發表了看法。本書是繼金毓黻所著《東北通史》中“蒲鮮萬奴之東夏國”一章後關於東夏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討論東夏國的論文,有張紹維、李蓮《東夏年號的研究》(《史學集刊》1983年第3期),樸真奭《論東夏稱號》(《延邊大學學報》 1983年第4期),李健才《關於東夏幾個問題的探討》(《民族研究》1985年第3期),董萬倫《關於東真國幾個問題的探討》(《蒲峪學刊》1988年第1期)等。
(三)社會生活與文化
1.社會生活。宋德金著《金代的社會生活》(陝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是關於這個專題研究的第一本專書,概括敘述了金代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包括各階級、階層的社會地位和生活,衣食住行,婚喪禮俗,宗教信仰,倫理道德,文娛體育,歲時雜俗等,還考察了金代漢族與女真文化的相互影響和民族融合的歷史趨勢。
2.文化。張博泉《論金代文化發展的特點》(《社會科學戰線》1986年第1期)、《論金代文化的發展及其歷史地位》(《社會科學戰線》1987年第1期)兩文指出,金代文化發展的主要特點是:中原文化北移;儒道釋三教合一;以中原文化為核心,發展了各民族文化。金代文化的發展起著“上掩遼而下轶元”的作用。陳學霖《金國號之起源及其釋義》(《遼金史論集》第3輯)透過這一命題探索女真與漢文化的接觸和交融及其對政治與意識形態的影響。宋德金《正統觀與金代文化》(《歷史研究》1990年第1期)認為正統理論推動了金代文化的發展,並對後世產生了影響。董克昌《大金統治思想主體的儒家文化論》(《遼金史論集》第5輯)論述在金朝統治思想中,儒家主體地位的確立原因、過程和特征。前述張碧波、董國堯主編《中國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有一章為“女真文化”,敘述女真語言文字、生活習俗、倫理宗教、科學技術、文學藝術、體育游藝等。
以下介紹進展較大的幾個方面的研究情況。
文學。周惠泉多年專事金代文學研究,發表一系列文章及專著《金代文學學發凡》(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此書為第一本金代文學研究史,或曰金代文學批評史。此外,他還參與多卷本“中國文學通史系列”的撰寫,承擔《宋代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之金代文學部分。最近又出版了《金代文學論》(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詹杭倫著《金代文學思想史》(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1990年)對金代文學思想(包括文學創作、批評和理論)的發展狀況及規律進行探討。前述張晶《遼金詩史》金代部分揭示了金詩發展的獨特軌跡。這部分占全書37萬字的4/5篇幅,是迄今最為詳實的金代詩史。張松如主編《遼金元詩歌史論》有多篇論述金詩。顧易生、蔣凡、劉明今《宋金元文學批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4編“金元文學批評”設有章節論述金代文學批評。
關於金代作家研究,主要集中在對元好問的研究上。有郝樹侯、楊國勇著《元好問傳》(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中國元好問學會編《紀念元好問800誕辰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降大任《元遺山新論》(北岳文藝出版社,1988年)等。降大任《且莫枉罪元遺山——重評元遺山的氣節問題》和《元遺山氣節問題諸說評議》兩文對有關元好問名節問題的議論提出新見,認為元好問大為金哀宗一人而死的動機和表現,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封建愚忠觀念,反映出他具有進步的氣節觀。韓志遠《元好問在金元之際的政治活動》(《元史論叢》第5輯,1993年)說,元好問不是政治家和思想家,不能誇大他在當時的政治作用;在學術上也並未創立一個學派、把金代詩文推進一個更高的階段。對元好問作品的整理與研究,有姚奠中主持校點的《元好問全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凡60卷,包括《遺山集》、《新樂府》、《續夷堅志》,還據有關本子作了增補,整理者稱,“遺山存世之作,可能已盡於此”。還有賀新群輯注《元好問詩詞集》(中國展望出版社,1986年)。元好問的詩歌選本有多種,如郝樹侯選注《元好問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陳沚齋《元好問詩選》(廣東人民出版社,1985年)等。金代詩詞總集,有唐圭章編《全金元詞》(中華書局,1979年),共收錄金元282位詞人,7293首詞作。其中金代70人,3572首,大大超過了前人所輯金詞。蔣瑞兆、郭明志編纂《全金詩》(南開大學出版社,1995年)是在元好問《中州集》和清《全金詩》基礎上廣搜博采,網羅散佚,編纂而成,為迄今輯詩最多的金詩總集。是書以詩人生卒年代為序編次。它不僅為研究金代文學提供了極大方便,而且對研究金代社會也很有價值。
對金院本、諸宮調等也有人進行整理與研究。楊萬裡於1957年發現《古本董解元西廂記》,並為古典文學出版社影印此書撰寫跋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凌景埏校注《董解元西廂記》(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朱平楚校點《全諸宮調》(甘肅人民出版社,1987年),其中有金代作品《劉知遠諸宮調》、《西廂記諸宮調》,孫遜著《董西廂和王西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語言文字。以金光平、金啟孮父子的研究成就最大,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其成果集中反映在他們合著的《女真語言文字研究》(文物出版社,1980年)和金啟孮編著的《女真文辭典》(文物出版社,1984年)兩書中。前書對女真文字的創制、構造、讀音,女真語語法以及女真文字對史學的貢獻等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後書在前書基礎上編次而成,是研究女真文及女真史、金史的重要參考書。此外,還有學者發表了考釋女真文字、探索女真文構制規律的文章。
宗教。專著有張踐《中國宋遼金夏宗教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論文有陳俊民《略論全真道的思想源流》、郭旃《全真道的興起及其與金王朝的關系》(《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3期)、陳智超《金元真大道教史補》(《歷史研究》1986年第6期)等。由陳垣編纂,陳智超、曾慶英校補的《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是一部大型的道教碑刻資料集,所收文獻按時間順序排列,金元部分數量最多,凡882通,是研究金元全真派、真大道派、太一派、正一派道教的重要資料。
(四)民族、民族關系、金宋關系
1.民族。干志耿、孫秀仁著《黑龍江古代民族史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一書有約7萬字篇幅敘述遼金時期女真族的歷史。孫進己《東北民族源流》(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認為,單純以金代皇室的起源作為金代女真族起源是不正確的。金代加入女真族中的除生女真外,還包括其他一些女真部落,乃至在遼代還不屬於女真部落的。孫進己等著《女真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敘述了從女真先人肅慎至遼金元明女真的發展史。趙振績《女真族系源流考異》(《歷史研究》1995年第5期)主張金代女真屬東胡族系,來自北魏初之奴真、唐之拏(奴真)、五代之女真。蔣秀松《女真與靺鞨》(《民族研究》1992年第3期)認為女真族的主源不是黑水部或狹義的黑水靺鞨,而是源於渤海統治下的靺鞨部落。王禹浪《“女真”稱號的含義與民族精神》(《北方文物》1992年第3期)認為“海東青”是女真稱號的真正含義,女真稱號就是民族精神的體現。
2.民族關系、金宋關系。鄧廣銘、王曾瑜、周寶珠等均有專書或文章對宋金戰爭的人物、史實等進行論述和考辨,這在有關宋史研究的綜述文章中都有介紹,不再贅述。這裡僅舉幾篇作為民族史和金史研究的論文,有岑家梧《金代女真和漢族及其他民族的經濟文化聯系》(《民族研究》1979年第2期)、吳泰《試論宋、遼、金對峙時期民族關系的幾個問題》(《北方論叢》1982年第3期)、張博泉《宋金和戰史論》(《史學集刊》1984年第2期)、任崇岳《略論宋金關系的幾個問題》(《社會科學輯刊》1990年第4期)、趙永春《關於宋金“海上之盟”的幾個史實問題》(《北方文物》1985年第2期),《宋金交聘制度述論》(《遼金史論集》第4輯)、《宋金關於“受書禮”的斗爭》(《民族研究》1993年第6 期)、董克昌《宋金外交往來初探》(《學習與探索》1990年第2期)等。
(五)人物
關於金代人物,以對阿骨打、海陵王、金世宗的研究為多。
1.阿骨打。蘇金源《論完顏阿骨打的政治、經濟改革》(《史學集刊》1982年第2期),張博泉、程妮娜《完顏阿骨打略論》(《遼金史論集》第1輯)、劉慶《完顏阿骨打》(軍事科學出版社,1992年)等,都肯定了金太祖阿骨打的歷史地位。
2.海陵王完顏亮。關於完顏亮,歷來毀譽不一,毀多於譽。近20年來,對此展開了熱烈討論。蔡美彪等著《中國通史》第6冊和蔡美彪《遼金史簡說》(《歷史教學》1982年第2期)指出,海陵王在其統治期間,展開了比熙宗時期更為激烈的一系列改革。包括嚴厲鎮壓女真族的保守派,大批任用漢人、契丹人和渤海人參政;進一步改革政治制度;遷都燕京;使大批女真人南下定居;攻打南宋。張博泉《金代經濟史略》(第182頁)、《金史簡編》(第135-163頁)、《論完顏亮改革及其失敗原因》(《歷史人物論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等論著指出,海陵王一方面繼熙宗之後,采取在北方恢復和發展社會經濟的各項措施,另一方面發動南侵,加深了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並導致了自身的最後滅亡。這是海陵王由一個改革派而被稱為暴君的歷史根源。此外,還有許多文章稱完顏亮是女真族歷史上傑出的政治家,肯定他的改革、遷都及用人政策等。有崔文印《略談海陵王完顏亮的評價問題》(《遼金史論集》第1輯),劉肅勇《論完顏亮》(《中國史研究》1985年第4期),張克、楊旸《完顏亮論》(《學習與探索》1988年第2期),王曾瑜《完顏亮用人的某些特點》(1985年8月 21日《光明日報》)等。有些學者則提出不同看法。肖民《也論完顏亮》(《北方文物》1989年第4期)認為,完顏亮消除女真族軍事民主制及其遺風,確立君主獨裁專制制度,不值得全盤肯定。羅繼祖《完顏亮小議》(《遼金史論集》第2輯)認為,完顏亮過大於功,這從他毀上京舊宮殿、諸大族第宅和儲慶寺以及其橫征暴斂,逼反契丹,妄起南侵戰禍,荒淫濫殺,卒到眾叛親離,不得其死,是不難得出結論的。董克昌《怎樣評價完顏亮的功過》(《北方文物》1989年第4 期)、《誰是小堯舜》(《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認為,完顏亮貢獻突出,問題也突出,其歷史功績不能與世宗相比。趙葆寓《略論完顏亮的功與罪》(《宋遼金史論叢》第2輯,中華書局,1991年)將海陵王在位12年以貞元南遷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對女真社會的進步起了推動作用;後期大興土木,擴軍備戰,剛愎自用,對社會經濟造成嚴重後果。
3.金世宗。舊史中對金世宗評價很高,稱之為“小堯舜”。許多論者認為,舊史記載雖有誇大之處,但在他統治期間的確實行了一些與民休息、整頓吏治等有利於推動社會前進的措施,因此是一個有作為的帝王和有能力的政治家。如劉肅勇著《金世宗傳》(三秦出版社,1986年),楊啟《略論金世宗》(《湘潭大學學報》1982年第1期),張博泉《試論金世宗的治世思想及其得失》(《黑龍江文物叢刊》1983年第3期),董克昌《試析金世宗的“保境息民”政策》(《北方文物》1985年第2期)、《誰是小堯舜》(《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等。崔文印《〈大金國志〉初探》(《史學研究》1982年第7期)對以上評價提出異議。認為《金史》中關於金世宗的記載不足為據,他並不像本紀所描繪的是什麼“小堯舜”,遠沒有海陵王那樣的政治抱負和雄心。他的形象是被封建史臣吹捧起來的。朱子方《金世宗簡論》(《東北地方史研究》1990年第2期)也認為金世宗是一個逆潮流而動的失敗者。
(六)歷史地理與文物考古
1.歷史地理。譚其骧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6 冊(宋遼金時期)及《中國歷史地圖集釋文匯集·東北卷》金代部分是這方面的重要成果。李健才《東北史地考略》一書中有《吉黑兩省西部地區四座遼、金古城考》、《松花江名稱的演變》、《白山黑水考》《鴨子河和金代肇州續考》、《金代東北的交通路線》、《關於東夏幾個問題的探討》等,均是論述金代歷史地理的,對前人的一些結論提出補充和修改。此外,景愛著有《關於金代蒲與路的考察》(《文史》第10輯)。王禹浪著《金代黑龍江述略》(哈爾濱出版社,1993年)是一本地方金朝斷代史。
2.都城。上京:阿城縣文管所編《金代故都上京會寧府遺址簡介》(1980年)是最早編成的有關這方面的簡要材料。朱國忱著《金源故都》(北方文物出版社,1991年),以文獻為主,結合考古研究成果,重點論述金上京會寧府的興廢過程以及與之相關的歷史事件。景愛著《金上京》(三聯書店,1991年),根據多次實地考察的結果,結合文獻對上京城的營建始末、建築結構、行政建置以及社會生活等作了論述。閻景全《金上京親查記》(《遼金史論集》第9輯)公布上京城確切周長為11100米左右。中都:於傑、於光度著《金中都》(北京出版社,1989 年)是繼周耿《金中都考》(1953年4月18日《光明日報》)、朱偰《八百年前的北京偉大建築——金中都宮殿圖考》(《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第7 期)、閻文儒《金中都》(《文物》1959年第9期)以及侯仁之《北京都市發展過程中的水源問題》(《北京大學學報》1955年第1期)等文以後,金中都研究的重要成果。對大城、宮城、園林、陵墓乃至政治、經濟、文化等都作了考察和論述。趙其昌《金中都城坊考》(《遼金史論集》第4輯)考述金中都城的營建過程、城牆與城門的基本情況及諸坊位置。
3.文物考古。參見前引《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北京考古四十年》、《黑龍江區域考古學》等。
(七)史料整理、工具書和譯著
1.史料整理。關於史料校點、箋證、注釋,有中華書局標點本《金史》(1975年),是迄今最好的本子。在金代史料整理方面,以崔文印用力最勤,有《金史紀事本末》(中華書局,1980年)、《大金國志校證》(中華書局,1986年)、《歸潛志》(中華書局,1983年)、《靖康稗史箋證》(中華書局,1988年)等。中華書局還主持點校《金文最》(1990年)。羅繼祖、張博泉著《鴨江行部志注釋》(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張博泉著《遼東行部志注釋》(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等。編纂史料,有董克昌主編《大金诏令釋注》(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參考《唐大诏令集》、《宋大诏令集》的編纂方法,分帝統,皇太後、皇後、妃嫔、公主,皇太子,宗室,典禮,軍事,經濟,政事,外事等門,匯集了有金一代的诏令,並附有注釋和說明。還有李澍田等輯注《金史輯佚》(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趙鳴岐、王慎榮編《東夏史料》(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張中澍、陳相偉等校注《金碑匯釋》(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以及前述趙永春編注《奉使遼金行程錄》。
2.工具書。陳述著《金史拾補五種》(科學出版社,1960年)分“金史氏族表”、“女真漢姓考”、“金賜姓表”、“金史同姓名表”、“金史異名表”,是研究遼、金、元史和民族史的重要工具書。崔文印《金史人名雜考》(《文史》第20輯)有所補正。此外,還有前述《中國歷史大辭典》遼夏金元卷和中國大百科全書《遼宋西夏金史》是兩本較好的斷代史辭書。
3.譯著。有金啟孮譯《金代女真史研究》(三上次男著,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李東源譯《金朝史研究》(外山軍治著,黑龍江朝鮮民族出版社,1988年),以及《遼金契丹女真史譯文集》、《民族史譯文集》第10輯(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1981年)等。
四、評價與展望
從以上對遼金史學的回顧,我們可以看出,從元人修遼金兩史到明末的300年間,遼金史學十分沉寂。到了清代雖有所變化,但直至上個世紀末尚未超出史料編纂整理的范疇。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二三十年間,由於大量珍貴史料的發現,包括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及西域各地簡牍,敦煌千佛洞六朝和唐人所書卷軸,內閣大庫書籍檔案,以及中國境內之“古外族遺文”(見王國維《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清華周刊》350期),極大地推動了中國歷史學的發展,出現了近代實證史學,這在遼金史研究上也有所反映。本世紀上半葉,一方面,遼金史料整理繼續有所進展;另方面,有學者開始用近代實證史學方法研究遼金史。在這個時期裡對遼金史學(主要是遼史學)及契丹文、女真文研究作出重要貢獻者有陳述、馮家昇、傅樂煥、羅福成、羅繼祖等。
20世紀後半葉,隨著新中國的誕生,馬克思主義史學主導地位的確立,遼金史研究者也努力以此作為指導思想從事研究。不過在50年代初到“文革”以前,以遼金史為主要研究方向的學者屈指可數,成果也很少。
近20年來,遼金史研究同許多學術領域一樣十分活躍,發表論著之多,涉及范圍之廣,是前所未有的。關於遼金史研究的具體成果與進展,已如前面所述。從宏觀上看,也有很大改觀。
一是遼金史在中國通中編纂中地位的變化。元人修遼金宋三史前,關於正閏問題爭論了幾十年,最後決定宋遼金“各與正統,各系其年號”,這在史書編纂史上是一個進步。然而在後來的五六百年間,一些史學家卻由此有所倒退,斥遼金史為不足觀。直至本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通史著作大都將遼金附於宋代部分之後而順便述及。近一二十年來,這種狀況已有改變。蔡美彪等著《中國通史》第6冊首先將遼、西夏、金史與兩宋分別立章敘述,確立了遼、西夏、金史在通史中應有的地位。此後,鄧廣銘主編的中國大百科全書《遼宋西夏金史》也是按朝代編次的。
二是如何評價遼金兩朝的歷史地位和作用問題。長期以來,由於遼金兩代流傳下來的史料較少,傳統正統觀念的影響,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對遼金史研究薄弱等原因,導致對遼金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認識不足。人們往往是更多地看到契丹女真及遼金兩朝的破壞作用,而無視或輕視其成就與貢獻。這種認識,不符合我國各族人民共同創造了中華文明的歷史實際。近幾十年來,研究者更新觀念,深入開展研究,在這方面提出若干新見,已為學術界所認同。如陳述多次強調遼金是我國歷史上的兩個重要朝代,是又一次北朝(見1982年8月30日《光明日報》)。
三是遼金史研究隊伍的形成與壯大。六七十年代以前,專門從事遼金史研究者甚少,而近20年來一批中青年史學工作者走入遼金史研究的行列,形成一支數量可觀的研究隊伍。而且他們之中有許多人研究課題有所側重,相對集中,為取得突破性進展奠定了基礎。
不過也應看到,雖然遼金史研究已經取得很大進展,但是同有些斷代史研究相比仍顯薄弱。功力深厚的專家和堪稱力作的成果不多。遼金史中還有不少領域有待開拓和深入探討,遼金史研究還有不少事情要做。
如何把遼金史研究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
一、縱橫比較,三史兼治。不能孤立地治遼金史,而應把它置於中國歷史長河中進行考察,並與同時期的五代、兩宋聯系起來研究。特別是宋遼金三史兼治,已為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所認同。早在40年代,金毓黻論治本期史的方法時即指出,“治本期史,惟有三史兼治,乃能相得益彰”(見《宋遼金史》,台灣洪氏出版社,1974年),這是不刊之言。
二、減少低層次重復,開拓新領域。近一二十年遼金史論著,特別是文章數量大增,令人目不暇接,然而其中有相當比重屬於低層次重復,有的甚至低於已經發表過的同類文章的水准。對於別人論過的題目要有所前進或駁難,否則便失去存在的價值。同時還應努力開拓新課題,關注新領域。
三、充分利用和繼續擴大史料資源。治遼金史者深為史料不足而苦惱,因而充分利用現有資料尤顯必要,諸如碑刻、考古、詩文、行程錄等,對研究制度、文化、社會生活等都有很大價值。至於宋元人的大量筆記、文集和史籍中有關遼金史料,如能充分利用,其成果的深度和廣度將有所改觀。
四、調整知識結構,開展多學科研究。為了把遼金史研究引向深入,許多課題除了需要歷史學的理論和方法之外,還要借助其他學科如民族學、文化人類學、語言學等方面的理論和方法才能取得突破性的進展。這尤應成為中青年學者努力的方向。
五、加強學科理論建設。20世紀的遼金史研究曾經是同國際政治相聯系的。從本世紀初,日本御用學者就開始對我國東北開展調查,制造了種種涉及我國東北主權及遼金史的若干論調,直至“二戰”前後,陸續出現了“南北對立論”、“異民族統治論”,進而又有所謂“征服王朝論”(初由美籍德國漢學家威特夫提出,後為日本學者所接受和發展)、“騎馬民族論”等等。這些大體上都出於由白鳥庫吉提出的旨在否定我國東北主權的“南北對立論”。幾十年來,這些“理論”不僅在國外影響深廣,而且至今還得到我國一些學者的贊同。如近年出版的江上波夫《騎馬民族國家》中譯本的譯後記中說,江上波夫的“騎馬民族——游牧國家——征服王朝的學術思想體系”,“對我們研究中國北方民族的國家起源問題和社會形態問題,有著帶啟發性的參考意義”,“沒有這樣一種指導思想,學術是難以避免錯誤的”。可見我們對這一學術思想體系不可掉以輕心。雖然近些年我國已有學者對上述體系進行清理,予以批駁,如張博泉積數十年研究地方史、遼金史和北方民族政權史的心得,撰寫《中華一體的歷史軌跡》(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年),為建構我們自己的遼金史學術體系開了先河。但此事任重而道遠,並非一兩本書或幾篇文章可以解決,以後應繼續進行更多有分量的評說。加強遼金史學的理論建設,乃是我們今後一項艱巨而光榮的任務。
最後,我要對本文的寫作作兩點說明。一、以上評述雖然力求全面、准確、公允,但因所見資料及筆者學識有限,難以如願,歡迎批評指正。二、第二三部分關於20世紀下半葉遼金研究的介紹,限於大陸出版的書刊。本時期台港地區,特別是台灣的遼金史研究有不少成果。如《姚從吾先生全集》(正中書局,1976年)中有遼朝史、金朝史及遼金史論文多篇;還有王民信著《契丹史論叢》(學海出版社,1973年),陶晉生著《宋遼關系史研究》(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女真史論》(食貨出版社,1981年),趙振績著《契丹族系源流考》(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楊樹藩著《遼金中央政治制度》(商務印書館,1978年),葉潛昭著《金律之研究》(商務印書館,1972年),王明荪著《宋遼金元史》(長橋出版社,1988年)、《宋遼金史論文稿》(明文書局,1988年),陳學霖著《中國歷史上之正統論:金代德運議研究》(西雅圖,1984年),《宋史論集》(東大圖書公司,1993年)也有數篇涉及金史等;宋史座談會編《宋史研究集》(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各輯亦收錄遼金史論文。史料匯編、輯錄有楊家駱主編《遼史匯編》(鼎文書局,1973年),陶晉生、王民信編《李焘續資治通鑒長編宋遼關系史料輯錄》,謝昭男撰《五代時期各國關涉契丹史事系年》、《澶淵之盟以前遼宋關系史事系年》(分見《遼史匯編》5冊和《遼史匯編補》)等。至於散篇論文就更多了。因聞見有限,為免掛一漏萬,未作評述,至為遺憾。敬請著者、讀者諒之。
【作者簡介】作者宋德金,1937年生,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編審。
- 上一頁:人氣旺盛的遼金古城——塔子城
- 下一頁:兩座800年古鎮的不同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