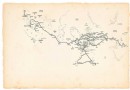偌大古都,容不下幾座會館?
日期:2016/12/14 20:23:38 編輯:古代建築史
2010會館保護與利用論壇”上公布的數據顯示,作為全國會館最為集中的北京西城區宣南地區,會館數量比建國初期減少了四分之三,比上世紀90年代減少了三分之二。這一地區現存的101個會館中,有94處仍有居民居住,另外7處為商業、辦公利用,預計未來只有約四成會館原址能夠避免“拆除”的命運。
在密密麻麻的各色商店、來往如梭的車流人流中,北京新街口北大街53號難掩落寞。兩扇青綠色的鐵門虛掩著,門前停著幾輛破舊自行車,之後是一尊三米余高徐悲鴻先生的塑像。塑像前兩束略微凋零的鮮花告訴別人:不久前,這裡有人來過。
這裡是徐悲鴻紀念館。院內告示欄清晰地寫道:9月起,徐悲鴻紀念館正式關閉。在館內工作了20余年的馮靜明說,原址上將重建一座相當於原使用面積兩倍的新館。“其實這次拆掉的紀念館已經不是真正意義的老建築了。徐悲鴻先生的故居在東城區受祿街,生命中最後6年他一直住在那裡,但多年前已經拆除了。”馮靜明說。
據“2010會館保護與利用論壇”上公布的數據顯示,作為全國會館最為集中的北京西城區宣南地區,會館數量比新中國成立初期減少了四分之三,比上世紀90年代減少了三分之二。這一地區現存的101個會館中,有94處仍有居民居住,另外7處為商業、辦公利用,預計未來只有約四成會館原址能夠避免“拆除”的命運。
即使為數不多幸存下來的會館,命運也大致相似。城市前進的滾滾步伐,讓這些盛名在外,卻已歷經歲月洗滌的老建築愈顯單薄。
落寞不應成為會館的定語
“砰、砰、砰”,在一陣沉悶的拍擊聲中,值班人員“叮叮當當”提著鑰匙出現,“吱呀”開了門。室內,陽光所及之處,看得見一抹浮塵。
即將拆除的徐悲鴻紀念館占地面積約4000多平方米,館內20余名職工擔負著整座建築管理、維護、保安等工作。紀念館灰體綠頂,裝飾中盡顯“老貴族”的做派。
“紀念館收藏了徐悲鴻先生各個時期的作品總計1000余件。”馮靜明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想要完好的保存這些珍品,恆濕恆溫是首要條件,但是這些年來我們一直做不到,安保工作只能說盡力做好吧。”
參觀是免費的,即使如此,平時一天最多也只有幾十個游客。“這樣的客流量還比不上周圍一家小賣部。現在很多學校規定學生必須來參觀,還要蓋章、簽到。但是很多孩子要麼讓家長代簽,要麼簽了到就走。”馮靜明說。
回顧這些年來老建築的命運,中國文物學會傳統建築園林委員會常務理事馬炳堅仍歷歷在目。“1999年,廣渠門內大街207號四合院數天內被拆,這是目前紅學專家唯一公認的有案可考的曹雪芹故居遺址;2000年,美術館後街22號一座明代兩進深四合院被拆,此前不久多位古建專家曾對這裡精美的磚雕稱奇;2005年,西城區共9間周作人的住房被拆除;2009年7月,梁思成故居也面臨同樣的困境。”
在馬炳堅看來,歷史之所以是歷史,就在於它的連綿和延續,而老建築是最真實的歷史符號和記憶。它們的存在就好像一部厚重的古書,講述著若干年前的故事,割裂自然的延續不是一種明智的選擇。
“一些發達國家在發展初期也發生過類似的情況。二戰之前的150多年裡,英國老建築的保護工作也一度不盡如人意,20世紀全英國有六分之一的別墅被毀壞。”馬炳堅說。“但是隨著人們在物質和精神生活越發富足,才意識到很多熟悉的東西已經蕩然無存,才感到後悔和遺憾。”
“後來為彌補這些過錯,英國在英格蘭和威爾士先後設立了500個保護區,用以保護原有建築和周圍的環境。”馬炳堅說,“可能因為經歷過失去和破壞,人們現在越發懂得珍惜,倫敦整座城市都成為了一座博物館。”
讓老建築體面地生存
郭沫若故居很有些鬧中取靜的意味:朱紅色大門,灰色院牆,在這座占地7000余平方米的兩進四合院內,處處可見茂盛的玫瑰叢和銀杏樹。在這片喧鬧的地段,它如同人群中一位干淨而體面的老人。
副館長趙笑潔說,作為北京市八大名人紀念館之一,郭沫若紀念館每年都能享受到政府的資助,待遇算很優越了。
“但是因為建築本身屬於文物,至少要做到‘5年一小修,10年一大修’。按照這樣的標准,即使只定期加固結構和給房子挑頂,所需要的經費就在1000萬元左右,而實際資金連一半都達不到。所以只能先挑最嚴重的問題解決。”趙笑潔說。
在微寒的秋末,紀念館內的銀杏葉已漸次泛黃,樹間千百片“小扇面”搖搖欲墜。兩只慵懶的貓踱著碎步,在石階、花叢間悠然自得。垂花門前兩口不成對的銅鐘左右為伍,與兩株上了年歲的松柏相伴。垂花門內,舊時的辦公室、臥房以及郭沫若夫人的寫字間依然如故。
“老建築本該以這樣的姿態存在。無論是修繕、翻新還是利用,都不該忽視建築本身的特質,這樣才能讓每一座建築‘體面’的生存。但要用這樣的標准來衡量我國諸多老建築的生存狀態,只能用‘委曲求全’來形容。”馬炳堅說。
幾年前,馬炳堅曾經概括過四合院建築工程中的十大“濫用”,包括了從建築材料、官事做法、彩畫、到雕刻、格局等方面。結果發現,這樣與歷史和文化不符的“濫用”在修繕和建造中比比皆是,很多施工方和操作工人對於建築文化缺乏起碼的了解。
以彩畫為例,中國古建築在構件上畫彩畫有嚴格的實施標准:皇家建築多用和玺彩畫、重要衙門建築多用旋子彩畫,而皇家園林和王府的次要建築一般采用蘇式彩畫等。但是近幾年的四合院修繕工程中,蘇式彩畫隨處可見,等級超越了王府。有的四合院甚至在屋內嵌滿了各朝代各色龍紋雕刻999條。
這種用拙劣的堆疊和粗糙的工藝拼湊而成的作品,被評為“毫無生命和尊嚴的建築。”“建築本身源自什麼朝代的風格、什麼身份的人住、和周圍環境是什麼樣的關系,都有嚴格的標准,好的建築會自己講故事。”馬炳堅說。
“好建築會藏著很多故事,每一個擺件、匾額都可能還原一段歷史細節。”湖廣會館大戲樓總經理霍建慶說。。穿過湖廣會館悠長的走廊,200年歷史的大戲樓赫然眼前。戲樓主體建築群雕梁畫棟、磨磚對縫青水牆。四周牆壁是如新的博古彩繪,戲台上方是“霓裳同詠”匾,抱柱楹聯長達一丈六尺。燈光亮起後更盡顯當年的金碧輝煌,精致玲珑間難掩王府風范。
“1994年到1996年5月,湖廣會館經歷了兩年的修繕期,花費數千萬元。在此之前這裡居住了35戶居民,柱子上到處綁著繩子晾衣服。大戲樓成了制本廠的倉庫,堆滿了紙張,據說‘前腳踏進戲樓就被灰塵沒了’。”霍建慶說。
“保護和利用老建築,無論是‘今為古用’還是‘古為今用’,前提都是尊重建築本身的特點。”馬炳堅說,“但這需要龐大的經濟支持。英格蘭紐卡斯爾一座由面粉廠改造的現代藝術博物館,為保留‘波羅的面粉廠’的字樣,就花了7000多萬英鎊,而推倒重建費用才不到一半。評價歷史建築保護與利用是否成功,實質是探討局部建築和整體城市、時代特征是否適應的問題。如果費半天力氣換來的是一座與周圍格格不入的建築,結果還是失敗的。”
商業底線在於保留韻味
西琉璃廠附近胡同內的安徽會館建於同治年間,如今它沉睡在一片破舊的民宅中。很多在附近生活數年的住戶,竟然不知道它的存在。晴朗的午後,陽光打在朱紅色屋檐上,反射出明媚的光輝,不時有幾只鳥兒寥落的飛過。沒有門牌號、沒有游客,在花費數年時間維修之後,一扇朱紅色鐵門將這裡的身世與外界隔絕。“老建築保護和利用歷來是一個充滿矛盾的話題。城市不發展就會沒有生命力,而因為發展而傷害了獨特的風貌,也會消磨城市的生命力。”中國人民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研究所所長金元浦說,“要夷平一片建築或圍起來保護很容易,而要將建築融合為城市的一部分才是最大的考驗。”
美國紐約蘇荷區是游客參觀的必到之處,然而這片鋼鐵生產基地變成藝術家聚集地後,也曾破舊不堪,甚至險些化為烏有。“20世紀60年代,洛克菲勒財團旗下的大通銀行計劃重新打造蘇荷區,用成片新建的辦公樓和豪華公寓取代舊廠房。在當地居民、藝術家和建築師的極力反對下,1965年,包括蘇荷區在內的900棟古建築和50多個歷史街區被列入保護名錄。”金元浦說。
1973年,蘇荷區被確定為文化藝術區,屬於重點保護區域。這意味著蘇荷區在整修時,必須堅持“以舊做舊”的原則,建築物原有的外貌不允許再有任何破壞和更改。
在霍建慶看來,老建築保護和商業利用不是非得“你死我活”。現在國內很多著名人文景點都在收取門票,也是創造商業價值的一種形式。
“但通常以這樣方式經營獲利是循序漸進的,很難產生‘裂變’式的經濟效益。而商業化過程中底線就在於,建築本身的韻味不能改變,獲利是為了更好地傳承文化。”霍建慶說。
霍建慶說,目前湖廣會館大部分收益來自於餐飲和茶樓,戲曲演出的收益並不豐厚。“事實上,我們一直在用餐飲和茶樓帶來的收入支持和保護戲曲演出。這兩年又將茶文化、喜壽宴文化引入。而在戲曲演出部分,經典的段落雖然觀眾不多,但是湖廣會館始終保留著這些橋段。老建築無論是利用還是保護,必須對原有文化起到傳承的作用。”
“文化產業是公認的新興產業,文化產業化是未來的必然趨勢。美、法、德等國家文化休閒服務經濟產業已占到GDP的70%左右,與他們相比我們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但是我們要時刻提示自己,每一座建築和城市在商業發展時必須保留自己的特點,與其‘模仿別人’,不如‘做好自己’。”金元浦說。
在密密麻麻的各色商店、來往如梭的車流人流中,北京新街口北大街53號難掩落寞。兩扇青綠色的鐵門虛掩著,門前停著幾輛破舊自行車,之後是一尊三米余高徐悲鴻先生的塑像。塑像前兩束略微凋零的鮮花告訴別人:不久前,這裡有人來過。
這裡是徐悲鴻紀念館。院內告示欄清晰地寫道:9月起,徐悲鴻紀念館正式關閉。在館內工作了20余年的馮靜明說,原址上將重建一座相當於原使用面積兩倍的新館。“其實這次拆掉的紀念館已經不是真正意義的老建築了。徐悲鴻先生的故居在東城區受祿街,生命中最後6年他一直住在那裡,但多年前已經拆除了。”馮靜明說。
據“2010會館保護與利用論壇”上公布的數據顯示,作為全國會館最為集中的北京西城區宣南地區,會館數量比新中國成立初期減少了四分之三,比上世紀90年代減少了三分之二。這一地區現存的101個會館中,有94處仍有居民居住,另外7處為商業、辦公利用,預計未來只有約四成會館原址能夠避免“拆除”的命運。
即使為數不多幸存下來的會館,命運也大致相似。城市前進的滾滾步伐,讓這些盛名在外,卻已歷經歲月洗滌的老建築愈顯單薄。
落寞不應成為會館的定語
“砰、砰、砰”,在一陣沉悶的拍擊聲中,值班人員“叮叮當當”提著鑰匙出現,“吱呀”開了門。室內,陽光所及之處,看得見一抹浮塵。
即將拆除的徐悲鴻紀念館占地面積約4000多平方米,館內20余名職工擔負著整座建築管理、維護、保安等工作。紀念館灰體綠頂,裝飾中盡顯“老貴族”的做派。
“紀念館收藏了徐悲鴻先生各個時期的作品總計1000余件。”馮靜明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想要完好的保存這些珍品,恆濕恆溫是首要條件,但是這些年來我們一直做不到,安保工作只能說盡力做好吧。”
參觀是免費的,即使如此,平時一天最多也只有幾十個游客。“這樣的客流量還比不上周圍一家小賣部。現在很多學校規定學生必須來參觀,還要蓋章、簽到。但是很多孩子要麼讓家長代簽,要麼簽了到就走。”馮靜明說。
回顧這些年來老建築的命運,中國文物學會傳統建築園林委員會常務理事馬炳堅仍歷歷在目。“1999年,廣渠門內大街207號四合院數天內被拆,這是目前紅學專家唯一公認的有案可考的曹雪芹故居遺址;2000年,美術館後街22號一座明代兩進深四合院被拆,此前不久多位古建專家曾對這裡精美的磚雕稱奇;2005年,西城區共9間周作人的住房被拆除;2009年7月,梁思成故居也面臨同樣的困境。”
在馬炳堅看來,歷史之所以是歷史,就在於它的連綿和延續,而老建築是最真實的歷史符號和記憶。它們的存在就好像一部厚重的古書,講述著若干年前的故事,割裂自然的延續不是一種明智的選擇。
“一些發達國家在發展初期也發生過類似的情況。二戰之前的150多年裡,英國老建築的保護工作也一度不盡如人意,20世紀全英國有六分之一的別墅被毀壞。”馬炳堅說。“但是隨著人們在物質和精神生活越發富足,才意識到很多熟悉的東西已經蕩然無存,才感到後悔和遺憾。”
“後來為彌補這些過錯,英國在英格蘭和威爾士先後設立了500個保護區,用以保護原有建築和周圍的環境。”馬炳堅說,“可能因為經歷過失去和破壞,人們現在越發懂得珍惜,倫敦整座城市都成為了一座博物館。”
讓老建築體面地生存
郭沫若故居很有些鬧中取靜的意味:朱紅色大門,灰色院牆,在這座占地7000余平方米的兩進四合院內,處處可見茂盛的玫瑰叢和銀杏樹。在這片喧鬧的地段,它如同人群中一位干淨而體面的老人。
副館長趙笑潔說,作為北京市八大名人紀念館之一,郭沫若紀念館每年都能享受到政府的資助,待遇算很優越了。
“但是因為建築本身屬於文物,至少要做到‘5年一小修,10年一大修’。按照這樣的標准,即使只定期加固結構和給房子挑頂,所需要的經費就在1000萬元左右,而實際資金連一半都達不到。所以只能先挑最嚴重的問題解決。”趙笑潔說。
在微寒的秋末,紀念館內的銀杏葉已漸次泛黃,樹間千百片“小扇面”搖搖欲墜。兩只慵懶的貓踱著碎步,在石階、花叢間悠然自得。垂花門前兩口不成對的銅鐘左右為伍,與兩株上了年歲的松柏相伴。垂花門內,舊時的辦公室、臥房以及郭沫若夫人的寫字間依然如故。
“老建築本該以這樣的姿態存在。無論是修繕、翻新還是利用,都不該忽視建築本身的特質,這樣才能讓每一座建築‘體面’的生存。但要用這樣的標准來衡量我國諸多老建築的生存狀態,只能用‘委曲求全’來形容。”馬炳堅說。
幾年前,馬炳堅曾經概括過四合院建築工程中的十大“濫用”,包括了從建築材料、官事做法、彩畫、到雕刻、格局等方面。結果發現,這樣與歷史和文化不符的“濫用”在修繕和建造中比比皆是,很多施工方和操作工人對於建築文化缺乏起碼的了解。
以彩畫為例,中國古建築在構件上畫彩畫有嚴格的實施標准:皇家建築多用和玺彩畫、重要衙門建築多用旋子彩畫,而皇家園林和王府的次要建築一般采用蘇式彩畫等。但是近幾年的四合院修繕工程中,蘇式彩畫隨處可見,等級超越了王府。有的四合院甚至在屋內嵌滿了各朝代各色龍紋雕刻999條。
這種用拙劣的堆疊和粗糙的工藝拼湊而成的作品,被評為“毫無生命和尊嚴的建築。”“建築本身源自什麼朝代的風格、什麼身份的人住、和周圍環境是什麼樣的關系,都有嚴格的標准,好的建築會自己講故事。”馬炳堅說。
“好建築會藏著很多故事,每一個擺件、匾額都可能還原一段歷史細節。”湖廣會館大戲樓總經理霍建慶說。。穿過湖廣會館悠長的走廊,200年歷史的大戲樓赫然眼前。戲樓主體建築群雕梁畫棟、磨磚對縫青水牆。四周牆壁是如新的博古彩繪,戲台上方是“霓裳同詠”匾,抱柱楹聯長達一丈六尺。燈光亮起後更盡顯當年的金碧輝煌,精致玲珑間難掩王府風范。
“1994年到1996年5月,湖廣會館經歷了兩年的修繕期,花費數千萬元。在此之前這裡居住了35戶居民,柱子上到處綁著繩子晾衣服。大戲樓成了制本廠的倉庫,堆滿了紙張,據說‘前腳踏進戲樓就被灰塵沒了’。”霍建慶說。
“保護和利用老建築,無論是‘今為古用’還是‘古為今用’,前提都是尊重建築本身的特點。”馬炳堅說,“但這需要龐大的經濟支持。英格蘭紐卡斯爾一座由面粉廠改造的現代藝術博物館,為保留‘波羅的面粉廠’的字樣,就花了7000多萬英鎊,而推倒重建費用才不到一半。評價歷史建築保護與利用是否成功,實質是探討局部建築和整體城市、時代特征是否適應的問題。如果費半天力氣換來的是一座與周圍格格不入的建築,結果還是失敗的。”
商業底線在於保留韻味
西琉璃廠附近胡同內的安徽會館建於同治年間,如今它沉睡在一片破舊的民宅中。很多在附近生活數年的住戶,竟然不知道它的存在。晴朗的午後,陽光打在朱紅色屋檐上,反射出明媚的光輝,不時有幾只鳥兒寥落的飛過。沒有門牌號、沒有游客,在花費數年時間維修之後,一扇朱紅色鐵門將這裡的身世與外界隔絕。“老建築保護和利用歷來是一個充滿矛盾的話題。城市不發展就會沒有生命力,而因為發展而傷害了獨特的風貌,也會消磨城市的生命力。”中國人民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研究所所長金元浦說,“要夷平一片建築或圍起來保護很容易,而要將建築融合為城市的一部分才是最大的考驗。”
美國紐約蘇荷區是游客參觀的必到之處,然而這片鋼鐵生產基地變成藝術家聚集地後,也曾破舊不堪,甚至險些化為烏有。“20世紀60年代,洛克菲勒財團旗下的大通銀行計劃重新打造蘇荷區,用成片新建的辦公樓和豪華公寓取代舊廠房。在當地居民、藝術家和建築師的極力反對下,1965年,包括蘇荷區在內的900棟古建築和50多個歷史街區被列入保護名錄。”金元浦說。
1973年,蘇荷區被確定為文化藝術區,屬於重點保護區域。這意味著蘇荷區在整修時,必須堅持“以舊做舊”的原則,建築物原有的外貌不允許再有任何破壞和更改。
在霍建慶看來,老建築保護和商業利用不是非得“你死我活”。現在國內很多著名人文景點都在收取門票,也是創造商業價值的一種形式。
“但通常以這樣方式經營獲利是循序漸進的,很難產生‘裂變’式的經濟效益。而商業化過程中底線就在於,建築本身的韻味不能改變,獲利是為了更好地傳承文化。”霍建慶說。
霍建慶說,目前湖廣會館大部分收益來自於餐飲和茶樓,戲曲演出的收益並不豐厚。“事實上,我們一直在用餐飲和茶樓帶來的收入支持和保護戲曲演出。這兩年又將茶文化、喜壽宴文化引入。而在戲曲演出部分,經典的段落雖然觀眾不多,但是湖廣會館始終保留著這些橋段。老建築無論是利用還是保護,必須對原有文化起到傳承的作用。”
“文化產業是公認的新興產業,文化產業化是未來的必然趨勢。美、法、德等國家文化休閒服務經濟產業已占到GDP的70%左右,與他們相比我們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但是我們要時刻提示自己,每一座建築和城市在商業發展時必須保留自己的特點,與其‘模仿別人’,不如‘做好自己’。”金元浦說。
熱門文章
熱門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