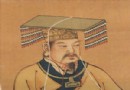一條黃瓜的千年承載
日期:2016/12/13 23:11:21 編輯:古建築紀錄
在《紅樓夢》裡有這樣一個場景,怡紅院低級丫鬟小紅,有一次去廚房對廚娘說,寶二爺晚上想吃酸酸的涼涼的菜,廚娘說知道了。這“酸酸的涼涼的”是個什麼菜?有養生專家考證說,是腌黃瓜。筆者以為,多半是對的。文學名著所記述的那些舌尖上的美味,總是令我神往,唯獨這個,我神往不起來。把脆生甜香、水靈靈的黃瓜,腌制成蔫不溜秋的樣子,撇開它的食用價值好壞不說,單就視覺感官而言,多少有些暴殄天物。
我喜歡吃黃瓜,生吃、炒雞蛋、煮湯,有時候還用它來下面條。每次吃黃瓜,都不由生出許多感慨,就這麼一條小小的黃瓜,它的歷史承載卻是那麼的遙遠厚重。千余年坎坎坷坷風風雨雨,一路走來,黃瓜的歷史,如夢一般飄搖至眼前,回聲在耳畔。就讓我們一起迷起眼睛,曬著暖暖的秋陽,來追尋黃瓜的故事。
絲綢之路的見證 說起絲綢之路,我們打心眼裡自豪,東西方經濟文化的交流碰撞,始於斯,盛於斯。相傳,漢武帝派張骞出使西域,歷經千難萬阻,才有了絲綢之路,張骞帶回的物產裡,就有黃瓜,當時稱為“胡瓜”。
今天我們享受黃瓜的清脆可口時,有無“以告我先輩,得來之不易”的感歎?黃瓜,自打從宮廷推廣至民間,早已沒有了鐘鼓馔玉的富貴,沒有了絲竹管弦的嘈雜,更沒有了討價還價的紛擾,但它對絲綢之路的承載,卻和大蒜(葫)、芫荽(胡荽)、芝麻(胡麻)、核桃(胡桃)、蠶豆(胡豆)以及石榴、葡萄、無花果等一樣,成了永遠抹殺不去的歷史見證。
族群認同的蘊藉 關於黃瓜之名的來歷,有兩則轶聞。
或曰,胡瓜更名為黃瓜,始於後趙,相傳後趙王朝的建立者石勒,乃是羯族,在襄國(今河北邢台)登基做皇帝後,對民眾稱羯族為胡人大為惱火,於是制定法令:說話寫文章出現“胡” 字者,殺不赦。這跟文字獄沒啥區別。某日,他用黃瓜招待襄國郡守樊坦(漢族),並問:“卿知此物何名”?顯然意在試探,樊坦恭敬回答:“紫案佳肴,銀杯綠茶,金樽甘露,玉盤黃瓜。”石勒聽後,滿意地笑了。又或曰,隋炀帝某次用膳,見一盤菜很是陌生,就問廚子,廚子說是涼拌胡瓜。隋炀帝不高興了,為啥?他有一半血統出自胡人呢,母親獨孤氏是鮮卑族,遂命改名為黃瓜。唐代吳兢的《貞觀政要》說的很清楚:“帝性好猜防,專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謂胡床為交床,胡瓜為黃瓜,築長城以避胡。”
孰真孰假,暫且不論,前者《晉書》未記,後者顯為罵街,反正此後胡瓜之名不見了,黃瓜成為定名,讓我又生出了一種親近感。無論黃瓜之黃,出於其自身的顏色,還是出於黃帝子孫對先祖的尊崇,少數民族對華夏文明的深層次心理上的拜服,這是毋庸置疑的。被異族認同,總是一件好事,從這個角度來說,趙炎以為,黃瓜的確承載了榮宗耀祖,承載了我們民族兼容並蓄的胸懷與先進的價值觀。黃瓜好吃,但蘊藉著的歷史秘密和社會心理之規律,不可不察。如在隋朝之後,凡漢族主政時期,士大夫提及黃瓜,總會說一句“古稱胡瓜”以示出典;凡少數民族居統治地位的時期,官方一律稱為黃瓜。
文藝美的載體 黃瓜入文入詩也入畫,多麼的惬意,何等的動人!趙炎讀古人的黃瓜詩,總忍不住品味把玩,神往其中的美。
唐代章懷太子有《黃台瓜詞》:“種瓜黃台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猶良可,四摘抱蔓歸”。把種瓜摘瓜的過程描寫得搖曳生姿,有著田園般淡淡的美感。王建的《宮詞》寫皇家風物:“酒幔高樓一百家,宮前楊柳寺前花。內園分得溫湯水,二月中旬已進瓜。”這內園是皇家的園圃,詩中的“瓜”,是用溫泉水加溫在溫室種植的黃瓜,用來供應宮廷的貢品。
北宋蘇轼的《浣溪沙》寫道:“簌簌衣巾落棗花,村南村北響缫車,牛衣古柳賣黃瓜。酒困路長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門試問野人家”。那須眉如雪的賣瓜者,慵懶口渴的旅客,道邊簌簌有聲飄動著的柳絲,和徐州府熙熙攘攘的熱鬧一加對比,分明就是塵世中的桃源啊!南宋陸游既喜歡黃瓜的脆:“白苣黃瓜上市稀,盤中頓覺有光輝;時清闾裡具安業,殊勝周人詠采薇。”又喜歡黃瓜的田園美:“園丁傍架摘黃瓜,村女沿籬采碧花。城市尚余三伏熱,秋光先到野人家。”
清代乾隆皇帝也有詠《黃瓜》詩:“菜盤佳品最燕京,二月嘗新豈定評。壓架綴籬偏有致,田家風景繪真情。”寫出了農家風致的真情;吳偉業所書《詠王瓜》:“同摘誰能待,離離早滿車。弱籐牽碧蒂,曲項戀黃花。客醉嘗應爽,兒涼枕易斜。齊民編月令,瓜路重王家。” 極力渲染黃瓜的花朵之美;黃之隽有《種王瓜籬豆諸蔬》:“終作抱甕身,五鼎未列筵。瓜瓠如有知,為我根蔓牽。蔓則蔽蒼野,根則入黃泉。以告我父母,貧賤子可憐。”這種抒情方式,有些隔著遙遙時空的意味了,盡顯滄桑之美。
民國“文學洛神”蕭紅,這樣描寫童年時故鄉的黃瓜:“願意開一個黃花,就開一個黃花,願意結一個黃瓜,就結一個黃瓜。若都不願意,就是一個黃瓜也不結,一朵花也不開,也沒有人問它……只是天空藍悠悠的,又高又遠。”以此苦澀筆觸抒發人生情懷,當真讓人讀來心裡堵得慌!
民間傳說亦相關 話說明代萬歷年間,有位姓韓的老大趕完集,買了碗熬豆腐吃。飯桌對面有個地主老財,一邊吃著肉絲拌黃瓜,喝著酒,一邊自得洋洋地自語道:“窮人窮,富人富,有錢的吃黃瓜,沒錢的吃豆腐。”韓老大一聽,知道這是在取笑自己,她也不急,也不氣,對跑堂的說:“我要一百五十盤肉絲拌黃瓜。”跑堂的說:“沒那麼多黃瓜,再說您老人家要這麼多有啥用呢?”韓老大說:“我在集上買了一頭公豬。那豬的主人說,這頭公豬最愛吃拌黃瓜。這就叫:窮人窮,富人富,公豬愛吃黃瓜。趕豬的只吃豆腐。”飯館裡吃飯的人都哄堂大笑起來。老財主氣紅了臉,端起酒壺一口氣喝個淨光,灰溜溜地跑出飯館去了。
黃瓜裡的經濟學 所謂物稀為貴,黃瓜也一樣。古代沒有大棚種植,一反了季節,黃瓜就成稀罕物,商品經濟的特點也就顯露了。
明初某年的臘月,朱元璋似乎犯了賈寶玉的毛病,突然感覺沒胃口了,只想吃黃瓜。這下苦了太監們,宮裡宮外四處尋找,差點把南京城挖地三尺,終於買到三根黃瓜,花了多少錢呢?不多,三百兩銀子,其中第三根還是求買的,人家小販原本是想留著自己吃。這叫什麼?做生意的人都知道,那叫奇貨可居。清代嘉慶間《京都竹枝詞》說:“黃瓜初見比人參,小小如簪值數金。微物不能增壽命,萬錢一食亦何心?”說的一點不誇張,反季節的黃瓜是比燕窩魚翅還貴。
在《清代野記》裡還有個故事,說舉子方朝觐某年二三月間到北京參加會試,有一天攜僕人去前門購買日用品,中午飯點,選一小館子吃飯。方對僕人說,京城物價貴,你要悠著點,別亂點菜。等主僕二人各自用餐畢,一算賬,傻眼了,共消費“五十吊零”。方對伙計說,怎麼這麼貴?你們是黑店呀!伙計說,哪裡話來?您的消費不足十吊,但您的僕人點的都是貴的菜呢。方大怒,叫來僕人好一陣訓斥。僕人很委屈,說生怕花冤枉錢,葷菜一個沒敢點,就點了四盤黃瓜。於是,伙計解釋說,京城黃瓜在夏天比較便宜,如今是正月間,一小盤黃瓜需要“外省制錢一千也”。僕人聽了直吐舌頭。
僕人不認字,不懂反季節菜蔬貴的經濟原理,倒還可以理解。而讀書人也不懂,就有點那個了,對吧?
清朝文人筆記裡就提到一位不懂經濟的才子,說這個才子初春時節去北京,當地文化界朋友請喝酒,那是必須的。一幫人找了家飯館坐定,出於禮貌,堅持讓這位才子點一道菜。才子推辭不過,又先入為主想當然,以為黃瓜是最便宜的。為了不讓眾人破費太多,就點了盤涼拌黃瓜。不料,卻把所有人都給得罪了。因為,他點的一盤涼拌黃瓜,其價值差不多可以再開一桌酒席了。
曾是外交使者 1993年,徐贻聰先生擔任中國駐古巴大使,曾用黃瓜作為中古兩國人民友好的見證,演繹出一段外交史上的佳話。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1994年下半年的一天晚上,勞爾·卡斯特羅應邀到中國駐古巴使館做客,散步時發現菜園子裡有細長的黃瓜,就很好奇,當即生吃品嘗,對其甘甜的滋味贊不絕口。原來古巴的黃瓜都是比較短粗的品種,味道苦澀。因為有了這個插曲,徐贻聰大使就從國內采購了許多黃瓜種子,通過古巴的華裔邵黃將軍,在古巴各地進行推廣種植,不僅對古巴農業,而且對古巴的旅游業也起到了很特殊的作用。
為此,古巴國務委員會還給徐大使頒發了一個“徐贻聰黃瓜”的證書。徐大使拿到證書後致答謝詞:“黃瓜不是我發明出來的,只是從中國帶回來一些種子;而且種子也不是我買的,是我夫人買的。我獲得證書應該是‘無功受祿’了。但是這件不大不小的外交上的事情,表達了古巴人民對中國的友好感情。黃瓜已經是中古兩國人民之間深情厚誼的體現。”
- 上一頁:揭秘:中國古代如何獎勵優秀體育選手?
- 下一頁:傳統婚禮新娘為何蓋紅蓋頭?
熱門文章
熱門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