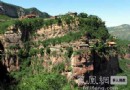西藏桑耶寺的造像與壁畫藝術
日期:2016/12/14 17:29:25 編輯:古建築紀錄
一、桑耶寺的興建與建築格局
桑耶寺位於西藏山南地區扎囊縣桑耶鎮桑耶村,雅魯藏布江北岸,距離山南地區行署所在地澤當38公裡,距離扎囊縣25公裡,海拔3676米。它不僅是藏族歷史上第一個佛法僧俱全的著名寺院,也是西藏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國家級雅砻風景區之一。
公元八世紀中葉(750),吐蕃第三十八代贊普、文殊菩薩化身的赤松德贊為施主,迎請薩霍爾(孟加拉國)國王古瑪特其之子大堪布寂護和烏仗那(今巴基斯坦境內)蓮花生大師入藏,三人共同設計、堪輿和興建了西藏歷史上第一座寺院桑耶寺。
桑耶寺,藏文意思是“無邊寺”、“超出意想”等含義,全名為“桑耶敏久倫吉朱白祖拉康”,意思是“不變自成的桑耶寺”。漢譯寺名曾有“桑葉”、“桑巖”、“桑木耶”等。
從桑耶寺的建築風格來看,該寺模仿了古代印度著名寺院烏旦達波日(飛行寺)的建築風格與格局,寺廟中央主殿的建築結構為三層三樣式:底層殿和塑像為西藏風格,中層殿為漢地風格,上層殿為印度風格,融合吸收了古代印度、漢地、藏地以及西域寺院建築的風格特征和營造手法。因而,也有學者把桑耶寺叫“三樣寺”,據說有“三羊開泰”之意。
桑耶寺建築規模宏大,殿塔林立,以金碧輝煌的“烏孜”大殿(烏孜仁松拉康)為主體,組成一座龐大、完整的建築群體,總面積為25000多平方米,整個寺院的布局,是按照佛教的世界結構設計而成。有學者認為是以印度摩揭陀的飛行寺為藍本;也有人認為,桑耶寺的建築形式是嚴格按照佛教密宗的“曼陀羅”壇城而建造布局的。例如,位於全寺中心的“烏孜”大殿,象征宇宙中心的須彌山:“烏孜”大殿四方各建一殿,象征四大部洲;四方各殿的周圍,各建兩座小殿,象征八小洲(即大圓滿佛殿、大能仁佛洲殿、大輪轉經佛殿,彌勒持法洲殿和法、報、化三身之大輪轉經佛殿);主殿左右兩側又建小殿,象征太陽和月亮;主殿的四方又建有紅、綠、黑、白四色神奇寶塔,以鎮服一切外道邪魔。為防止天災人禍的發生,在寺院圍牆上修建108座小佛塔,在佛塔的周圍設立金剛杵,每個金剛杵下置一捨利,象征佛法堅固不摧。桑耶寺的其他建築還有護法神殿、僧捨、倉庫等。最後在這些建築周圍,又圍上了一道橢圓形圍牆,象征鐵圍山,圍牆的四面各開一座大門,東門為正門。
圍牆外還有三位王妃所建的三界銅洲殿(現為農場糧庫)、遍淨響銅洲殿(已被毀)、哦采金洲殿(現為鄉小學)。桑耶寺院東南為西藏四大名山之一的哈布日山,山背後有大堪布寂護的靈塔和小型佛殿。寺院北方有長壽修行處聶瑪隆溝,東北山地為隱居修行之地青樸。
關於桑耶寺的興建歷史,除藏族史書《巴協》和《桑耶寺志》專門記述外,《賢者喜宴》、《西藏王統記》、《西藏王臣記》、《蓮花遺教》、《銅洲遺教》、《五部遺教》、《遍照護面具》等教史也都有記載。
自公元八世紀建寺以來,桑耶寺逐漸成為吐蕃中期宗教文化的中心,赤松德贊以桑耶寺為根據地,大力扶持佛教,除了從印度迎請蓮花生、寂護等大師外,還從唐朝請來大批的漢族高僧,翻譯佛教典籍、傳播教義、興佛滅苯。作為西藏第一座佛法僧三寶俱全的寺院,首創了藏族人出家為僧的先例,建立了完整嚴謹的僧伽制度,廣譯經論,講經說法,建立專修道場,形成了規模相當的寺院修行體制。諸如,修建經藏傳規大壇城,律藏傳規經堂,論藏傳規講堂等。從藏文史料來看,當時的桑耶寺已經開設了經、律、論三藏的道場,同時也開辟了譯經、學經、辯經、修行、閉關、受戒等宗教場地,使得初傳的外來佛教開始在西藏站穩了腳跟並迅速發展,終於形成了藏傳佛教“前弘期”的繁榮局面。
朗達瑪興苯滅佛後,吐蕃王朝日趨衰落,桑耶寺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人為破壞以及地震等自然災害,日趨凋零。直到藏傳佛教後弘期,桑耶寺再次成為前藏佛教復興的主要道場,並受到了不同教派的護持和修繕。諸如,後弘期的薩迦派、噶舉派、格魯派等高僧大德和當地的貴族頭人們都曾對桑耶寺進行過不同規模和程度的修葺、擴建工作,使得這座吐蕃時期的古老寺院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又煥發出新的生機。經過一千多年的滄桑變故,桑耶寺不僅成了藏傳佛教寧瑪派的祖庭,同時也成了薩迦、噶舉、格魯三派合一的著名道場,對藏族後期的政治經濟和宗教文化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在藏傳文化史和佛教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深受廣大信教群眾的無比崇敬和虔誠朝拜。
二、桑耶寺的造像藝術
從松贊干布到赤松德贊時期,是藏傳佛教早期藝術發展的一個重要歷史階段,尤其是桑耶寺的興建,不但標志藏傳佛教僧團的建立,同時也象征著藏傳佛教真正的興起。可以說,桑耶寺的修建將前弘期佛教推向了一個高潮,而藏傳佛教藝術也正是在這一時期開始走向了本土化、民族化的進程。
據《王統世系明鑒》提供的有關桑耶寺泥塑造像的材料看,當時桑耶寺的各大殿堂內並不像今天有那麼多青銅造像,而多數造像為泥塑彩繪作品。例如在修桑耶寺之前,按照尊勝度母的教誡,先修造了一座叫阿扎耶巴洛的神殿,該殿所供的塑像就有:主尊觀音菩薩,右為度母,左為具光母,再右為六字大明咒,再左為馬頭明王,共計五尊,它的上面又修造無量光佛主從五尊。從桑耶寺三層不同佛像的布局看,當時的佛像布局都有較嚴謹統一的設計和修行目的。例如:
桑耶寺下層主供有用寶泥包裹的釋迦牟尼像,相好端嚴。右為彌勒、觀音、地藏、喜吉祥,三界尊勝憤怒明王等;左為普賢、金剛手、文殊、除障、無垢居士、不動憤怒王等,主從十三尊佛像按藏地式樣建造。
中層的主要塑像有:主尊大日如來,右為燃燈,左為彌勒。前為釋迦牟尼佛、藥師佛、無量光佛三尊。其左右兩方為八大菩薩近侍弟子、無垢居士、喜吉祥菩薩、忿怒金剛,這一層是按漢地風格建造。
密宗殿中,塑有十方如來,閻羅地獄諸尊,桑耶諸護法像。上層的主尊為大日如來,每一面有兩個弟子,觀音菩薩八大近侍弟子,裡面的佛像有菩提薩埵金剛幢等十方諸佛、菩薩、不動憤怒明王及金剛手等,都是按印度的造像風格建造的。
桑耶寺的泥塑造像並不限以上所說,其它佛殿看來也有不少。只是經過了一千二百多年的變故,原有的泥塑被毀或重修過多次,有的泥塑已被銅像取代,而且每一層的佛像布局也都不再是吐蕃時的格局。加之後來寧瑪派、薩迦派、格魯派宗教領袖都執掌過桑耶寺的教權,所以各教派的歷史人物又增加到佛像的行列之中,甚至原有的一些泥塑造像被取消。例如一層佛殿主供的釋迦佛,文革時頭部被砸毀,後經修復。在釋迦像前方左右兩邊,各有泥塑菩薩五尊和護法神一尊。菩薩像高達4.2米,如今我們見到這幾尊立像是近年重新塑造的,是否保持了過去的原貌就不得而知了。又如二層現主供的是蓮花生大師,左為降欽·晉美林巴泥塑和釋迦牟尼佛合金銅像,右為隆欽·繞绛巴泥塑和無量光合金銅像。完全打破了桑耶寺初期二層佛殿的佛像供奉布局。
又如,今天烏孜大殿內經堂的造像左側是:松贊干布、赤松德贊、寂護、白路扎那、唐東傑布等。右側是仲傑瓦窮乃、鄂勒巴協饒、降欽仁布欽、阿底峽、宗喀巴等塑像。這些歷代贊普和各大教派的祖師像都是後來逐漸增添上去的,因而也打破了早期塑像的風格與供奉佛像的布局模式。
我們在前面曾提到桑耶寺的修建使得藏傳佛教藝術開始走向民族化的道路。這正如法國藏學家石泰安所言,桑耶寺中的造型奠定或確立了這種藏族藝術風格的基礎。在塑造佛教中的諸佛菩薩時運用了活生生的藏人模特兒。如藏文史料《漢藏史集》所言:
從亨本比哈比來了一位名叫藏瑪堅的漢族人,手裡拿著一個盛滿一小缽畫料的大缽和一捆畫筆。並說“我是世界上最傑出的雕塑家和畫家。我是吐蕃國王建寺院的藝術家。”因此,他應召而來。國王、大師(蓮花生)和這位藝術家一起在宮殿中就如何繪塑神像問題進行了協商。這位藝術家說:“這些眾神按印度風格,還是按漢族風格造像?”大師言道:“正如佛陀乃出生為印度一樣,應按印度風格繪塑”。國王說道:“大師,我希望好斗的藏人成為佛教信徒,還是讓他按照藏族風格繪塑諸神吧。”(大師)因而說道:“召集吐蕃百姓,按藏族風格繪塑諸神。”於是,在召集的吐蕃人中,以俊美男子麥悉諾察布為模特兒,塑造了阿耶婆羅卡薩巴尼神像;以漂亮女子交繞·布瓊為模特兒,在左面塑造了具光女神塑像;以美貌女子交繞·拉布美為模特兒,在右邊塑造了救度佛母塑像;以塔桑·悉諾列為模特兒,在救度母右側塑造了六字阿耶波羅塑像;以美葉哥為模特兒,塑造了守門神阿耶波羅馬鳴王神像。
顯而易見,這則史料的價值在於吐蕃時期的藏族統治者已明確意識到印度佛教藝術必須與藏族生活相結合,必須具有民族化的個性特征,只有這樣佛教造像才有可能在藏地深入持久並感化更多的藏族信眾。
據調查,桑耶寺的石刻造像數量龐大,題材廣泛,內容豐富,其造像水平均居西藏首位。初步統計,石刻造像總數大約在1500余尊,大多為佛、菩薩、羅漢、天王、護法神及蓮花生、阿底峽、米拉日巴等歷史宗教人物。
在桑耶寺烏孜大殿內圍牆回廊南面的兩間房屋裡藏有大量的石刻造像,這些造像一般雕刻在長0.4-0.82米之間的長方形石板上,其題材多為佛陀造像,一般稱為“千佛像”,大約有900多尊,此外,還有度母、觀音菩薩、四大天王、羅漢等像。
千佛像大多刻在0.4至0.5米長的長方形石板上。總體看,千佛造像的風格、服飾、表情基本一致。造像手法為半浮雕,有圓形背光,高發髻,面方圓,著袒右肩袈裟,結跏趺坐於仰蓮花座上,手執法印,有觸地印、辯論印、施捨印、無畏印、轉法輪印五種手印。
四大天王造像,一組4尊,皆為高浮雕,其風格與藏傳佛教壁畫中的形象基本相同,造像古樸,刀法簡潔。菩薩造像1尊,為高浮雕,頭戴塔式寶冠,上身袒露,下身著長裙,天衣披飄帶,雙耳佩環,右手於胸前,左手下垂執一朵蓮花,造像優美輕盈,帶有鮮明的印度佛教造像的神韻。
桑耶寺現存的羅漢石刻造像有6尊,都為高浮雕精品。由於藏地十方羅漢像是由漢地傳來,故其造型、神態、衣飾均與內地的羅漢像相同。裸體男像是這些造像中較特別的造像,雙手捧寶瓶於胸前,跣足站立在覆蓮座,全身赤裸,頭戴寶冠,垂發披肩,腰部系馬尾裙,面相凶狠。此類造型在石刻中並不常見。
此外,在桑耶寺千手千眼菩薩殿內,還保存有部分石板造像藝術。題材以西藏歷史的著名宗教人物為多,還有一些綠度母、佛塔造像。人物造像比較寫實,如米拉日巴尊者像,周圍刻有雲、山、日、月圖案,米拉為短卷發,眉目清秀,著袒右肩袈裟,右肩並斜披一條寬帶;右手執於右耳邊,左手持缽,右腳外露,游戲坐於一塊鼠皮上。傳說,這尊造像就是米拉在山洞裡苦修的真實形象。阿底峽尊者造像的頭部有背光和橢圓形頭光,頭戴紅色尖頂帽,內穿圓形衫,外著寬袖長袈裟,雙手作轉法輪印,結跏趺坐於蓮花座上,造像左右分別刻有轉經輪和塔式寶瓶。湯東傑布的造像之所以讓他右手執鐵索鏈,左手捧瓶,其因在於他以修建鐵橋聞名全藏。故而突出他右手上的鐵鏈,造像生動寫實。
相形之下,蓮花生大師和阿底峽尊者的造像更趨於程式化,而缺少強烈的感情沖動。桑耶寺的瑪尼石刻除部分為吐蕃時期的作品外,大部分是後弘期以後的作品,這些作品尤其是千佛像具有統一的造像風格,顯得嚴謹規范、布局構圖都很統一,有可能出自同一位雕刻家之手。
由於吐蕃時期留存下來的泥塑造像很少,所以我們只能更多地借助有關藏史文字材料加以研究,故而很難對吐蕃時期的佛教泥塑的源流及風格給以全面准確的把握,但大體上可以認為,吐蕃時期的泥塑造像主要受到了來自尼泊爾、印度、克什米爾、於阗、漢地的影響較大。松贊干布時興建的大、小昭寺、昌珠寺等寺的建築藝術和泥塑造像,則多受尼泊爾、漢地、印度的影響。赤松德贊時興建桑耶寺、噶窮寺,赤熱巴巾時修建白美扎西格沛寺等除受上述影響外,克什米爾、於阗、斯瓦特造像藝術的影響則更突出一些。從公元7世紀松贊干布開始到9世紀朗達瑪滅佛,藏傳佛教藝術經歷了約三百年的歷史,作為前弘期的佛教藝術包括泥塑造像,更多地是學習借鑒引進域外佛教藝術手法和風格的時期,還沒有完全形成本民族的造型技藝和美學風格,雖然赤松德贊時已表現出強烈的民族化要求,但從發展的角度講,那也僅僅是邁向民族化藝術之路的第一步。就整個吐蕃時期的泥塑造像而言,他更多地體現了崛起時代吐蕃人的一種寬容、博大、多元的文化精神和素樸、虔誠、渴望超越生死輪回的審美理想。正如聖觀音贊所言:
為利益眾生建築此像,
我在您的面前虔誠頂禮。
您這三尊諸佛的密意,
化成百看不倦的美妙身像,
您具有善巧智慧的慈悲,
懇請您眷顧有情眾生。
您是世間眾生的依怙,
備受各種苦難煎熬的,
災難深重的有情眾生,
懇請您用慈悲來拯救。
三、桑耶寺的壁畫藝術
藏傳佛教的壁畫藝術,主要是指繪制在寺院牆壁上的宗教美術作品。這些壁畫是根據寺院建築的總體設計的需要,以及不同“札倉”顯密修行的要求、儀軌等繪制而成的宗教美術作品。一般而言,藏族壁畫大多集中在每一個寺院的大經堂中。不同的教派寺院以及下屬“札倉”,有不同內容和風格的壁畫作品。按照藏族寺院的一般布局,寺院的壁畫往往集中在大經堂內,因為大經堂常常是一座寺院的建築中心和學經集會的主要場所。經堂的正中一般供奉釋迦牟尼像,兩旁是菩薩像和祖師像,有的寺院內供奉歷代贊普像。大門外側的牆壁上一般繪有四大天王像,大門內側的牆壁上繪有護法神像。有些寺院外的轉經回廊上也都繪有大量的壁畫。藏傳佛教寺院的壁畫內容豐富多彩,其藝術技巧與壁畫面積大大超過內地漢傳佛教寺院的壁畫。可以說,壁畫藝術是藏傳佛教藝術中最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
藏族壁畫藝術產生於吐蕃時代,藏王松贊干布在迎娶尼泊爾公主赤尊和唐文成公主後,曾為二位公主修築宮殿、大昭寺、小昭寺以及布達拉宮早期宮殿建築中保存了吐蕃時代最早的一批壁畫藝術。
吐蕃壁畫藝術的興起是伴隨著寺院的興建發展起來的。當時所建的大昭寺、小昭寺、昌珠寺等都繪有大量的壁畫作品。關於吐蕃早期的壁畫作品,我們能從藏文史料中找到不少記錄。《西藏王統記》記載,國王松贊干布為了慶賀大昭寺的興建完工,曾應眾大臣及不同階層人士的請求分別繪制了一批壁畫作品,如史料說:“於四門畫壇城國,令喇嘛等喜悅;殿柱畫金剛撅形,令咒師喜悅;四角畫萬字卍紋,令苯教徒喜悅;又畫網格紋,令藏民喜悅。凡所許人之風規,皆實踐諾言,故護法龍王、藥叉、羅剎等無不欣喜”。大昭寺、小昭寺開光典禮的贊詞中也提到繪制的壁畫內部,如贊詞曰:
桑耶寺位於西藏山南地區扎囊縣桑耶鎮桑耶村,雅魯藏布江北岸,距離山南地區行署所在地澤當38公裡,距離扎囊縣25公裡,海拔3676米。它不僅是藏族歷史上第一個佛法僧俱全的著名寺院,也是西藏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國家級雅砻風景區之一。
公元八世紀中葉(750),吐蕃第三十八代贊普、文殊菩薩化身的赤松德贊為施主,迎請薩霍爾(孟加拉國)國王古瑪特其之子大堪布寂護和烏仗那(今巴基斯坦境內)蓮花生大師入藏,三人共同設計、堪輿和興建了西藏歷史上第一座寺院桑耶寺。
桑耶寺,藏文意思是“無邊寺”、“超出意想”等含義,全名為“桑耶敏久倫吉朱白祖拉康”,意思是“不變自成的桑耶寺”。漢譯寺名曾有“桑葉”、“桑巖”、“桑木耶”等。
從桑耶寺的建築風格來看,該寺模仿了古代印度著名寺院烏旦達波日(飛行寺)的建築風格與格局,寺廟中央主殿的建築結構為三層三樣式:底層殿和塑像為西藏風格,中層殿為漢地風格,上層殿為印度風格,融合吸收了古代印度、漢地、藏地以及西域寺院建築的風格特征和營造手法。因而,也有學者把桑耶寺叫“三樣寺”,據說有“三羊開泰”之意。
桑耶寺建築規模宏大,殿塔林立,以金碧輝煌的“烏孜”大殿(烏孜仁松拉康)為主體,組成一座龐大、完整的建築群體,總面積為25000多平方米,整個寺院的布局,是按照佛教的世界結構設計而成。有學者認為是以印度摩揭陀的飛行寺為藍本;也有人認為,桑耶寺的建築形式是嚴格按照佛教密宗的“曼陀羅”壇城而建造布局的。例如,位於全寺中心的“烏孜”大殿,象征宇宙中心的須彌山:“烏孜”大殿四方各建一殿,象征四大部洲;四方各殿的周圍,各建兩座小殿,象征八小洲(即大圓滿佛殿、大能仁佛洲殿、大輪轉經佛殿,彌勒持法洲殿和法、報、化三身之大輪轉經佛殿);主殿左右兩側又建小殿,象征太陽和月亮;主殿的四方又建有紅、綠、黑、白四色神奇寶塔,以鎮服一切外道邪魔。為防止天災人禍的發生,在寺院圍牆上修建108座小佛塔,在佛塔的周圍設立金剛杵,每個金剛杵下置一捨利,象征佛法堅固不摧。桑耶寺的其他建築還有護法神殿、僧捨、倉庫等。最後在這些建築周圍,又圍上了一道橢圓形圍牆,象征鐵圍山,圍牆的四面各開一座大門,東門為正門。
圍牆外還有三位王妃所建的三界銅洲殿(現為農場糧庫)、遍淨響銅洲殿(已被毀)、哦采金洲殿(現為鄉小學)。桑耶寺院東南為西藏四大名山之一的哈布日山,山背後有大堪布寂護的靈塔和小型佛殿。寺院北方有長壽修行處聶瑪隆溝,東北山地為隱居修行之地青樸。
關於桑耶寺的興建歷史,除藏族史書《巴協》和《桑耶寺志》專門記述外,《賢者喜宴》、《西藏王統記》、《西藏王臣記》、《蓮花遺教》、《銅洲遺教》、《五部遺教》、《遍照護面具》等教史也都有記載。
自公元八世紀建寺以來,桑耶寺逐漸成為吐蕃中期宗教文化的中心,赤松德贊以桑耶寺為根據地,大力扶持佛教,除了從印度迎請蓮花生、寂護等大師外,還從唐朝請來大批的漢族高僧,翻譯佛教典籍、傳播教義、興佛滅苯。作為西藏第一座佛法僧三寶俱全的寺院,首創了藏族人出家為僧的先例,建立了完整嚴謹的僧伽制度,廣譯經論,講經說法,建立專修道場,形成了規模相當的寺院修行體制。諸如,修建經藏傳規大壇城,律藏傳規經堂,論藏傳規講堂等。從藏文史料來看,當時的桑耶寺已經開設了經、律、論三藏的道場,同時也開辟了譯經、學經、辯經、修行、閉關、受戒等宗教場地,使得初傳的外來佛教開始在西藏站穩了腳跟並迅速發展,終於形成了藏傳佛教“前弘期”的繁榮局面。
朗達瑪興苯滅佛後,吐蕃王朝日趨衰落,桑耶寺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人為破壞以及地震等自然災害,日趨凋零。直到藏傳佛教後弘期,桑耶寺再次成為前藏佛教復興的主要道場,並受到了不同教派的護持和修繕。諸如,後弘期的薩迦派、噶舉派、格魯派等高僧大德和當地的貴族頭人們都曾對桑耶寺進行過不同規模和程度的修葺、擴建工作,使得這座吐蕃時期的古老寺院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又煥發出新的生機。經過一千多年的滄桑變故,桑耶寺不僅成了藏傳佛教寧瑪派的祖庭,同時也成了薩迦、噶舉、格魯三派合一的著名道場,對藏族後期的政治經濟和宗教文化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在藏傳文化史和佛教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深受廣大信教群眾的無比崇敬和虔誠朝拜。
二、桑耶寺的造像藝術
從松贊干布到赤松德贊時期,是藏傳佛教早期藝術發展的一個重要歷史階段,尤其是桑耶寺的興建,不但標志藏傳佛教僧團的建立,同時也象征著藏傳佛教真正的興起。可以說,桑耶寺的修建將前弘期佛教推向了一個高潮,而藏傳佛教藝術也正是在這一時期開始走向了本土化、民族化的進程。
據《王統世系明鑒》提供的有關桑耶寺泥塑造像的材料看,當時桑耶寺的各大殿堂內並不像今天有那麼多青銅造像,而多數造像為泥塑彩繪作品。例如在修桑耶寺之前,按照尊勝度母的教誡,先修造了一座叫阿扎耶巴洛的神殿,該殿所供的塑像就有:主尊觀音菩薩,右為度母,左為具光母,再右為六字大明咒,再左為馬頭明王,共計五尊,它的上面又修造無量光佛主從五尊。從桑耶寺三層不同佛像的布局看,當時的佛像布局都有較嚴謹統一的設計和修行目的。例如:
桑耶寺下層主供有用寶泥包裹的釋迦牟尼像,相好端嚴。右為彌勒、觀音、地藏、喜吉祥,三界尊勝憤怒明王等;左為普賢、金剛手、文殊、除障、無垢居士、不動憤怒王等,主從十三尊佛像按藏地式樣建造。
中層的主要塑像有:主尊大日如來,右為燃燈,左為彌勒。前為釋迦牟尼佛、藥師佛、無量光佛三尊。其左右兩方為八大菩薩近侍弟子、無垢居士、喜吉祥菩薩、忿怒金剛,這一層是按漢地風格建造。
密宗殿中,塑有十方如來,閻羅地獄諸尊,桑耶諸護法像。上層的主尊為大日如來,每一面有兩個弟子,觀音菩薩八大近侍弟子,裡面的佛像有菩提薩埵金剛幢等十方諸佛、菩薩、不動憤怒明王及金剛手等,都是按印度的造像風格建造的。
桑耶寺的泥塑造像並不限以上所說,其它佛殿看來也有不少。只是經過了一千二百多年的變故,原有的泥塑被毀或重修過多次,有的泥塑已被銅像取代,而且每一層的佛像布局也都不再是吐蕃時的格局。加之後來寧瑪派、薩迦派、格魯派宗教領袖都執掌過桑耶寺的教權,所以各教派的歷史人物又增加到佛像的行列之中,甚至原有的一些泥塑造像被取消。例如一層佛殿主供的釋迦佛,文革時頭部被砸毀,後經修復。在釋迦像前方左右兩邊,各有泥塑菩薩五尊和護法神一尊。菩薩像高達4.2米,如今我們見到這幾尊立像是近年重新塑造的,是否保持了過去的原貌就不得而知了。又如二層現主供的是蓮花生大師,左為降欽·晉美林巴泥塑和釋迦牟尼佛合金銅像,右為隆欽·繞绛巴泥塑和無量光合金銅像。完全打破了桑耶寺初期二層佛殿的佛像供奉布局。
又如,今天烏孜大殿內經堂的造像左側是:松贊干布、赤松德贊、寂護、白路扎那、唐東傑布等。右側是仲傑瓦窮乃、鄂勒巴協饒、降欽仁布欽、阿底峽、宗喀巴等塑像。這些歷代贊普和各大教派的祖師像都是後來逐漸增添上去的,因而也打破了早期塑像的風格與供奉佛像的布局模式。
我們在前面曾提到桑耶寺的修建使得藏傳佛教藝術開始走向民族化的道路。這正如法國藏學家石泰安所言,桑耶寺中的造型奠定或確立了這種藏族藝術風格的基礎。在塑造佛教中的諸佛菩薩時運用了活生生的藏人模特兒。如藏文史料《漢藏史集》所言:
從亨本比哈比來了一位名叫藏瑪堅的漢族人,手裡拿著一個盛滿一小缽畫料的大缽和一捆畫筆。並說“我是世界上最傑出的雕塑家和畫家。我是吐蕃國王建寺院的藝術家。”因此,他應召而來。國王、大師(蓮花生)和這位藝術家一起在宮殿中就如何繪塑神像問題進行了協商。這位藝術家說:“這些眾神按印度風格,還是按漢族風格造像?”大師言道:“正如佛陀乃出生為印度一樣,應按印度風格繪塑”。國王說道:“大師,我希望好斗的藏人成為佛教信徒,還是讓他按照藏族風格繪塑諸神吧。”(大師)因而說道:“召集吐蕃百姓,按藏族風格繪塑諸神。”於是,在召集的吐蕃人中,以俊美男子麥悉諾察布為模特兒,塑造了阿耶婆羅卡薩巴尼神像;以漂亮女子交繞·布瓊為模特兒,在左面塑造了具光女神塑像;以美貌女子交繞·拉布美為模特兒,在右邊塑造了救度佛母塑像;以塔桑·悉諾列為模特兒,在救度母右側塑造了六字阿耶波羅塑像;以美葉哥為模特兒,塑造了守門神阿耶波羅馬鳴王神像。
顯而易見,這則史料的價值在於吐蕃時期的藏族統治者已明確意識到印度佛教藝術必須與藏族生活相結合,必須具有民族化的個性特征,只有這樣佛教造像才有可能在藏地深入持久並感化更多的藏族信眾。
據調查,桑耶寺的石刻造像數量龐大,題材廣泛,內容豐富,其造像水平均居西藏首位。初步統計,石刻造像總數大約在1500余尊,大多為佛、菩薩、羅漢、天王、護法神及蓮花生、阿底峽、米拉日巴等歷史宗教人物。
在桑耶寺烏孜大殿內圍牆回廊南面的兩間房屋裡藏有大量的石刻造像,這些造像一般雕刻在長0.4-0.82米之間的長方形石板上,其題材多為佛陀造像,一般稱為“千佛像”,大約有900多尊,此外,還有度母、觀音菩薩、四大天王、羅漢等像。
千佛像大多刻在0.4至0.5米長的長方形石板上。總體看,千佛造像的風格、服飾、表情基本一致。造像手法為半浮雕,有圓形背光,高發髻,面方圓,著袒右肩袈裟,結跏趺坐於仰蓮花座上,手執法印,有觸地印、辯論印、施捨印、無畏印、轉法輪印五種手印。
四大天王造像,一組4尊,皆為高浮雕,其風格與藏傳佛教壁畫中的形象基本相同,造像古樸,刀法簡潔。菩薩造像1尊,為高浮雕,頭戴塔式寶冠,上身袒露,下身著長裙,天衣披飄帶,雙耳佩環,右手於胸前,左手下垂執一朵蓮花,造像優美輕盈,帶有鮮明的印度佛教造像的神韻。
桑耶寺現存的羅漢石刻造像有6尊,都為高浮雕精品。由於藏地十方羅漢像是由漢地傳來,故其造型、神態、衣飾均與內地的羅漢像相同。裸體男像是這些造像中較特別的造像,雙手捧寶瓶於胸前,跣足站立在覆蓮座,全身赤裸,頭戴寶冠,垂發披肩,腰部系馬尾裙,面相凶狠。此類造型在石刻中並不常見。
此外,在桑耶寺千手千眼菩薩殿內,還保存有部分石板造像藝術。題材以西藏歷史的著名宗教人物為多,還有一些綠度母、佛塔造像。人物造像比較寫實,如米拉日巴尊者像,周圍刻有雲、山、日、月圖案,米拉為短卷發,眉目清秀,著袒右肩袈裟,右肩並斜披一條寬帶;右手執於右耳邊,左手持缽,右腳外露,游戲坐於一塊鼠皮上。傳說,這尊造像就是米拉在山洞裡苦修的真實形象。阿底峽尊者造像的頭部有背光和橢圓形頭光,頭戴紅色尖頂帽,內穿圓形衫,外著寬袖長袈裟,雙手作轉法輪印,結跏趺坐於蓮花座上,造像左右分別刻有轉經輪和塔式寶瓶。湯東傑布的造像之所以讓他右手執鐵索鏈,左手捧瓶,其因在於他以修建鐵橋聞名全藏。故而突出他右手上的鐵鏈,造像生動寫實。
相形之下,蓮花生大師和阿底峽尊者的造像更趨於程式化,而缺少強烈的感情沖動。桑耶寺的瑪尼石刻除部分為吐蕃時期的作品外,大部分是後弘期以後的作品,這些作品尤其是千佛像具有統一的造像風格,顯得嚴謹規范、布局構圖都很統一,有可能出自同一位雕刻家之手。
由於吐蕃時期留存下來的泥塑造像很少,所以我們只能更多地借助有關藏史文字材料加以研究,故而很難對吐蕃時期的佛教泥塑的源流及風格給以全面准確的把握,但大體上可以認為,吐蕃時期的泥塑造像主要受到了來自尼泊爾、印度、克什米爾、於阗、漢地的影響較大。松贊干布時興建的大、小昭寺、昌珠寺等寺的建築藝術和泥塑造像,則多受尼泊爾、漢地、印度的影響。赤松德贊時興建桑耶寺、噶窮寺,赤熱巴巾時修建白美扎西格沛寺等除受上述影響外,克什米爾、於阗、斯瓦特造像藝術的影響則更突出一些。從公元7世紀松贊干布開始到9世紀朗達瑪滅佛,藏傳佛教藝術經歷了約三百年的歷史,作為前弘期的佛教藝術包括泥塑造像,更多地是學習借鑒引進域外佛教藝術手法和風格的時期,還沒有完全形成本民族的造型技藝和美學風格,雖然赤松德贊時已表現出強烈的民族化要求,但從發展的角度講,那也僅僅是邁向民族化藝術之路的第一步。就整個吐蕃時期的泥塑造像而言,他更多地體現了崛起時代吐蕃人的一種寬容、博大、多元的文化精神和素樸、虔誠、渴望超越生死輪回的審美理想。正如聖觀音贊所言:
為利益眾生建築此像,
我在您的面前虔誠頂禮。
您這三尊諸佛的密意,
化成百看不倦的美妙身像,
您具有善巧智慧的慈悲,
懇請您眷顧有情眾生。
您是世間眾生的依怙,
備受各種苦難煎熬的,
災難深重的有情眾生,
懇請您用慈悲來拯救。
三、桑耶寺的壁畫藝術
藏傳佛教的壁畫藝術,主要是指繪制在寺院牆壁上的宗教美術作品。這些壁畫是根據寺院建築的總體設計的需要,以及不同“札倉”顯密修行的要求、儀軌等繪制而成的宗教美術作品。一般而言,藏族壁畫大多集中在每一個寺院的大經堂中。不同的教派寺院以及下屬“札倉”,有不同內容和風格的壁畫作品。按照藏族寺院的一般布局,寺院的壁畫往往集中在大經堂內,因為大經堂常常是一座寺院的建築中心和學經集會的主要場所。經堂的正中一般供奉釋迦牟尼像,兩旁是菩薩像和祖師像,有的寺院內供奉歷代贊普像。大門外側的牆壁上一般繪有四大天王像,大門內側的牆壁上繪有護法神像。有些寺院外的轉經回廊上也都繪有大量的壁畫。藏傳佛教寺院的壁畫內容豐富多彩,其藝術技巧與壁畫面積大大超過內地漢傳佛教寺院的壁畫。可以說,壁畫藝術是藏傳佛教藝術中最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
藏族壁畫藝術產生於吐蕃時代,藏王松贊干布在迎娶尼泊爾公主赤尊和唐文成公主後,曾為二位公主修築宮殿、大昭寺、小昭寺以及布達拉宮早期宮殿建築中保存了吐蕃時代最早的一批壁畫藝術。
吐蕃壁畫藝術的興起是伴隨著寺院的興建發展起來的。當時所建的大昭寺、小昭寺、昌珠寺等都繪有大量的壁畫作品。關於吐蕃早期的壁畫作品,我們能從藏文史料中找到不少記錄。《西藏王統記》記載,國王松贊干布為了慶賀大昭寺的興建完工,曾應眾大臣及不同階層人士的請求分別繪制了一批壁畫作品,如史料說:“於四門畫壇城國,令喇嘛等喜悅;殿柱畫金剛撅形,令咒師喜悅;四角畫萬字卍紋,令苯教徒喜悅;又畫網格紋,令藏民喜悅。凡所許人之風規,皆實踐諾言,故護法龍王、藥叉、羅剎等無不欣喜”。大昭寺、小昭寺開光典禮的贊詞中也提到繪制的壁畫內部,如贊詞曰:
- 上一頁:北京八大處各處寺廟古建大修
- 下一頁:木棉花開映古寺
熱門文章
熱門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