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村落:江西古老家園之脈
日期:2016/12/16 18:44:19 編輯:古代建築
而古村無言,以其獨特的安靜和固執一路留守至今。因為高聳山脈的阻隔掩藏,絕大多數江西古村落能夠安然無恙地保存完好,現在江西擁有著許多從全國范圍來講都比較罕見的古村落,國家、省級歷史文化名村(鎮)達到48個。在今天,這些古村(鎮)不僅僅是被看做古代居民棲息地那樣簡單,散落在江西各個角落的這些古老家園,在數百年乃至千余年的產生發展歷程中,每個家園都有著鮮明的地域特征和背景,每個家園都有著不一樣的興衰史和獨特的文化內涵,有些是鴻儒巨宦的深深庭院,有些則是達官富賈的橫聯縱進,有些僻靜的村落還有可能蘊藏著極為神秘的血緣。
除了用腳步去行走丈量這些村落,我們走訪了中國民居建築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黃浩、江西省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施由明和南昌大學旅游管理系主任黃細嘉教授,試圖梳理出江西古老家園的脈絡。
每個古村都有著鮮明的地域特征和背景。記者劉國偉攝
【古老家園興旺之根源】
在古代社會,攻讀入仕能給家園帶來畢世的榮耀。記者劉國偉攝
交通要沖位置賦予發達機遇
公元880,因避晚唐戰亂,湖北蕲州羅田村人黃光遠遷徙到今安義羅田村定居,據安義縣黃氏家族所編《黃氏宗譜》記載:“光遠公,系湖廣羅田人也。唐廣明年間,避兵亂遷卜茲地,裡名羅田,不忘所自帶耳。”到安義境地後,以打獵捕魚為生,繁衍生息,“小小安義縣,大大羅田黃”,一句俗語說明黃氏在當地的興旺發達。一千多年以後,羅田以古村落的方式聲名遠播,與此形成鼎足之勢的古村落群還包括安義水南、京台兩個古村落,向今人呈現著曾經的輝煌過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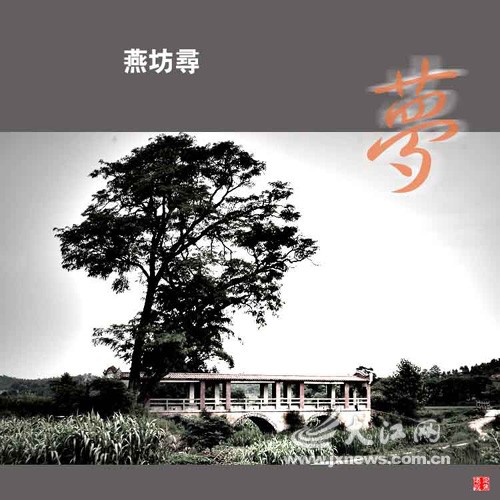
羅田村口的大牌坊顯示著榮耀,村中麻石板道、古車轍清晰可見,商鋪林立,還能看到碾槽、酒坊等歷史遺存和至今保留完整的地下排水系統。街邊窄巷高壁聳立,形成“一線天”。在最小的水南村,以刻有100只形態各異蝙蝠的“百福圖”窗雕最為珍貴,1830年建造的余慶堂有一閨秀樓,是富家女擇婿拋繡球處。
不得不提的是,村落的重要地理位置在其發展史中起到重要作用。江西省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施由明說,在明清時期全國商品經濟較歷代有一個大發展的背景下,當時古村人利用其靠近明清時期江西四大名鎮之一的吳城鎮,處於交通要道的特點,以地理優勢發展商業,在商品經濟的大潮中經商致富發達。
不僅僅是安義的古村落如此,隨著元、明、清時期全國政治中心定都北京,更鞏固了中國政治中心東移的格局,政治中心東移及大運河開通之後,漢水——長江——湘江——西江——珠江這一南北交通要道失去了往昔的地位,而運河──長江──贛江──北江——珠江則成為國內主要的南北通道。這條通道全長兩千多公裡,貫穿北京、河北、山東、江蘇、安徽、江西、廣東七省市,而在江西境內則占了三分之一。
“可以想象這給江西臨近水運的地方發展帶來了何等的便利,像樂安縣流坑村的董氏家族,也是在明清時期,利用其地處贛中烏江上游的地理優勢,合宗族的勢力,壟斷了贛中地區烏江上游的竹木貿易。”施由明說。此外,自唐以來,婺源縣江灣古鎮因為具備通往皖浙贛三省的水陸交通要塞的因素,成為婺源東大門,正是由於這裡獨特的區位優勢,使得江灣在千余年裡,由一個防御型村落發展成為一個經貿繁榮、群賢輩出的千年名鎮,隨著人口的增多和商業的繁榮,江灣古村不斷擴展壯大。還有燕坊等古村落也都是因為處於交通要道,形成了重要的商埠、碼頭而興旺發達。
實際上,在古代交通工具不發達的情況下,天然的交通要沖位置對培育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特色產業成古村崛起良機
除了交通要沖的天然因素,天然的名特產品成為古村崛起的另一天賜良機,江西許多古村就是憑借當地資源經營特色產業興旺起來。
作家沈從文在他的作品中,“一個包袱一把傘,跑到湖南當老板”的描述,說的就是經營江西古村一大特色商業的布商。對棠陰比較熟悉的人,都聽說過一首傳唱了幾百年的民歌:“棠陰街有幾裡長?棠陰街有幾條巷?幾座橋來幾座嶺?幾個菩薩坐壁上?”當一群兒童游戲,左手拍右手互問互答時,棠陰鎮的繁興歷史全都在這首民歌反映出來,“棠陰街有五裡長,棠陰街有十三巷。五座橋來九座嶺,三尊菩薩坐壁上,滿街都是夏布行。”
南昌大學旅游管理系主任黃細嘉教授說,棠陰的興旺離不開當地的夏布。棠陰夏布始於明朝中葉,當時有一位吳姓的本地商人在漢口經商,看到夏布盛銷,便組織了一班人去產地學技術。而後返回棠陰鎮辦起了織布坊。到清乾隆時期最為興盛,建有織布坊100多個,還不包括那些大大小小的家庭作坊,鎮上居民家家會織夏布。隨著市場的需求,又興起了漂染坊。那時,從雷灣村渣堡到解放村索湖7公裡的河邊,建有漂染坊20多個,其中以碓白橋漂染坊技術最高,曾有“藥不到樟樹不全,夏布不到棠陰不白”的說法。
當然,棠陰夏布能成為高檔夏布,與宜河富含礦物質的河水有很大關系,由於境內宜水全是鵝卵石,清澈見底,含硫黃質多,使得出產的夏布潔白如銀,輕柔勝絲。這使得棠陰成為湘贛兩省夏布的集散地,外地夏布經棠陰漂洗後,暢銷南昌、九江、上海、天津等地,遠銷日本、朝鮮。鼎盛時,棠陰集鎮“五裡長街,商店栉比,十裡河埠,商船雲集”。不僅如此,夏布經濟的飛速發展,帶來了棠陰經濟、文化的繁榮。如今老街、民宅、祠堂、牌坊等保存完好,讓人完全可以感受到當年繁花似錦。
江西獨占兩大手工業區
歷史學家翦伯贊曾在《中國通史綱要》中指出:“明代中葉,棉紡織業的松江,絲織業的蘇杭,漿染業的蕪湖,制瓷業的景德鎮和造紙業的鉛山,為江南五大手工業區。”五大手工業區,江西就有兩個,可見手工業之發達。據明《鉛書食貨》記載,鉛山縣僅石塘鎮一地,每年產紙4500多石,其中有200多石被官府收購作為奏本紙。當時鉛山生產的紙有連史、毛邊、關山、京川、貢川、大表、表心、荊川、書策、白綿等十多種。
因瓷器特色產業興起的則數景德鎮瑤裡,因為景德鎮瓷器的主要原料——高嶺土就產於瑤裡附近的高嶺山,在瑤河沿岸的山水之間,既有多處瓷業生產基地——礦坑、窯址和作坊,又有為之服務的交通體系——水運碼頭、古驿道,所以就興起了瓷業貿易,瑤裡原名窯裡,正由窯而得名。但是在明代之後,景德鎮成為瓷業中心,瑤裡的制瓷業逐漸衰落,瑤裡則依靠另一特色產業——茶葉,繼續繁榮。
黃細嘉教授說,此外,他在金溪縣竹橋村調查時,了解到當地也是因為特色產業而興旺起來的村落,其產業就是古代雕版印書業,在康乾時期,竹橋村就有人在全國做賣書生意,在北京開書肆,收羅古籍,這些在家譜均有明確記載。“刊書牌置局於裡門,晝則躬耕於南畝,暮則肆力於書局,以刻書鬻書為業。”至今在竹橋村,還保留著許多雕版作坊,“養正山房”就是一個刻印古籍的地方,位於竹橋村仲和公祠右側,進門為一大庭院,上堂及後堂為印書之所,乾嘉時期書板盈架,直到解放初期保留的刻版才被焚燒。
攻讀入仕為古村帶來榮耀
在古代社會,攻讀入仕同樣能給家園帶來畢世的榮耀,在中國民居建築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黃浩看來,吉安興橋鎮釣源村不失為此類的代表。
早在唐代末年,廬陵望族歐陽氏的一支遷居釣源繁衍生息,釣源歐陽氏與文壇宗師歐陽修同宗,歷代以歐陽修為榮,繼承了祖輩的文風家訓,代代賢良,出現了一大批標名史冊的歐陽子孫。不僅有唐尚書令、博士、兵部侍郎、進士、州官、縣令,更有明代的“父子登科,兄弟連科”,清代的兵部郎中歐陽模等。據殘存的三達堂族譜及墓志碑刻統計,釣源歐陽氏自唐朝開科取士至清代中葉,共有6位進士,6位解元,27位貢生,21位例授郎職,童生、禀生、庠生更是無法統計。
仕途官宦的顯貴給釣源帶來了怎樣的繁榮?釣源號稱“小南京”,這並非族人的自诩,而是吉安城裡人給予的雅稱。專家們根據遺址考察了解,在村落西北角原有兩條繁華街道,這裡有近百家店鋪,有中國知府山水園林式的私家園林,有錢莊,有賭場,有妓院,有戲台,有跑馬場,甚至還有除寧國知府莊園以外的“三美院”、“六美院”、“七美院”等專供個人棲息的“後宮”。在這裡,天天生意興隆,夜夜莺歌燕舞,足不出戶,灶不生火,各種生活娛樂設施一應齊備,各種生活享受呼之即來,俨然一個繁華的鄉村都市。連吉安城裡的闊爺少奶都不願在城裡呆,日夜向往著這不夜的“小南京”。現在人們見到的釣源,僅為原有規模的三分之一,絕大部分的精華已在鹹豐五年的戰火中化為灰燼。
釣源村只是廬陵文化中的一支,廬陵人重教尊儒,崇尚辦學,積澱了深厚的文化底蘊,他們堅信“耕可致富,讀可榮身”,尊師崇學,興建書院,蔚為風尚,這應該是廬陵地區多進士、狀元的主要原因。根據《吉水縣志》記載,該縣僅在明朝中狀元者即有五人,中榜眼、探花者各三人,並出現了“一門三進士,隔河兩宰相,五裡三狀元,十裡九布政,九子十知州”的人文盛況。
在吉安市青原區渼陂村同樣可以感受到當年攻讀入仕的盛況。明、清時期,由梁氏宗族和各大房派興辦的書院多達六所,保留至今的養源書院建於明嘉靖年間,坐南朝北,三層飛角挑檐,磚木結構,樓高15.75米,占地313平方米。由於書院眾多,形成了“序塾相望,弦誦相聞”、“人無貴賤,無不讀書”的社會風尚,而“三尺童子,稍知文章”,孕育出以儒行商、以商助德、商儒合一的渼陂儒商文化。
實際上,對於前人重視攻讀致仕的古村,大多建有巍峨宏偉的祠堂,裝飾優雅的書院、學館、花園,以及匾聯、石刻、名樹、墨跡和文物等,此外還包括樂安的流坑,婺源的理坑,吉州的盧家洲,泰和的爵譽、蜀口,安福的三捨,進賢的艾溪,新建的大塘汪山土庫,莫不如此。
【古老家園建築之文化】
熱衷買田置宅以光宗耀祖
在施由明看來,一個古村的興旺發達不是僅僅依靠某一方面,往往都是耕、商、讀相結合,但不論如何,村落的繁榮最終都在建築上一一體現出來了,這與古人根深蒂固的光宗耀祖思想有著極大的關系。
據江西省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專家調查,在古村宗族成員經商致富以後,不是向著資本主義的雇工經營轉進,而是將大量的錢財在故裡買田置宅,回歸為地主。如清代乾隆年間,安義縣羅田村的黃秀文在吳城經商致富以後,捐了一個監貢生,後被贈奉直大夫,然後將其錢財在其故裡建了一幢規模特大的世大夫第,占地七畝多,用料和雕刻都非常精制,內有天井48個,其錢財也就消耗在光宗耀祖上了;再如清代乾隆年間京台的劉華松、劉華傑兄弟倆亦官亦商,暴富之後,花大量的錢財在故裡買田建宅,一口氣築起三十四幢房屋,成為規模很大的建築群,並且做工非常精美,“此外,還有水南村的黃道源、黃怡耀,京台的劉世美、劉明清等在吳城經商致富後,都是捐官建屋,極盡光宗耀祖之能事。現存的羅田、水南、京台的古建築群,就是宗族成員經商致富後光宗耀祖的成果。”施由明說。
此外,曾經鼎盛的科舉文化,一度給江西帶來過許多個世紀的驕傲,但也使江西的重功名、輕工商的觀念根深蒂固。小有積累的江西商人一旦擺脫貧困,就希望子孫進入仕途,光宗耀祖,或者花數百上千兩銀子為自己及子弟捐個空頭官銜,以改變在家族及社會中的地位。截至太平天國起義之前的清代,資本並非雄厚的江西,以捐錢為手段而獲得的國子監監生的名額,竟居全國的首位。
“這可以說是江右商幫的一大特征,在明清商品經濟有較大發展的背景下,這種現象在江西是很典型的,在全國也是很普遍的,全國許多地區如廣東、福建、浙江、江西、安徽、山西等地都湧現了一大批商人,但經商致富後,大量的資金都不是投向工場手工業或商業資本積累,而是回歸農村,想辦法彰顯門庭,如明清時期,全國聞名的晉商和徽商也是如此。”施由明說。
中國歷史文化名村
樂安縣牛田鎮流坑村(圖1)
婺源縣江灣鎮汪口村(圖2)
吉安市青原區文陂鄉渼陂村(圖3)
高安市新街鎮賈家村(圖4)
婺源縣沱川鄉理坑村(圖5)
吉水縣金灘鎮燕坊村(圖6)
首批省級歷史文化名村
景德鎮
浮梁縣鵝湖鎮高嶺東埠村
上饒
婺源縣江灣鎮汪口村
婺源縣江灣鎮曉起村
婺源縣秋口鎮李坑村
婺源縣沱川鄉理坑村
婺源縣江灣鎮江灣村
婺源縣思口鎮延村
吉安
吉水縣金灘鎮燕坊村
吉水縣金灘鎮桑園村
吉安市青原區文陂鄉渼陂村
吉安市吉州區興橋鎮釣源村
安福縣洲湖鎮塘邊村
宜春
豐城市張巷鎮白馬寨村
豐城市筱塘鄉厚板塘村
贛州
安遠縣鎮崗鄉老圍村
於都縣馬安鄉上寶村
龍南縣關西鎮新圍村
瑞金市九堡鎮密溪村
尋烏縣澄江鎮周田村
鷹潭
貴溪市耳口鄉曾家村
南昌
安義縣長埠鎮羅田村,水南村
石鼻鎮京台村
第二批省級歷史文化名村
南昌
進賢縣架橋鎮陳家村
宜春
萬載縣株潭鎮周家村
高安市新街鎮賈家村
宜豐縣天寶鄉天寶村
吉安
吉安縣橫江鎮唐賢坊村
安福縣金田鄉柘溪村
吉水縣金灘鎮仁和店村
青原區富田鎮陂下村
景德鎮
浮梁縣勒功鄉滄溪村
浮梁縣江村鄉嚴台村
上饒
婺源縣思口鎮思溪村
婺源縣浙源鄉虹關村
婺源縣鎮頭鎮游山村
婺源縣思口鎮西沖村
婺源縣段莘鄉慶源村
撫州
東鄉縣黎圩鎮浯溪村
贛州
贛縣白鹭鄉白鹭村
【江西古村家園之地位】
數量和完好性居全國前列
江西境內許多古村保存完好。記者劉國偉攝
“無論是從保存的完好性還是數量方面,江西古村的地位在全國范圍來講算較高的。”黃浩這樣說。
江西省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專家調查得知,從1985年全省各縣地名普查所編地名志可知,江西各縣的村莊,大約三分之二是明清時期所建,三分之一左右為唐宋所建,而晉以前所建村莊則已無記載。唐宋時期所建村莊大都是北人遷贛定居建立,元明清時期全省各平原、盆地、丘陵地帶所建村莊,大部分是唐宋時期北方人遷贛的後裔所建。
千百年來,為何江西境內許多古村能夠保存完好?黃細嘉教授認為,這與古村宗法制的關系很大,這些古村落都是按照父系的血緣關系,將龐大的族群緊緊結合在一起,大多一村一姓,他們都不許其他雜姓混居進來。這樣雖然顯得很封閉,但同一村落的居民有著共同的宗祠,守著共同制訂的族規。這種大家族制度,讓古村能安然無恙地生存下來,“但相對浙江等地的古村來講,江西的古村又都屬於偏小規模的,這不僅是受江西地形地貌影響,也與經濟實力有很大關系。”他說。
但黃浩同時仍然認為,對於江西古村的保護一刻也不能放松,對於古村的開發更不能急功近利。
【溯源故事】
婺源延村:祖先是匈奴?
在婺源這個古村林立的地域,思口鎮延村同樣擁有著氣派而又精美的建築群,站在湖邊眺望延村,黑白分明的古村房屋極為華麗,明了而又統一。“我們金氏族人是匈奴的後裔,族譜上都有記載。”婺源縣思口鎮文化站老站長金繼榮的這句話,令我們大吃一驚。
金老站長說,歷史考證,延村最早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北宋末年,這個極為動蕩不安的年代,當時的朝廷在金人的摧枯拉朽攻擊之下瞬間崩塌,所有的王族和貴族紛紛逃離,其中就包括大學士金思德的後裔,“到後來,我們進行徹底清查家譜的時候,發現我們自己最早的祖先並不是北宋的大學士金思德,而是漢代名臣金日磾,我們這一支後裔經歷了西安——南京——安徽——婺源理坑的遷徙路線,最後才到了延村。”
這次查譜的結果讓延村蒙上一層神秘的色彩。歷史上金日磾的名氣遠遠要高於金思德。關於金日磾的傳奇身世,在《漢書》裡面最為詳細。“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他本來的身世為匈奴王的太子,他看到自己的父親拒不投降被漢武帝殺害,自己選擇了一條求生的道路,在十四歲的時候成為漢武帝的宮中馬倌,這個職務負責當時的禮賓安排、皇帝出巡的後勤准備等,在某種程度上說他已經屬於漢武帝的近臣。不久便因為他的機智極為賞識,升任侍中、驸馬都尉、直至光祿大夫。
查閱資料,得知關於金日磾還有一則意味深長的故事,漢武帝臨終之前,將太子劉欣托付給當時著名的政治家霍光,請霍光擔任輔政大臣,霍光在漢武帝的病榻前卻舉薦了金日磾,金日磾知道後立刻以“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為理由迅速做了推辭,並主動要求擔任霍光的副手。漢哀帝繼位後,霍光將自己的女兒嫁給了金日磾的兒子。數年後金日磾去世,霍光“恸哭失聲、不能自持”。
實際上,因為金日磾成為中原望族,其後代已經完全被漢化,最後拋棄了匈奴人的生活方式以及思想信仰。延村的金氏家族與草原上的匈奴民族究竟還存在多大的關系?金繼榮說,現在延村還有不一樣的“十番鑼鼓”民俗,據祖輩老人稱這其中還帶有北方特色,與南方民俗存在著差異;而當地的民居高牆環侍,牆上少有開窗,有也是高高小小的,這正是傳承了他們祖上北方黃土窯洞“地台式”建築的痕跡。對於這種說法,當地政府部門表示尚需要進一步考證,但這個不尋常的金姓,已經讓古老的延村在外人眼裡更具傳奇色彩。(文/實習生胡長春 記者劉國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