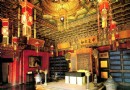文物保護讓龜茲藝術永續留存
日期:2016/12/14 11:05:13 編輯:中國古代建築說起龜茲,就會讓人遙想那婀娜多姿的時代,歌樂袅袅,衣袂飄飄,壁畫艷美,香客絡繹。而今,那個時代的韻味,留在了龜茲石窟的一個個洞窟裡、一幅幅壁畫中。那是人類的瑰寶,留給今人多少聯翩浮想。而當那些抵御了風雨侵蝕的石窟依然能夠為今人所見,其背後印刻著新疆龜茲研究院的文物保護工作者執著的腳步。 9月18日至20日,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名錄的克孜爾石窟,迎來了一批國內著名文物保護以及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參加由自治區文物局主辦的“龜茲石窟保護工作座談會”,總結龜茲石窟保護30年來的成果,現場考察克孜爾石窟、庫木吐喇石窟、森木塞姆石窟、克孜爾尕哈石窟等。 努力保存這段古老的文化記憶,不要讓它損毀於各種自然的以及人為因素的破壞,新疆龜茲研究院從1986年開始,30年來對於龜茲石窟的研究與保護從未停止。在摸索、探尋、研究、創新的歷程裡,他們付出了青春年華、聰明才智,也積累了一批豐厚的學術成果。 龜茲石窟的歲月之殇 絲綢之路上的龜茲古國,是古西域三十六國之一,東西方文化交匯之地。開鑿於公元3世紀至12世紀的龜茲石窟,散落在龜茲古國的20余處。這些大小石窟所展現的,是當時佛教藝術的傑出創造和高度成就,呈現出佛教文化在絲綢之路沿線區域交流和傳播的歷史發展軌跡。新疆龜茲研究院院長徐永明說:“佛教經西域由西向東的傳播軌跡,以及在傳播過程中的本土化過程,在龜茲石窟中都有呈現。” 龜茲石窟作為絲綢之路上最重要的文化遺跡之一,不僅為消失的文明提供了特殊的歷史見證,而且具有審美的突出價值,是古絲綢之路文化不可或缺的構成要素。 龜茲石窟在歷史上曾經歷過兩次大劫難,第一次是在公元十世紀以後,隨著伊斯蘭文化越過帕米爾高原向東傳播之後,在近兩個世紀的佛教與伊斯蘭教的宗教紛爭中,隨著龜茲佛教的衰敗而逐漸被廢棄,同時遭到較大的人為破壞。第二次是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外國探險隊不斷在龜茲地區進行探險活動,致使龜茲諸石窟壁畫遭到嚴重損壞,一部分洞窟內的精美壁畫被野蠻盜割,許多洞窟的牆壁上刀痕斑駁,殘留壁畫千瘡百孔。 另外,由於龜茲石窟建造時代久遠,受石窟建築巖體質地的脆弱性,以及自然侵蝕和突發性自然災害等自然因素的影響,致使龜茲石窟文化遺產的損毀程度一直在不斷加劇。 風雨兼程的铿锵足音 自制的油燈,自制的發電機,用來裝水的葫蘆,當年使用過的簡陋的桌子、箱子……9月20日,記者在新疆龜茲研究院龜茲石窟保護30年展覽看到,龜茲石窟的文物保護工作者在艱苦的生活環境和簡陋的工作條件下,所付出的艱辛努力。他們常年奔波於偏遠山溝裡的石窟,有家不能回,孩子和家中老人無法照顧。老一輩文物工作者李麗告訴記者:“過去,我們還要坐著馬車,去離駐地很遠的洞窟展開田野調查,帶著馕和水,住在簡易搭建的土坯房裡,點著油燈,牆上爬滿了壁虎……” 可以說,新中國成立之後,龜茲石窟的保護經歷了兩代人的艱苦奮斗。 如何從學術和藝術角度客觀真實地反映龜茲石窟一體多元文化以及燦爛的發展歷史?龜茲文物保護工作者一直在努力探尋、摸索與創新。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第一批文物保護工作者來到龜茲石窟,做了大量基礎性保護工作,為搶救龜茲石窟瀕危洞窟發揮了巨大作用。尤其是1986年7月,新疆龜茲研究所(新疆龜茲研究院前身)在國家以及自治區有關部門的關心支持下,在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和積極援助下,經過30年奮發進取,龜茲石窟保護與研究以及窟區基礎設施建設工作不斷邁上新台階,發生巨大變化;特別是2000年以後,在國家的大力支持下,龜茲石窟文物的保護和管理進入科學保護的時代,也標志著龜茲石窟保護管理和研究事業進入新的歷史階段。 龜茲石窟文物之珍貴,保護范圍之廣大,也意味著保護工作的任重道遠。 如今,走進龜茲研究院,從外部設施環境到內部設施布局都發生了巨變,寬闊平坦的專線旅游公路,古色古香的展館場所,電腦、電視、WiFi等應有盡有,變化可謂翻天覆地。 科學保護刻不容緩 記者跟隨全國文物研究與保護領域的著名專家學者,一起現場考察台台爾石窟、庫木吐喇石窟、克孜爾尕哈石窟的時候,親眼目睹了該院保護這些寶貴的文化遺跡所取得的可喜成就。 在庫木吐喇石窟,記者看到,兩座快要坍塌的石窟被木柱結實地支撐加固,周圍牆壁上的壁畫已經在久遠的年代剝落殆盡,而頂部的壁畫卻被接近完好地保存了下來。人物風韻十足,姿態婀娜,色彩艷麗,美不勝收,我們通過這些美妙壁畫,仿佛可以望見當年的繁華盛世。 著名專家黃克忠高度贊揚了這兩個洞窟的保護成績,他說:“這是非常好的示范項目,完全可以成為范本,在國內其他洞窟壁畫保護方面作為借鑒。” 中國美術學院教授王雄飛望著這些精美壁畫感歎著:“這些六、七世紀的壁畫,手法非常娴熟,藝術造詣可謂空前絕後。” 的確,以克孜爾石窟為代表的龜茲石窟是絲綢之路佛教代表性遺址,也是絲綢之路世界文化遺產重要的組成部分。龜茲石窟反映了佛教與佛教文化在中國傳播、發展關鍵階段的歷程,對於正確闡明古代新疆地區宗教發展史,以及多元文明碰撞與交融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保護這些洞窟,意義重大。 龜茲石窟700多個洞窟要保護,其中克孜爾石窟就有279個。記者了解到,該院負責保護和管理的龜茲石窟群共有9處,拜城縣3處,即克孜爾石窟、台台爾石窟、溫巴什石窟;庫車縣5處,即庫木吐喇石窟、克孜爾尕哈石窟、森木塞姆石窟、瑪扎伯哈石窟、阿艾石窟;新和縣1處,即托乎克拉艾肯石窟,目前皆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克孜爾石窟2014年6月被列入“絲綢之路:長安至天山廊道的路網”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經過30年的成長與磨煉,新疆龜茲研究院如今已成為全國石窟文化遺產保護、管理和研究領域一支重要的隊伍。”徐永明告訴記者:“目前保護難度最大的是病害防治,包括石窟巖體病害和壁畫病害,近十年來我們依托國家支持的保護項目,與國內相關科研機構合作,培養了一支自己的壁畫保護修復隊伍,緩解了人才不足的問題。” 特別是從2011年開始,他們在上海印刷集團的援助下,采用先進的數字化技術用於石窟壁畫保護,通過摸索實驗,掌握了石窟三維建模和壁畫數據采集、拼貼、色彩還原,以及多光譜技術和3D打印技術。2015年承擔了國家文物局支持的克孜爾石窟數字化保護項目一期工作,完成了13個洞窟的數字化保護工作,並在此基礎上按照1 1的比例,在上海復制出一模一樣的洞窟。從此,龜茲石窟異地原貌展出的夢想,終於實現了。 穿越了一千多年留存到今世的龜茲石窟,將由於科學保護時代的來臨,而煥發出更加迷人的光芒。 讓舉世矚目的龜茲藝術永續留存,是新疆龜茲研究院過去30年的奮進足印,也將是他們今後努力拼搏的動力源泉。 來源:新疆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