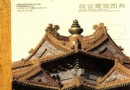古泗州城曾輝煌近千年 “蓄清刷黃”注定被淹命運
日期:2016/12/14 9:37:01 編輯:古建築紀錄

古泗州城遺址出土的建築構件:滴水。

脊獸
王小平 王衛華 文/ 圖
公元1680年(清康熙十九年),飽受水患侵擾的古泗州城(位於今江蘇省盱眙縣縣城以北)終遭滅頂之災,一場大洪水讓這個喧鬧繁華的“水陸都會”沉入洪澤湖西岸的淮河底端,此後再也未能復現。自此,除了歷史典籍記載,與這座古城有關的只是神秘的傳說和揣測,留給人們無盡的遐想。
一直以來,後人從未停止過探尋古城真容、揭開眾多謎底的腳步。經國家文物局批准,一年多前,江蘇省考古研究所聯合淮安市博物館、盱眙縣博物館的考古人員,正式啟動了對這座“東方水下龐貝城”的考古發掘。
經過勘探發掘,考古人員初步確定了古城西南一片重點區域地下磚石遺跡的分布范圍,還發現了城門、城牆,並在建築垃圾層下發現殘存的建築牆體、灰磚鋪地面、外方內圓覆蓮紋石柱礎、抱鼓石、大鐵镬等遺跡遺物……水下泗州城的神秘面紗已經撩開令人激動的一角。
目前,考古工作仍在有條不紊地繼續開展。據省考古研究所所長林留根透露,今年還要發掘10000多平方米。作為曾經盛極一時的繁華都市、佛教聖地,沉睡300余年的泗州城一定蘊藏著更多的驚喜,等待著人們去發現。
數度遷徙
古城輝煌近千年
據史載,古泗州一帶最初為徐國,泗州之名始設於南北朝時期的北周大象二年(公元580年)。改名泗州之後,其州治(不含臨時建治在內)數次搬遷,前後經歷了千年的興衰沉浮。 縱觀歷史,不難發現,泗州州治設於淮河鎮的時間最長,也是泗州城最繁盛的時期。後來人們所稱的古泗州城遺址通常是指這個“唐代始建、宋代擴建、明代最為鼎盛”的水下泗州城。
據專家學者考證,在唐代,泗州舊有東西南座土城,中間隔汴河,有汴泗橋相連。明初,為了防洪,城門外還建有六道月城和六座月門,每門外一座,南門外兩座(像雙閘門套閘一樣)。城外發大水,即先堵月門,行人則從月城上出入,這種形式在國內非常獨特。每座城門下都建有水關,舟楫可以出入,宋時通漕艘。
泗州城內有內城河,城外有外城河,河外還有防洪堤(原為宋時築的土提),明萬歷四、五年間,巡按御史邵陛修築了石堤,堤周長二千八百四十五丈,闊五尺,高九尺。明萬歷九年(公元1581年)重修,萬歷十六年(公元1588年),總理河漕的潘季馴又“加幫真土”,加高石工二尺,將堤頂石工後面的沙土換成了黏土。古城環城皆濠,濠外有堤,濠水相通。因溝濠縱橫,故橋梁較多,各城門原皆有吊橋,以通行人,萬歷初南門改建石橋。城內外有橋16座,其中城內8座、城外8座。在其最鼎盛時期,城區有居民9000余戶,36000余人,城區房捨密集,交通便利,商賈雲集。
泗州城不僅是歷史州郡所在地,而且唐時淮東節度使、南宋時淮南路東宣撫使、明清時的廬風淮揚滁徐欽差以及監察御史、鳳泗兵備道、江北提弄按察使司等官員、官署也都曾設駐於此。北宋時,建有城北公園,城內還有古跡、廟宇、庵觀、碑亭多處和其時聞名的“泗州十景”;國師僧伽和尚入城興建大聖寺,寺中建有香火鼎盛的僧伽塔和明遠大師塔,大聖寺成為當時全國五大名剎之一。
百年一歎
水漫全城繁華盡
清澈溫潤的淮河發源於河南桐柏山,曲折蜿蜒千裡到達江蘇盱眙。在這裡,它注入中國第四大淡水湖——洪澤湖。然後,經由與洪澤湖相連的二河、三河、入江水道、入海水道和蘇北渠溉總渠等分流,與京杭大運河、長江和黃海融為一體。而曾經的古泗州城就坐落在淮河最下游,淮河與洪澤湖的接口處。
然而,又有誰能預見,盛極一時的古泗州城其實潛伏著巨大的危機呢?而談及“水漫泗州”的悲劇,不能不追溯黃河變遷的歷史。
公元前2000年至南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黃河經河北、山東入渤海。公元1128年,朝廷任命杜充任東京留守,此時金兵來犯。面對金兵的金戈鐵騎,杜充想到“水淹三軍”的辦法。他在滑州(今河南滑縣)挖開黃河之堤。滾滾黃河水,從滑州李固渡噴湧而出。熟料,這黃河水非但沒有阻止金兵的步伐,反而一改原來向北的水道,轉而向南搶奪淮河水道,由江蘇進入黃海,歷時728年的“黃河奪淮”的災難史由此開始。
明代潘季馴曾提出了“蓄清刷黃濟運”的方略,即在與淮河相接的洪澤湖東岸的高家埝築起大堤(即現在的洪澤湖大堤),提高淮河水位,使淮河的清水從清口處倒灌黃河,沖刷黃河帶入大運河等的泥沙,從而使得大運河暢通無阻。但在洪澤湖東岸築堤,提高淮河的水位,也就決定了位於洪澤湖西岸的泗州古城日後連遭水患並被淹沒的命運。
到了清朝,季馴的治河方略再獲認可。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靳輔出任河督,再行“蓄清刷黃”之策,不斷抬高洪澤湖大堤,最終,洪澤湖成了懸湖,泗州城位於洪澤湖正常水位之下。
公元1417年,當時的泗州太守王升帶領軍民運土填城,所填土方達45920方。他們墊高大街小巷21條及軍署民宅院基,並助蓋民房2000余間。這是在泗州城被淹前人們最後一次大規模與“老天”的抗爭。
清朝康熙十八年(1679年)冬十月,大水先沖開了泗州城外東北處的石堤,決口七十余丈。接著,泗州城城牆西北角忽然崩塌,開口數十丈,大水沖入城中,人們四處逃散。次年,泗州城徹底沉沒,遙遙望去,只有普照王寺的僧伽塔和明元大師塔的塔頂還露在了水面上。
水漫泗州城後,知州莫之翰欲哭無淚。他感到了自己的失職,搭棚駐守在還未完全淹入水中的防洪堤上,現場辦公,設點赈濟災民。後又在泗州城外築兩道新堤,以保護防洪堤上的州署和棚戶居民。莫之翰和他的後任官員們一直守護著水下泗州城,盼望著皇上能想辦法讓沉沒於水下的城池再浮上水面,讓丟失的城池重回到他們手上。
就這樣,他們一守就是97年。然而,泗州城終究沒有再浮上來。黃河上游不斷湧來的泥沙最終將泗州城掩埋得了無蹤跡。
滄海桑田
“夢”醒時分露真容
2010年12月,江蘇省考古研究所牽頭開始對這座沉睡的古城進行正式考古發掘。為什麼選擇這一時間點呢?專家解釋說,一是前期調查比較充分,已具備了大規模發掘的條件,二是國家即將實施南水北調東線二期工程將經過古泗州城遺址,“如果不抓緊考古發掘,將來水位蓄高後,將被徹底淹沒,成為永遠的遺憾。”
近日,筆者驅車前往考古現場——盱眙縣淮河鎮沿河村實地探訪。據江蘇省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員朱曉汀女士介紹,泗州城遺址位於盱眙縣西北部淮河北岸的狹長灘地上。遺址東北部為一望無際的洪澤湖,東南隔淮河與第一山、寶積山等山地相望,正北方有明代第一陵——明祖陵。整個古城遺址面積約2.46平方公裡,呈橢圓形,狀似烏龜,其中淮河及中間小島下方占六分之一,淮河北岸占六分之五。
筆者在發掘現場看到,腳下是農田,不遠處是一片灘塗。區域內,有一處面積2000多平方米的坑塘,四周用圍網圍住,西邊堆起幾座高高的土堆,土堆間混雜著青色的碎磚渣和瓦片。
朱曉汀稱,水塘就是他們去年試探性挖掘的地點,而旁邊的土就是挖出來的堆土。現場清理完畢後,就到了冬天,由於天氣太冷,且晝夜溫差較大,熱脹冷縮很可能對底下的青磚和柱礎造成損傷,注水實質上是一種保護。
據她介紹,現場位於古城的西南部位,他們通過借鑒、參考之前勘探的成果,以史料記載為指導,進行了再次鑽探。在此基礎上,確定了三個發掘點:一是香華門及月城;二是內城牆;三是建築區。
截至目前,考古人員已發現內城牆、外城牆及城門一座及建築密集區一處。
在建築密集區(水塘及其周邊),考古人員發掘出了房址兩座、磚鋪路面三條。其中一個房址的面積較大,平面為規整的長方形,東西長18.7米,南北寬9.6米,面積179.5平方米,共有五間房。值得一提的是,只有中間一間的地面用青磚錯縫鋪就,並且居中的房間南北均有道路相連,其他四間分東西兩側對稱分布。考古人員推測,這一間極有可能是過道。
這處房址內,他們共清理發現柱石9個;過道兩側的隔牆中清理出兩個鋪地蓮花柱礎;在房址南半部,清理出一塊抱鼓石。另外,在瓦礫層中,出土了大量制作精美的建築構件,其中瓦、瓦當、滴水、屋脊上的螭吻獸以及其他建築構件上百件;北側的道路兩側還出土了石香爐3座。
“從遺物來看,可見當時洪水很猛,因為除了殘磚斷瓦外,很多建築構件都偏離了本來的位置。”朱曉汀說,他們初步判斷這是一個跟佛教相關的公共建築,可能是大聖寺,也有可能是祭淮河水神的龍王廟,亟待在今後的發掘中進一步確認。
相關鏈接
古泗州城考古發掘概況
古泗州城淹沒水底距今已超過300年,長期以來,關於它的更多的只是傳說。然而,上世紀70年代後期,盱眙縣在建設淮河大橋時,工人們偶然間發現一些碎磚片瓦,一時引起了社會關注。有關人士據此考證,認為附近區域就是古泗州城遺址所在,這也稱得上泗州城考古的肇始。
1986年,泗州城的研究正式列為課題。1993年,盱眙縣文史辦在泗州城遺址范圍內調查出8處遺跡。1999年,江蘇省物探院和盱眙縣有關部門共同對遺址的位置、范圍、面積、走向,外城牆、內城牆、月城的寬度、深度、殘存高度以及性質做了確定,並探測出城內的部分建築遺跡。
2004年,南京大學文化與自然遺產研究所、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盱眙縣文化局對遺址進行考古調查勘探,較為准確地確定了古泗州城內外城垣的位置、城垣構築方法、城址的四至、具體走向、城門性質和城門的大致結構、城內主要街道、古汴河和部分重要建築區的位置等。
200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物探隊確定了靈瑞塔塔基、香華門、北門、主要道路、部分建築的位置和大致范圍。2007年,江蘇省考古研究所開展了為期一個月的考古調查和勘探,找到了西門及東西大街、古汴河及香華門、靈瑞塔及大聖寺的准確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