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麗中國:難識的地名 難忘的古鎮
日期:2016/12/13 22:44:41 編輯:古建築紀錄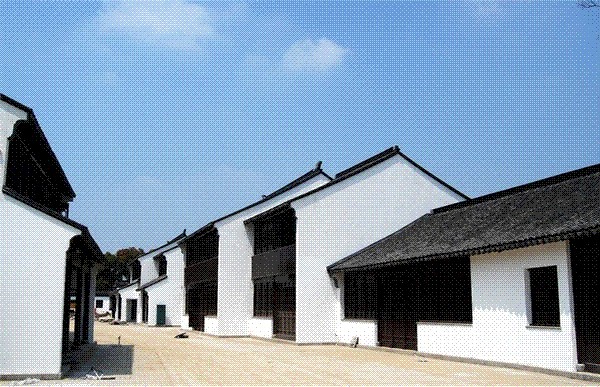
甪直,因鎮有甪端而名。古稱甫裡。 在當地,我一直聽不清人們怎樣念這個“甪 ”字,查查字典,讀“lù"。甪端,中國傳說中的一種神獸,形似麒麟,頭有獨角;甪端專住風水寶地,為象征吉祥之獸。 甪直是個小鎮 ,在鎮上走一圈,個把小時足矣。但它是太湖風景名勝區十三個景區之一,1994年,被命名為江蘇省歷史文化名鎮。從蘇州到甪直,公交車約四十分鐘。
鎮裡小店街鋪大都保留了古舊模樣,依街而行,不顯零亂。古老街市中尚存百年老店一兩家。一底一樓的老房未改,店裡的格局也難有更新,可惜裝修油飾得有點過分,大失古色古香的韻味。不過菜確實做得好,“甫裡鴨羹”色澤清爽,入口味美。
甪直依然保留著水運習俗,每天凌晨三四點鐘,周圍農家漁家搖著小船,運來各種農產水產,集市旁的小碼頭便開始繁忙,搬運交易,人聲嘈雜,直到天明。
獨自流連小鎮,可以盡享江南水鄉安然靜谧,吳侬軟語的美妙。小鎮水流縱橫,橋梁密布,貼水成街,人家枕河而眠,鎮貌古樸,風情幽逸。隨處小橋流水,狹窄彎彎的卵石曲徑,小瓦挑檐的二層小樓,花枝出牆的深巷家居,方桌條凳的飯館廳堂,黑漆櫃台的雜貨店,蹲踞河邊淘米洗菜的老妪,路旁一畦畦綠油油的菜田,一切生活的場面仿佛挽留了逝去的光陰,定影為歷史的紀念照,鑲嵌在一個似乎不願消失的江南社會鏡框裡。這兒的美景讓人留戀,在這兒生活過的名士更讓人欽羨。
陸龜蒙是晚唐詩人,與皮日休為友,相互唱和,世稱“皮陸”。他出身破落世家,舉進士不第,曾為湖州、蘇州刺史的幕僚,後來長期隱居在甪直鎮,賦詩撰文,經營茶園。他的詩,有相當多的描寫田園生活,他的散文成就更超過了詩,在晚唐文學中,獨具光芒。陸龜蒙墓就在甪直鎮保聖寺西院, 墓園占地約一畝,墓前的斗鴨池(陸龜蒙養鴨的遺跡)和清風亭,1986年進行了整修復原。
現代文學家葉聖陶生於蘇州,早年曾在這裡任教,離開後一直不能忘懷,常稱甪直為“第二個故鄉”。他有多篇作品取材於甪直。如《寒曉的琴歌》是從西匯上、下塘街獲得的素材。在葉聖陶當年居住、教書、著作的小院漫步,一草一木,都讓我莫名地感到親切。所有的想象,所有的從有關記述中獲取的信息,共同編織成對聖陶老人的追憶。這裡非常安靜,已經移址而建的甪直小學琅琅的讀書聲飄過來,我疑心尋聲而去就能望見葉老的身影。
從保聖寺、葉聖陶紀念館出來,經香花弄,往東步行,走不多遠,可見到一座石門宅院,前有青磚照壁,上镌“漪韻”兩字。這座宅院就是甪直教育家沈柏寒的私邸。 沈伯寒是甪直創辦新學的第一人。沈家原為富豪,房產廣布,時有“沈半鎮”之稱。沈宅占地約二千五百平米,現修復開放的為其西部,約八百平方米。為了更加豐富沈宅的觀賞內容,原設於保聖寺天王殿的吳東水鄉婦女服飾館,今移置沈宅西前廳展出。沈宅庭院布局的精雅,家中陳設的考究,雕梁畫棟,讓人歎為觀止,然而我更佩服的是曾經走出國門的沈先生洞察教育,興學重教,鐘情於人才培養的功業。
離開沈宅的大門,沿西匯上塘街東行,到南市下塘街向南,就到萬盛米行了。
“萬盛米行的河埠頭,橫七豎八停泊著鄉村裡出來的敞口船。船裡裝載的是新米,把船身壓得很低……”這是葉聖陶的小說《多收了三五斗》裡描寫的景象。這篇小說後來被收入中學語文教科書。 “萬盛米行”,門面為三開間朝西店鋪,面對河埠。店鋪設有售糧高櫃,上掛“萬商雲集”的廣告牌。兩廊陳列有稻作農具、加工谷米的各式器具,集江南農具之大全。 修復了的“萬盛米行”不僅再現了民國年間江南米市的風貌,而且因為增設了江南歷代農具的陳列,成為一處具有水鄉生活特色的景觀。
從萬盛米行北行,到眠牛任浜口,就可見到“三步二橋”。 兩橋相連成“ L”形的景觀,俗稱雙橋,又加上它形似古代的鑰匙,也稱鑰匙橋。
“三步二橋”是三步跨兩橋的意思。古鎮水道縱橫,在兩河交匯處,往往有相連成直角的兩座橋。東西跨於塘河上的三元橋是三步二橋的代表。1986年,甪直鎮的水道駁岸及古橋被列為吳縣文物保護區。
在飄飛的細雨中造訪甪直,入心的遺跡凝結為詩情,入眼的景致充盈著畫意,偶爾從身邊緩緩走過一位老者,心裡就嘀咕,這是哪位先賢?甪直非常幽靜,正契合了我對清靜的追求,在這樣的氛圍裡,沾染些許名士的靈氣,也算造化,我讀過北方人對江南“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的詩句,我沒有福分生於斯長於斯,算是遺憾。也罷,就這樣讓我惦念著江南,魂牽夢萦著甪直小鎮好了。蘇州4月8日電
熱門文章
熱門圖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