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昌古鎮的歷史和傳說
日期:2016/12/16 20:26:02 編輯:古代建築名稱
一、禹會諸侯於塗山的傳說
表面看來將安昌的歷史一育追本窮源到傳說中的大禹時代,似乎有些勉強。因為4000多年前雖經海進與海退的反復輪回,“海水離開南部丘陵山邃向北退去”.海面逐漸下降,“全新世時還是一片淺海的會稽山地以北(大致相當於今山會平原)隨之涸出,並“一直基本處於今天的高度上,中問短期小幅波動不會超過2米爹但仍展遭潮水倒惡、山洪暴發之害水患頻仍一片沼澤。囚卷轉蟲海進遷徙至會稽、四明山地的人類尚在原地活動,“人民山居”,“隨陵陸而耕種,或逐禽鹿而給食,很明顯此時的安昌僅作為會稽山地以北淺海沼澤地的一部分,既無人類的活動,更缺乏文字資料,從歷史學的角度進行研究,既無可能,也沒必要。局限於生產力發展的水平,當時\類的活動憲全依賴生產和生活的自然環境,而裹現為對育接影響生產和生活的自然環境的執著崇拜。面對這片水泛頻仍的淺海沼澤地,人們夢寐以求出現神化了的英雄,整治滔滔洪水,讓重回故土的願望馬上變成現實。“越族居民在會稽、四明山地的山麓沖積扇頂端,俯視這片茫茫大海,面對著這塊他們祖輩相傳的、如今已經為洪水所弄噬的故土,當然不勝感慨。他們幻想和期待著有這樣一位偉大的神明,能驅走這滔滔洪水,讓他們口到這塊廣裹、平坦、富庶、美麗的平原上,於是,大禹的傳說應運而生了。

大禹其人及其在會稽的活動歷來頗有爭議,即有關其人其事的真偽辨。但傳說自有傳說的價值,通過傳說,隱隱約約可窺見當時人類生產和生活之一斑。神話和傳說本來不必如同歷史一樣的認真對待,但應該承認,他們仍然是值得研究的。其實,對於上古歷史,特別是經過儒家們的打扮並且統一了口徑的上古歷史,他們與神話、傳說的差距有時實在不大。在這個意義上將安昌的歷史追溯到大禹時代,應該無可非議。
大禹與會稽的關系,根據記載,至少可歸納為五件大事:宛委得書、娶妻塗山、功成了溪、會諸侯於塗山、崩葬會稽。其中娶妻塗山、會諸侯於塗山兩事,與安昌有較密切的關系。
娶妻塗山。大禹致力於治水,及三十仍未娶。行至塗山,娶塗山氏之女為妻。其妻十月後生子啟。在《尚書•益稷》中,大禹稱:“娶於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予弗子.唯荒度土功。”《吳越春秋》也說廠禹一十來娶行到塗山恐時之菩,欠其度制乃辭雲:“吾娶也,必有應矣。”……禹因娶塗山,謂之女嬌.取辛壬贅甲。禹行十月,女嬌牛子啟。”記載中出現地名“塗山”。塗山在何地?容後再敘此不贅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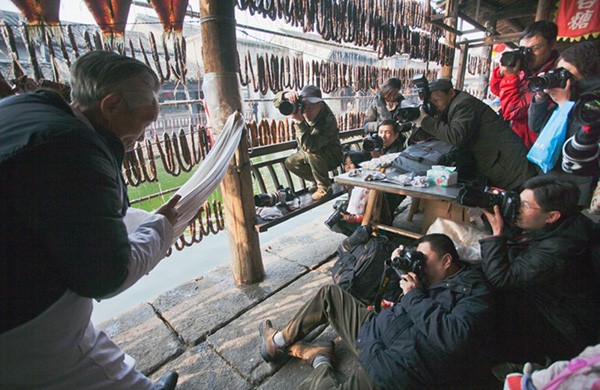
禹會諸侯於塗山。大禹治水成功以後,會諸侯於會稽。《左傳•哀公七年》記載;“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吊者萬國。說到大禹會諸侯於塗山時,不能不說防風氏,因為他被殺於塗山。《國語•魯語下》謂:“昔禹致群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戳之。”開會遲到竟招殺身之禍,的確十分罕見。有人分析這是大禹為樹立自己的權威所采取的措施。而後唐馬缟在《中華古今注》中提供了另一種說法,“昔禹王集諸候於塗山之夕,忽大風雷震,雲中甲馬及九十一千余人,中有服全甲及鐵甲;不被甲者,以紅絹襪其首額。禹王問之,對曰:‘此襪額蓋武士之首服,皆佩刀以為衛隊,乃是海神來朝也,。‘一雲風伯雨師。”有人推測這是防風氏所率軍隊形成的海市魔樓。塗山若是臨海,以此解釋防風氏被殺的原因.也有一定的道理,而非無的放矢。
那麼,塗山究竟位於何地?向來說法甚多。東漢許慎《說文解字》謂:‘塗,會稽山,一曰九江當塗也”;晉杜預注《左傳》時,已有壽春東北之說;東晉常琢在《華陽國志》中稱禹娶於塗山……今江州徐山是也。所以,庸蘇鄂在《蘇氏演義中綜合上述幾種說法:“塗山有四:一者會稽;二者渝州即巴南,舊江州是也……三者濠州。一四者文字音義雲塗山……今宣州當塗縣也。”

其實對塗山的爭論,.早在越工勾踐三年(公元前494)孔子就有過結論。《國語•魯語下》曰:“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徹俎而宴,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為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群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戳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此事在《孔子家語•辨物》、《史記•孔子世家》中均有類似記載。而晉杜預注《左傳•哀公七年》時.則否定了塗山在壽春東北的說法,說:“塗山在壽春東北.非也。又在引述《孔子家語》中孔子論大骨的記載後說;“蓋丘明親丞聖旨,錄為實證.臾。又案劉向《說苑.辨物》,王肅之敘孔子世孫孔猛,所出先人書《家語》,並出此事,故塗山有會稽之名。考校群書及方士之目,疑非此矣,蓋周穆之所會矣。此外.《水經注•淮水》基本上也全文引用,肯定塗山應在會稽之說。
限於資料尤其是出上文物的印證,有關塗山在何地的爭論仍將繼續進行,一年半載難以形成定論。但據已有的資料分析,塗山在會稽的可能將大於氣其他諸地。
今天的塗山是一海邊的小山丘。《越絕書》載:“塗山者,禹所取妻之山也,去縣五十裡。”嘉泰《會稽志》雲:,“塗山在縣西北四十五裡.舊經雲禹會萬國之所。亦稱西底山或旗山。明諸萬裡《於越新篇》記載;“塗山一作西扆,謂禹負底朝諸侯處。扆是帝工宮殿上所設戶牗之間的屏風,大禹以山為扆,大會萬國諸侯,西扆由此得名。又因山坡由西向東略成四十五度,遠望似三角形旗,故名旗山。塗山之頂原有禹廟,《郡國志》雲:“《十道四番志》:聖姑,從海中乘石舟,張石兜帆至此,遂立廟。“秦始皇廟,在縣西一裡。會稽記石:始皇崩……像乃訴流而上。人以為異,茲廟遂廢。”嘉泰《會稽志》謂:“東海聖姑,棄石魟、張石帆至,二物見在廟中,蓋江北禹廟也。”

廟中溢汀北禹廟也。 有周時樂器,錞於,銅為之,形似鐘,有頸映水,用芒莖拂之則鳴。《太平寰寧記》曰:“。宋武修廟,得古珪,梁初又得青玉印。”相傳,明初劉伯溫為破旗山帝王風水,令廟遷移山之永南麓。據明代萬歷年問《紹興府志》載:山陰大禹廟在塗山南麓,宋、元以來鹹祀於此。國朝始會稽山陵廟致祭,茲廟遂廢。山之東另有斬將台,乃斬防風氏處。相傳.防風氏被斬後,鮮血流至山下河中.染紅河水,故有’“紅橋”之名。宋代潘江《紅橋》詩日:
略釣橫溪畔,何緣獨著名;
九州稱甸服,.多士號公卿。
跋扈誠無益,征誅非不平;
余波屬玷穢,千載未澄清。
小溪上橫跨著無數簡陋的獨木橋,.為何唯有紅橋大名鼎鼎,那是因為防風氏的傳說。千百年來,流水潺潺,仿佛看淡人間煙雲,不停地洗刷著防風氏飛揚跋扈的罵名。
滄海桑田後的今天.過去的許多情境都被無情地替換,禹廟、紅橋、斬將台等都已蕩然無存,慢慢地離現實遠去。幸.好傳說尚在民間,歷史之筆也忠實地記著傳說中的是是非非,而讓我們又觸摸到了4000多年前的安昌。

二、後白洋村的古文化遺址
傳說自然美麗動人,廣泛流傳,如傅斯年所說:“禹的蹤跡的傳說是無所不在的,北匈奴,南百越.都說是禹後。而龍門、會稽、禹之跡尤著名。即在古代僻居汶山(岷山)一帶不通中國的蜀人,也一般的有治水傳說。”之所以如此,或許基於一定的科學依據,而非憑空臆想、信口開河。但傳說畢竟是傳說,絕非信史。對安昌的研究,仍應借用考古資料。
1994年3月因基建發現後白洋村古文化遺址,經勘探分布范圍約1000平方米。同年5月,文物部門組織力量進行搶救性考古發掘,發掘面積計450平方米,掌握了遺址所處位置、文化內涵、分期年代等基本信息。該遺址位於安昌後白洋村金溝溇、銀溝溇兩台地,與馬鞍、壺瓶山古文化遺址相接壤;高出稻田1米之多,文化層疊壓於距高地表面約2.5米以下,有文化層一層,厚0.2-0.8米,出土石器、陶器和原始青瓷器等類遺物,其中石器有石镞、石锛、石箭頭、破土器、半月形石刀,陶器系列由夾砂紅陶、泥質紅陶、泥質灰陶、印紋硬陶組成,器種有敞口折沿圓錐或扁錐足鼎、敞口折頸鼎、斂口孟、高足杯、三足盤、支座、器蓋、罐和盆等, 器表紋飾有方格紋、米字紋、雲雷紋、葉脈紋、繩紋和條紋,原始瓷器較少,僅見碗與豆兩種器皿。根據器物特征推斷,年代相當於西周晚至春秋初期。

在古代寧紹地區.人類選擇生產和生活的空問位置往往是逐水向陽避風的小山頭下、當時海拔高度在2米左右的平緩坡地。這或許是人類選擇生產和生活自然環境的第一原則。逐水而居,可以在人類活動完全依賴生產和生活的自 然環境的低級階段,僅僅依靠陶罐等小件容器,解決必要的水源問題;向陽避風,具有相對獨立的小氣候條件,人類可以依據區域內的各類資源,墾殖土地,發展農業,獲得生存;平緩坡地,地勢相對高於四周,顯得干燥,可以避免水患,有利於定居農業的發展。據後白洋村古文化遺址考古發櫥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一些初步認識:一是人類已經選擇安昌作為生產和生活的某一空間,從發掘到的生產、生活遺物看,此地已形成沿海聚落,且系至今為止安昌最早之村落;二是人類憑借寬闊、平緩、溫暖、濕潤的近海台地作為立足點,已墾殖了若干土地,開始從事農業生產;三是人類逐水而居.仍依靠陶罐等小件容器儲水受後白洋村古文化遺址考古發掘現狀的限制,當時安昌 人類生產和生活的許多特征並不十分清楚,基本上是一個謎,至於聚落要素則更欠缺,而未發現墓地、道路、窯場、活動廣場等聚落要素構成的聚落整體形態,遺物僅呈現出生產和生活最粗淺的線條。要解讀安昌此時此刻的歷史,應該繼續尋找相關的古文化遺址。

三、安昌地名的由來與變遷
當我們還津津樂道後白洋村古文化遺址所傳達的安昌人類早期活動的某些信息時,距此僅18公裡的今紹興城一帶即將築起一座國都。事情的來龍去脈很復雜,此僅作簡單敘述。春秋戰國時期,“同俗並土的吳越為謀自身生存和發展,刀光劍影,爭戰不休。’魯哀公元年(公元前494年),越國戰敗求和,許為屬國,越下勾踐被迫於吳國國都姑蘇(今蘇州)服了兩年多的苦役,期滿歸國後臥薪嘗膽,擇種山〔今府山,或稱臥龍山)東南麓興建小城,“周二裡二百二十三步、陸門四,水門一”。又在小城以東建築大城,“周二十裡七十二步”,“陸門三,水門三”。立國建都是越國滅吳的基礎,更重要的則是發展農業生產、保障糧食供應。而此時的山會平原仍於後海(今杭州灣)相連,“西則迫江,東則薄海,水屬蒼天,不知所止。交錯相過,波濤浚流,沉而復起,因復相還。浩浩之水,朝夕即有時,動作若驚駭,聲言若雷霆。波濤援而起,船失不能救”。墾殖土地、發展生產,首先必須北御鹹潮、中蓄淡水、南截山洪。改造水土成為勢所必然,越王勾踐采納大夫計倪“饑饉在問,或水或塘,因熟積以備四方”的建議,立足於逐水向陽避風的平緩坡地,圍堤築塘,蓄淡拒鹹,興建了一大批水利工程,著名者有吳塘、練塘、石塘、苦竹城(塘〕、富中大塘、山陰古水道等,使都城附近少數水患頻仍的淺海沼澤地,慢慢成為可以墾殖的農田.提高了糧食產量,足以供給越國30萬人口之需。
此後鑒於人口增加、土地墾殖的需要.山會平原的水利建設獲得了深入、持久的發展,經歷了從兩漢魏晉點狀、零散的水利建設,到唐宋主干水利網絡的初步形成,再到明清區域水利格局的最終定型的道路。該地區的水利建設,“大體可以隋唐為界,分為兩個階段、隋唐以前要以攔蓄為主,偏重於利用窪地興建湖陂,用以蓄淡御鹹,抗洪抗旱,是於越居民從山麓沖積扇聚落及孤丘聚落向平原聚落發展過程中采用的手段;隋唐以後,轉向側重於外阻內洩水利工程的建設,外阻即建立海塘防御下程,內洩即疏治平原上的河網。正是在山會平原水利建設尤其是海塘修建的背景下.安昌被納入到該地區發展的樞架之內。

唐代以前,山會平原北部已有零星的海塘,並呈現出建設的兩個趨勢:一是由點狀向線狀發展;二是由南向北推移;但史書中的正式記載卻從唐代開始。唐垂拱二年(686),在山陰與蕭山交界處的後海沿岸,築成長50裡、寬9尺的海塘.因位於兩縣交界處,稱作界塘。開元十年(722),在會稽東北40裡.李俊之增修海塘,“至上虞江抵山陰百余裡,以蓄水溉田”,捍衛了整個會稽的北部海岸。大歷七年(755)和大和六年(832),皇甫溫、李左次先後兩次修築會稽防海塘。《新唐書》有關防海塘的記載,至少說明了兩點:一是“增修” 之說,表明海塘早已有之,此時不過是加固與連接罷了;二是山會平原的開發正向海岸延伸,修築防海塘主要是為了防御潮水泛濫,故多建在海岸地區,塘身低薄,高1-2米.且為土塘。而直到宋元時期,整個山會平原北部的海塘休系才告基本形成,那時,普遍.采用石塘.抵御潮水沖擊,李左次修築海塘的基本情況,史籍記載相當稀疏,根據推測,當憑借白洋山海拔125.2米的有利地形,以修築海塘,白洋山由此易名大和山。大和山右安昌北部,瀕錢塘江,表明安昌在此時或許更早的時候已開始修築海塘。海塘有效地阻隔了安昌與後海的潮水.加快了把此地淺海沼變成墾殖土地的進程。
唐末,中央大權旁落,地方藩鎮割據,狠煙四起.萬民疲敝、紹興很快被卷人到城頭大王旗不斷變換的動蕩政局。在爭奪和厮殺中,安昌不經意地走進了歷史。

唐乾符二年(875),浙西狼山鎮遏使王郢起兵反唐,攻掠浙東、浙西諸州。董昌時戍石鏡鎮(今臨安),遂以捍衛鄉裡為名,募集土團軍,並平王郢,以功擢石鏡鎮將。乾符五年(878)又與余杭縣陳晟、於潛縣吳文舉、鹽官縣徐及、新登縣杜凌、唐山縣饒京.、富春縣文禹、龍泉縣凌文舉等合建杭州八都兵,自任石鏡都將。中和三年(883),董昌聞朝廷任路審中為杭州刺史,十分不滿,率先攻入杭州,稱都押司。鎮海軍節度使周寶見無法控制局而,表請任董昌為杭州刺史。光啟二年(886〕,董昌派麾下錢謬消滅了浙東觀察使劉漢宏.徙鎮越州(今紹興),稱知越州軍討事,後朝廷進為義勝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在越初期,治政尚廉,後則殘暴酷虐,百姓稍有過錯,即遭誅族之罪,以致“血流刑場,地為之赤”。又因朝廷未封越王,於乾寧二年(895)據越州自立,國號“大越羅平”,稱“聖人”,鑄“順天治國”銀幣。鎮海節度使錢謬奉唐昭宗之命發兵征討,大敗董軍,執董昌還杭州,至西小江、董昌覺無顏見人,投江自殺〔一說途中被殺)錢謬為彰顯自己的功績,名俘獲董昌地羊石寨為安昌,《羊石山石佛庵碑記》謂:“大唐中和間,武肅王謬以八郡(都)兵屯羊石寨,平劉漢宏及獲董昌,因名其鄉為安昌焉。”是安昌地名之緣起。

錢謬大獲全勝以後.建吳越國.定杭州為吳越國西府,越州為東府、錢謬偏安東南一隅,”保境安民”,.慘淡經茸.同時崇尚佛教,致使杭州寺院林立,寶塔遍布,梵音不絕,“九廂四壁,諸縣境中,一王所建,已盈八十八所,合一十四州悉數之.且不能舉其目矣”,始有“東南佛國”之稱。而在吳越寶正五年(930)安昌競也破天荒地興建了兩處寺院。一處叫福安院,又名福安寺,後稱西扆塗山寺,在西扆山東麓寺前村。嘉泰《會稽志》謂:“福安院,在縣西北九十二裡,後唐長興元年,於古棲隱寺基上建,號“資福院”。治平元年改賜今額。明嘉靖年間,因營造尚書何诏墓,遷寺於眠牛溪東岸,額曰“塗山古剎”。占地面積近15畝,黃牆黛瓦,山門巍峨,計有正殿、禅房、齋堂等200余間,為附近寺院之冠。明詩人羅欣《詠福安寺》詩曰:
密密松篁覆古阡,入林方見寶幢懸。
樓聽潮汐三江近,山引滄洲七寺連。
樓鵑枝頭傳粥鼓,眠牛溪上起爐煙。
老僧盡日巖扉底,迎客唯供禹並泉。
據傳,乾隆帝下江南時,曾賜該院經本多部。興盛之時。當地佛事,曾匯集過一千尼姑和八百僧眾、另一處叫安康教寺,在安昌東市街河南岸、嘉泰《會稽志》曰:“安康院,在縣西北九十三裡。後唐長興三年建。嘉慶《山陰縣志》則謂:安康教寺,在縣西北四十五裡清風鄉,地名安昌。後唐長興元年.僧普安創建,初本號安昌院。《綱鑒易知錄》載:為建寺,五代後唐郭崇韬後人捨毛基地十三畝,故寺之住持僧每歲首,辄至郭氏,拜崇韬靈座。北宋末年,金兵南下,據傳因趙構避難至此,始稱安康寺。清順治間重建,康熙年間又擴建。山門額題“天路雲虹”和婁大任狂草“西方聖人”,寺內樓閣,黃牆雕甍,氣勢恢宏,有禅房、配飨房、香積廚和斗壇等近百間。觀音閣旁有假山、荷花池,景色幽雅。清末民初,佛事頗盛。一度曾做警察分局、傷兵療養院等。
千余年問,寺院修修建建.死死生生,接納過真命天子的恩典垂青,也飽嘗過黎民百姓的頂禮膜拜;既領教過權的無理干涉,也經歷過戰火的猙獰慘烈,如今更被掩沒於歷史的塵埃之中,坍塌不存,但觀照其興衰的命運,幾乎與安昌的歷史不謀而合。敘述安昌的過去,少不了吳越王錢謬,更無法抹去曾經香火火缭繞的寺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