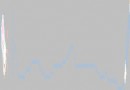徽駱駝與績溪牛
日期:2016/12/14 19:18:00 編輯:古建築結構
駱駝,哺乳綱。適於沙地行走。善耐饑渴。性溫馴而執拗。能負重致遠,號稱“沙漠之舟”……
人格化的駱駝,更是給人以一種不畏道路艱險,忍辱負重,長途跋涉,富有進取開拓精神的深刻印象。無怪不少有識之士把徽州人稱作為“徽駱駝”。
據史書載,早在二千年以前,徽州便是“山越”的土著居民勞動生息的山國。三國以前,皖南的黟、歙、休寧,浙西的遂安、淳安,統稱為歙,或黟歙,他們聚居在新安江上游源頭,後又沿江東徙,在下游山谷繁衍生息。
徽州人民的祖先,不僅是山林的驕子,攀嶺越谷,騰躍如飛。而且勤勞樸實,為創造中華民族燦爛的古文化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幾千年的歷史長河,哺育了徽州大地一代又一代有志之士。他們或經商,足跡遍及全國,有“無徽不成鎮”之說。徽商在明清時代處於鼎盛時期,對經濟發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或從文,文風昌盛,教育發達。“連科三殿舉,十裡四翰林”,“父子尚書”,“兄弟丞相”,“同胞翰林”,傳為佳話。早在宋代就有程朱理學(程頤、程灏、朱熹)的創始人在此活動。後相繼湧現出無數文人雅士,燦若繁星,代不乏人。發明活字印刷的畢升,我國最早的望遠鏡制造者鄭復光,北宋著名農民起義領袖方臘,以及我國傑出的山水畫家黃賓虹,當代偉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著名的新安畫派創始人漸江大師和著名的新文化運動人士胡適等人,也都出生於徽州。
徽州地處山林,交通不便,按現代人的廉潔叫做“信息量較差”。很難想象,從深山密林中走向社會,走向世界,需要付出何等的努力!其堅韌不拔的精神,即便是“沙漠駱駝”也難以企及。
我們可想見,那一峰峰響著駝鈴,昂著頭,馱著日月星辰,一步一個腳印地走向天際盡天的“沙漠之舟”。
由此迭化為:一個個揣著報國與奮進理想,拎著土藍布小包裹,告別家鄉熟悉的山山水水,走川過壑,投向理想王國的的“徽駱駝”……
這樣的“徽駱駝”隨處可見:黃山挑佚、新安江艄公、田頭勞作的農人、在老屋祠堂勤奮就讀的學生。甚至連我所熟識的徽州一帶的朋友們,都好象有這麼一種“駱駝”精神,他們長年工作在比較艱苦的環境裡,不圖戀大都市的繁華,默默地為建設徽州這塊土地作出貢獻。
徽州,在封閉了好多個世紀的歲月裡,由於避開了戰火的困擾,“關起門來搞建設”,曾經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裡,得天獨厚地發展了經濟和文化。可是,這種由自然經濟建立起的“花源”,終究禁不起商品經濟大潮的沖擊,一度時期內制約了徽州的發展。令人可喜的是,隨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改革開放政策的進一步落實,古老的徽州突然抖開了神秘的面紗,向人們展示出燦爛的歷史文化和庶足的特產資源。現代化交通通訊工具,把徽州向世界拉近了一個很大的跨度。旅游事業的大發展,更使得徽州的發展較之其他地區有著更加優越的條件。
如是說,駱駝和飛機乃至火箭有著多大的區別,同樣推動著歷史車輪的前進。而駱駝更有著難能可貴的精神品貌和堅強的性格。
我愛徽州的山山水水,更愛“徽駱駝”,是他們創造了徽州這塊土地上的一切。
一生癡絕處,無夢到徽州。
徽州地處皖南崇山峻嶺之中,四面群山環繞,層巒疊嶂,河流交叉,風景優美。長期以來它一直處在一個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中,逐漸形成一個獨立的民俗單元,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俗和民情。
但是,這裡可耕土地非常少,素有“七山半水半分田,兩分道路和莊園”之稱。即使是耕地,也是土質非常差,“骍剛而不化”,不適於耕種。而且遇到雨水豐富的季節,山洪暴發,耕地就被淹沒,莊稼被洪水橫掃一空;而到雨水稀少的季節,耕地就會缺水干涸而龜裂,只要有十天不下雨,山民就要仰天而呼,求神祈禱下雨。耕地如此之少,但是到明清時期,這裡的人口卻迅速增加,大大地超過了有限耕地的承載力,造成了嚴重的地少人多的矛盾。
正是在這種地少人多、農耕環境惡劣的情況下,造就了一群群 “徽駱駝”和“績溪牛”。這裡的“徽駱駝”和“績溪牛”指的是走出家鄉四處經商的徽州商人。以駱駝和牛來形容,一方面說明的是徽商創業的艱辛,另一方面指的是徽商具有忍辱負重、堅忍不拔的精神。這種精神正是徽商創業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駱駝和牛是人們所熟知的兩種哺乳動物。在風塵彌漫、干旱缺水的沙漠地區,駱駝是主要的畜力;在田園阡陌、春耕秋耨的農耕地帶,牛是人們得力的助手。日久天長,在人們眼中,駱駝和牛便象征著吃苦耐勞和勤懇努力,體現了敬業、執著、拼搏、進取、友愛、和諧等等優秀品質。
明清以來,不少人在觀察、了解、研究徽商後,都把徽商比作“徽駱駝”,這是對徽州商幫的形象概括,集中反映了徽商整體品質。
不過,在徽州六縣當中,績溪徽商的興起要比其他縣商人晚一些,所以,當徽州其他縣的商人日趨沒落之際,績溪徽商卻方興未艾。這種後繼之秀、亂世中爭雄的徽商余輝同樣令人們關注,折射在績溪徽商身上的“績溪牛”精神,也已成為中外學者爭相發掘、探索和研究的對象。如今更多的時候,人們已不僅僅局限於績溪商人,而是把它同樣地形容於所有的徽商後起之秀身上。
無論是“徽駱駝”還是“績溪牛”,它們都是對徽商精神的形象概括。在如今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商業環境的優越遠非明清時代所能比擬,然而,作為一種創業精神——徽商精神依然值得我們去探究、學習和借鑒。概括起來,徽商精神有下述要點:
其一,衛國安民的愛國精神。從早期徽商不辭勞苦,運糧輸邊,到明中後期徽商積極參與抵抗倭寇侵略的斗爭,乃至近代徽商為了抵御外國入侵,踴躍捐資捐物,處處時時體現了他們的愛國精神。因為他們深知,沒有國家的安定與統一,就不會有個人事業的興旺和發達。“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這是我國歷史上商人的愛國主義傳統。
其二,百折不撓的進取精神。窮困的生存環境迫使徽商走出家門,他們一般以小本起家,闖蕩商海。商海浪濤洶湧,凶險異常,一不小心就會擱淺甚至是沉沒。然而徽商的可貴之處在於,他們受到挫折之後,並非一蹶不振,從此便銷聲匿跡,而是義無反顧、百折不撓,不成功決不罷休。許多徽州大商人都是經歷了無數次失敗,最後終於成功走上致富的道路。
其三,度勢趨時的競爭精神。市場風雲變幻莫測,活躍於市場的徽商必須時時細心預測市場,觀察市場動向,分析市場行情,審時度勢,根據市場商品種類的盈虛和供求情況,對目標市場進行細分,去選擇所經銷的商品,並且能夠使經營時間、地點隨供求關系的變化而靈活機變。他們所從事的五大行業:食鹽、糧食、木材、茶葉、典當無不是根據市場行情的變化而隨機經營的。正是由於他們能夠隨時觀察市場,根據市場變化審時度勢,因此面對同行業的競爭,他們時時能走在同行業的前面,能夠出奇制勝。
其四,以眾幫眾的和協精神。徽商的和協精神不僅表現在家族中,也表現在一個個的商業團體中。即便在整個徽州商幫內部,也能做到同舟共濟、以眾幫眾。遍布各地的徽州會館、同業公所的建立,就突出體現了這種精神,從而大大地強化了徽州商幫內部的凝聚力,提高了市場競爭力。
其五,惠而不費的勤儉精神。大多徽商是從小本起家,不畏艱難,克服了種種不利因素,經過了一番奮斗拼搏,最後才建立了自己的基業,成為富商大賈的。“致富思源”,他們大多數人特別珍惜得來不易的財富。因此,他們雖然致富,但日常生活仍舊保持在家時的艱苦樸素的作風。不僅如此,他們還以艱苦樸素的勤儉精神教育子孫。
其六,以義制利的奉獻精神。這突出表現在大量徽商發財致富後,以種種“義行”、“義舉”來奉獻社會。徽商由於“賈而好儒”,因而絕大多數人在經商活動中比較重視人文精神、講求理性追求。雖然致富,但他們依然自奉儉約,克勤克儉。不過一旦當他們面對國難民困或旱荒水災時,卻又會慷慨解囊,將財富奉獻給社會。
其七,賈而好儒的文化精神。“賈而好儒”是徽商的顯著特點。徽商很愛讀書,他們有的白天經商,晚上讀書。在路途中也是時時忘不了讀書。愛讀書給徽商帶來了三個方面的影響:一是提高了徽商的文化素養、文化品位。這樣,較高的文化素質就成為他們與官僚士大夫交往的“黏合劑”。同時也給徽商的商業經營同樣帶來了許多便利;二是由於讀書,使得徽商善於從歷史上汲取豐富的商業經驗、智慧,促進自身商業的發展;三是增強了經商的理性認識,即他們能夠以所謂的“儒道經商”,從而形成良好的商業道德。
徽商正是憑著他們特有的徽商精神,從而能夠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乃至於發展為雄視天下的大商幫。這種精神植根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之中,又被徽商進一步發揚光大。“徽駱駝”和“績溪牛”所造就的徽商精神,不僅是徽商的巨大財富,更是徽商留給後人的寶貴遺產。
以眾幫眾的團隊精神
徽商是以血緣和地緣為紐帶結成的商幫團體。“美不美,家鄉水;親不親,故鄉人。”有著共同血緣或者地緣關系的徽商,有著很強的親緣和地緣認同意識。在人生地不熟的異鄉外地,不期然碰見了同族人或者家鄉人,徽商往往會興奮得忘乎所以。這種固有的“鄉誼觀念”和“宗族意識”,形成了徽商以眾幫眾、相互提攜的傳統。
有一吳姓徽商家族,族裡長輩就曾制定這樣的族規:凡是族中有些子弟不能讀書,並且家裡又無田可耕的,因為生活所迫不得不出外做生意,那麼族裡諸位有經營經驗的長輩在外要麼提攜他,要麼在其他親友處推薦他,好讓他能有個穩定的職業,可供其糊口,千萬不能讓他在外游手好閒,以致衍生禍患。
有位徽州商人名叫方用彬,他在經商過程中,結交了包括政府官僚、文人士大夫、缙紳商賈等等各界朋友。那麼方用彬這位名不見經傳的儒商是怎樣認識這麼多不同地區、不同社會地位的人物的呢?或者用現在的話來說,他是怎樣建立這樣一個廣泛的交際網絡的呢?要知道在當時交通、通訊都遠遠不如今天發達。答案就是除了方用彬本人喜好交游而且文學書畫無所不通外,他的同宗同鄉關系給了他許多接觸不同人物的機會。
在徽商的鄉族觀念中包含著約定俗成的道德觀念和帶有強制性的宗族族規,這些使徽商彼此之間有著很強烈的患難與共意識。這種意識客觀上成為徽商之間信息傳遞的動力泉源。一首績溪民謠這樣唱道:
有生意,就停留,沒生意,去蘇州。跑來拐去到上海,托親求友尋碼頭。同鄉肯顧愛,答應給收留。
就拿歙縣和休寧兩縣來說,明清時期,兩縣由於不少人在外經商,這些在外經商的人往往攜帶親戚朋友出外共同經營。因此往往出現這種情況:一家創業成功,那麼這家人不會獨享,往往大家共同分享,規模大的甚至能攜帶千家百家,生意小的也能攜帶幾家幾十家共同致富。
有位徽商叫許孟潔,這個人親族觀念極強,他在外生意做得非常紅火,於是親戚朋友紛紛去投靠他。凡來投靠者,他都加以提攜,於是他的親戚朋友也就個個致富。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徽商宗族之間是何等的休戚與共!
千人同心,則得千人之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
相互提攜自然也就形成了一種團隊精神,在商場競爭中造成了一個集體優勢。
近代徽州人胡適早就認識到徽商宗族團體的優勢,他聽說家鄉績溪准備編纂縣志時,就說:“縣志應該注重縣裡人移動轉徙經商的分布與歷史,縣志不能夠只見小績溪,而不看見那更重要的‘大績溪’,若無那大績溪,小績溪早已不成個局面。”胡適所說的“大績溪”實際上就是靠宗族紐帶聯系的散落於各地經商的績溪人團體。宗族意識隱含的強制性在這裡起著關鍵性作用。
比如說,一旦出現一些不顧家鄉的族人,族中一些長老就會百般對他們進行勸誡,說:“我們徽州家鄉一直保留著千百年的祖墓,千百年的祠堂,千百戶的鄉村。這些在其他地方是沒有的啊。假如你們背離了家鄉,即使子孫可以長保富貴,但是他們在外地已成為孤家單親,假設出現家業敗落的情況,就會無依無靠。這種輕易背離家鄉的事情,你可要謹慎地好好想想!”這些輿論說教再加上道德和宗族法規的制約,使宗族和鄉緣之鏈堅實而牢靠,也就使徽商的團隊精神愈加發揚,團隊力量也就愈加壯大。
正是由於徽商具有強大的團隊精神,他們在挫敗競爭對手後,憑自身實力往往進一步變一般經營為壟斷經營,謀取高額利潤。如兩淮的鹽業、北京的茶業、松江的布業等,差不多都是由徽商壟斷的。
此外,明清商人畢竟處在封建時代,由於封建意識的狹隘性,商業經營者之間往往對經驗和技術相互加以保密。但是,在具有“以眾幫眾”團隊精神的徽商內部,這種情況卻很少存在。雖然商人深知商業經驗的價值,一般不會輕易傳人,但是徽商是通過血緣和地緣關系建立起來的商幫集團,經驗的傳授也就順理成章了。再加上徽商的行業宗族化和行業地緣化的特點,商業的成敗、興衰直接與本族、本地利益息息相關,所以前人也就樂於向後人傳授經驗。這種以鄉族親緣為紐帶的關系網絡,使徽商具有同時期其他商幫所沒有的信息交流優勢。
不做“茴香蘿卜干”
敬業精神是從業者對所從事職業具有的一種執著的信念和深深投入的意識。
明清徽州地區從事商業活動的人口很多,幾乎超過全地區人口的一大半。明清筆記體小說《豆棚閒話》說:徽州風俗慣例,一般人一到16歲左右就要出門學做生意。徽州還有一則民諺說: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
一般人家生活貧困,小孩長到十五六歲,就要隨鄉族長輩出外學做生意,尋覓謀生之路。一開始他們多半是在自己的長輩或親戚的店鋪裡當學徒。學徒一般歷時三年,三年的學徒生活是相當辛苦的。吃苦倒是小事,關鍵要能圓滿結束學業,否則就要被人嘲笑。
在外學徒以及日後獨自做生意,最忌諱被人稱作“茴香蘿卜干”。因為“茴香”諧音為“回鄉”,“蘿卜”諧音為“落泊”,意為在外學無所成或者經營不善落泊回鄉。所以徽商無論拜師學徒還是日後獨自闖蕩商海,他們都會兢兢業業、勤勤懇懇,一旦生意不成功,他們寧願客死他鄉,也不願輕易回家。
徽商對商業的執著和專注,在中國商業史上可以說是相當罕見的。許多人離家別妻,一年到頭奔波於外。明萬歷《休寧縣志》說:休寧縣百姓往往身揣資本,出外四處經商謀生。他們做生意一般講究公平,往往以物美價廉取勝。他們在商海經營往往一直到老才罷休。經商期間,按照徽州的風俗,經營者一般每年回家探親一次,然而那些離家遠的三四年才能夠回家與父母妻兒團聚一次。探視之後又要出門繼續經營生意。
雖然如此年復一年地在外操勞,黑發出門白發回,但他們依然無怨無悔。甚至有的徽商外出,數十年而不歸。
健婦持家身作客,黑頭直到白頭回。兒孫長大不相識,反問老翁何處來。
上面這首新安竹枝詞就是徽人經商的真實寫照。出門時孩兒還在襁褓中,回來時孩子都已長大成人,他們腦中的父親往往只是個概念而已,如今父親回來了,他們自然不認識。
民國《歙縣志》說:“我縣習俗重經商。經商必然遠離家門。每每離開家門,往往幾年才回來一次,有時甚至長年在外不回家的。剛剛結婚,丈夫就離家經商的情況,在這裡比比皆是,都習以為常了。”
清代婺源縣有一位商人姓詹,他在兒子出生幾個月後就離家出外經商,結果一別就是17年。兒子長大後決心追尋當年父親的蹤跡,把父親給找回來。於是兒子深入四川、雲南等山區,又遍尋湖北、四川成都等地,最終把父親給找到,父子相攜而歸。還有一位歙縣商人程世铎,六歲便隨父親出外經商,直到27歲才輾轉回家。所以有人說,新安商人“出至10年、20年、30年不歸,歸則孫娶媳婦而子或不識其父”。徽州商人一生無怨無悔投身於商業經營的行為,充分體現了他們的敬業精神。
徽商的敬業精神,不僅僅表現在徽商個人的一生無悔投入商業的行為方面,更體現在商人家族對商業世代不懈、前赴後繼的執著和追求。
徽州居民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聚族而居,往往一村甚至一鄉都是一個家族,所謂“千丁之族,未嘗散處”。他們宗族觀念濃厚,宗法成為維系家族關系的紐帶。同樣,在經商中,宗法在族人中同樣起著重要的關聯作用,往往出現“舉族經商”的情況,族人之間在經商中相互提攜、相互關照。
舉族經商的結果,是在徽州形成了一些著名的商人家族,譬如歙縣的汪氏家族、江氏家族、鮑氏家族,休寧的吳氏家族,婺源的朱氏家族等等。這種舉族上下成百上千人對商業的投入和專心,在明清時期的其他商幫中是不多見的。其中許多家庭都是幾代人前僕後繼,勤懇敬業,潛心經商。
譬如祁門倪國樹,頗具經商才能,曾販木饒河,後不幸溺死在一處渡口。其子起蟄當時還在襁褓中,長大後立志繼續父志,努力學習經商,經商中不圖厚利,往往以義為利,聲名遠播,最後成為一名富商。
在徽州《許氏家譜》中,還記載了一段更為感人的“家庭創業史”:許氏家族中有一人名叫許道善,年輕時曾在清源經商,因為他善於經營,贏利累至千金,在當地商人中名列前茅。後來中途回家,商業隨之中斷,家中逐漸困頓。道善看著兒子們漸漸長大,於是決心復出經商。他命兒子永京主持家事,自己只身前往臨清經商。不久,因遇騷亂,道善所帶資金耗竭,又染病不愈,竟客死異鄉。其子永京為了振興家業,毅然繼承父志,告別母親與妻兒,循著父親的足跡出外經營。沒想到他這一去就是幾十年,最後也是死於異鄉。永京的兒子長大成人後,母親拿出自己的私房錢,命他繼續出門經商,完成爺爺和父親未竟的事業。結果功夫不負有心人,許家終於在商業上獲得成功,家業重新振興起來。這樣的事例在徽商中還有很多。
人格化的駱駝,更是給人以一種不畏道路艱險,忍辱負重,長途跋涉,富有進取開拓精神的深刻印象。無怪不少有識之士把徽州人稱作為“徽駱駝”。
據史書載,早在二千年以前,徽州便是“山越”的土著居民勞動生息的山國。三國以前,皖南的黟、歙、休寧,浙西的遂安、淳安,統稱為歙,或黟歙,他們聚居在新安江上游源頭,後又沿江東徙,在下游山谷繁衍生息。
徽州人民的祖先,不僅是山林的驕子,攀嶺越谷,騰躍如飛。而且勤勞樸實,為創造中華民族燦爛的古文化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幾千年的歷史長河,哺育了徽州大地一代又一代有志之士。他們或經商,足跡遍及全國,有“無徽不成鎮”之說。徽商在明清時代處於鼎盛時期,對經濟發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或從文,文風昌盛,教育發達。“連科三殿舉,十裡四翰林”,“父子尚書”,“兄弟丞相”,“同胞翰林”,傳為佳話。早在宋代就有程朱理學(程頤、程灏、朱熹)的創始人在此活動。後相繼湧現出無數文人雅士,燦若繁星,代不乏人。發明活字印刷的畢升,我國最早的望遠鏡制造者鄭復光,北宋著名農民起義領袖方臘,以及我國傑出的山水畫家黃賓虹,當代偉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著名的新安畫派創始人漸江大師和著名的新文化運動人士胡適等人,也都出生於徽州。
徽州地處山林,交通不便,按現代人的廉潔叫做“信息量較差”。很難想象,從深山密林中走向社會,走向世界,需要付出何等的努力!其堅韌不拔的精神,即便是“沙漠駱駝”也難以企及。
我們可想見,那一峰峰響著駝鈴,昂著頭,馱著日月星辰,一步一個腳印地走向天際盡天的“沙漠之舟”。
由此迭化為:一個個揣著報國與奮進理想,拎著土藍布小包裹,告別家鄉熟悉的山山水水,走川過壑,投向理想王國的的“徽駱駝”……
這樣的“徽駱駝”隨處可見:黃山挑佚、新安江艄公、田頭勞作的農人、在老屋祠堂勤奮就讀的學生。甚至連我所熟識的徽州一帶的朋友們,都好象有這麼一種“駱駝”精神,他們長年工作在比較艱苦的環境裡,不圖戀大都市的繁華,默默地為建設徽州這塊土地作出貢獻。
徽州,在封閉了好多個世紀的歲月裡,由於避開了戰火的困擾,“關起門來搞建設”,曾經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裡,得天獨厚地發展了經濟和文化。可是,這種由自然經濟建立起的“花源”,終究禁不起商品經濟大潮的沖擊,一度時期內制約了徽州的發展。令人可喜的是,隨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改革開放政策的進一步落實,古老的徽州突然抖開了神秘的面紗,向人們展示出燦爛的歷史文化和庶足的特產資源。現代化交通通訊工具,把徽州向世界拉近了一個很大的跨度。旅游事業的大發展,更使得徽州的發展較之其他地區有著更加優越的條件。
如是說,駱駝和飛機乃至火箭有著多大的區別,同樣推動著歷史車輪的前進。而駱駝更有著難能可貴的精神品貌和堅強的性格。
我愛徽州的山山水水,更愛“徽駱駝”,是他們創造了徽州這塊土地上的一切。
一生癡絕處,無夢到徽州。
徽州地處皖南崇山峻嶺之中,四面群山環繞,層巒疊嶂,河流交叉,風景優美。長期以來它一直處在一個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中,逐漸形成一個獨立的民俗單元,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俗和民情。
但是,這裡可耕土地非常少,素有“七山半水半分田,兩分道路和莊園”之稱。即使是耕地,也是土質非常差,“骍剛而不化”,不適於耕種。而且遇到雨水豐富的季節,山洪暴發,耕地就被淹沒,莊稼被洪水橫掃一空;而到雨水稀少的季節,耕地就會缺水干涸而龜裂,只要有十天不下雨,山民就要仰天而呼,求神祈禱下雨。耕地如此之少,但是到明清時期,這裡的人口卻迅速增加,大大地超過了有限耕地的承載力,造成了嚴重的地少人多的矛盾。
正是在這種地少人多、農耕環境惡劣的情況下,造就了一群群 “徽駱駝”和“績溪牛”。這裡的“徽駱駝”和“績溪牛”指的是走出家鄉四處經商的徽州商人。以駱駝和牛來形容,一方面說明的是徽商創業的艱辛,另一方面指的是徽商具有忍辱負重、堅忍不拔的精神。這種精神正是徽商創業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駱駝和牛是人們所熟知的兩種哺乳動物。在風塵彌漫、干旱缺水的沙漠地區,駱駝是主要的畜力;在田園阡陌、春耕秋耨的農耕地帶,牛是人們得力的助手。日久天長,在人們眼中,駱駝和牛便象征著吃苦耐勞和勤懇努力,體現了敬業、執著、拼搏、進取、友愛、和諧等等優秀品質。
明清以來,不少人在觀察、了解、研究徽商後,都把徽商比作“徽駱駝”,這是對徽州商幫的形象概括,集中反映了徽商整體品質。
不過,在徽州六縣當中,績溪徽商的興起要比其他縣商人晚一些,所以,當徽州其他縣的商人日趨沒落之際,績溪徽商卻方興未艾。這種後繼之秀、亂世中爭雄的徽商余輝同樣令人們關注,折射在績溪徽商身上的“績溪牛”精神,也已成為中外學者爭相發掘、探索和研究的對象。如今更多的時候,人們已不僅僅局限於績溪商人,而是把它同樣地形容於所有的徽商後起之秀身上。
無論是“徽駱駝”還是“績溪牛”,它們都是對徽商精神的形象概括。在如今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商業環境的優越遠非明清時代所能比擬,然而,作為一種創業精神——徽商精神依然值得我們去探究、學習和借鑒。概括起來,徽商精神有下述要點:
其一,衛國安民的愛國精神。從早期徽商不辭勞苦,運糧輸邊,到明中後期徽商積極參與抵抗倭寇侵略的斗爭,乃至近代徽商為了抵御外國入侵,踴躍捐資捐物,處處時時體現了他們的愛國精神。因為他們深知,沒有國家的安定與統一,就不會有個人事業的興旺和發達。“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這是我國歷史上商人的愛國主義傳統。
其二,百折不撓的進取精神。窮困的生存環境迫使徽商走出家門,他們一般以小本起家,闖蕩商海。商海浪濤洶湧,凶險異常,一不小心就會擱淺甚至是沉沒。然而徽商的可貴之處在於,他們受到挫折之後,並非一蹶不振,從此便銷聲匿跡,而是義無反顧、百折不撓,不成功決不罷休。許多徽州大商人都是經歷了無數次失敗,最後終於成功走上致富的道路。
其三,度勢趨時的競爭精神。市場風雲變幻莫測,活躍於市場的徽商必須時時細心預測市場,觀察市場動向,分析市場行情,審時度勢,根據市場商品種類的盈虛和供求情況,對目標市場進行細分,去選擇所經銷的商品,並且能夠使經營時間、地點隨供求關系的變化而靈活機變。他們所從事的五大行業:食鹽、糧食、木材、茶葉、典當無不是根據市場行情的變化而隨機經營的。正是由於他們能夠隨時觀察市場,根據市場變化審時度勢,因此面對同行業的競爭,他們時時能走在同行業的前面,能夠出奇制勝。
其四,以眾幫眾的和協精神。徽商的和協精神不僅表現在家族中,也表現在一個個的商業團體中。即便在整個徽州商幫內部,也能做到同舟共濟、以眾幫眾。遍布各地的徽州會館、同業公所的建立,就突出體現了這種精神,從而大大地強化了徽州商幫內部的凝聚力,提高了市場競爭力。
其五,惠而不費的勤儉精神。大多徽商是從小本起家,不畏艱難,克服了種種不利因素,經過了一番奮斗拼搏,最後才建立了自己的基業,成為富商大賈的。“致富思源”,他們大多數人特別珍惜得來不易的財富。因此,他們雖然致富,但日常生活仍舊保持在家時的艱苦樸素的作風。不僅如此,他們還以艱苦樸素的勤儉精神教育子孫。
其六,以義制利的奉獻精神。這突出表現在大量徽商發財致富後,以種種“義行”、“義舉”來奉獻社會。徽商由於“賈而好儒”,因而絕大多數人在經商活動中比較重視人文精神、講求理性追求。雖然致富,但他們依然自奉儉約,克勤克儉。不過一旦當他們面對國難民困或旱荒水災時,卻又會慷慨解囊,將財富奉獻給社會。
其七,賈而好儒的文化精神。“賈而好儒”是徽商的顯著特點。徽商很愛讀書,他們有的白天經商,晚上讀書。在路途中也是時時忘不了讀書。愛讀書給徽商帶來了三個方面的影響:一是提高了徽商的文化素養、文化品位。這樣,較高的文化素質就成為他們與官僚士大夫交往的“黏合劑”。同時也給徽商的商業經營同樣帶來了許多便利;二是由於讀書,使得徽商善於從歷史上汲取豐富的商業經驗、智慧,促進自身商業的發展;三是增強了經商的理性認識,即他們能夠以所謂的“儒道經商”,從而形成良好的商業道德。
徽商正是憑著他們特有的徽商精神,從而能夠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乃至於發展為雄視天下的大商幫。這種精神植根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之中,又被徽商進一步發揚光大。“徽駱駝”和“績溪牛”所造就的徽商精神,不僅是徽商的巨大財富,更是徽商留給後人的寶貴遺產。
以眾幫眾的團隊精神
徽商是以血緣和地緣為紐帶結成的商幫團體。“美不美,家鄉水;親不親,故鄉人。”有著共同血緣或者地緣關系的徽商,有著很強的親緣和地緣認同意識。在人生地不熟的異鄉外地,不期然碰見了同族人或者家鄉人,徽商往往會興奮得忘乎所以。這種固有的“鄉誼觀念”和“宗族意識”,形成了徽商以眾幫眾、相互提攜的傳統。
有一吳姓徽商家族,族裡長輩就曾制定這樣的族規:凡是族中有些子弟不能讀書,並且家裡又無田可耕的,因為生活所迫不得不出外做生意,那麼族裡諸位有經營經驗的長輩在外要麼提攜他,要麼在其他親友處推薦他,好讓他能有個穩定的職業,可供其糊口,千萬不能讓他在外游手好閒,以致衍生禍患。
有位徽州商人名叫方用彬,他在經商過程中,結交了包括政府官僚、文人士大夫、缙紳商賈等等各界朋友。那麼方用彬這位名不見經傳的儒商是怎樣認識這麼多不同地區、不同社會地位的人物的呢?或者用現在的話來說,他是怎樣建立這樣一個廣泛的交際網絡的呢?要知道在當時交通、通訊都遠遠不如今天發達。答案就是除了方用彬本人喜好交游而且文學書畫無所不通外,他的同宗同鄉關系給了他許多接觸不同人物的機會。
在徽商的鄉族觀念中包含著約定俗成的道德觀念和帶有強制性的宗族族規,這些使徽商彼此之間有著很強烈的患難與共意識。這種意識客觀上成為徽商之間信息傳遞的動力泉源。一首績溪民謠這樣唱道:
有生意,就停留,沒生意,去蘇州。跑來拐去到上海,托親求友尋碼頭。同鄉肯顧愛,答應給收留。
就拿歙縣和休寧兩縣來說,明清時期,兩縣由於不少人在外經商,這些在外經商的人往往攜帶親戚朋友出外共同經營。因此往往出現這種情況:一家創業成功,那麼這家人不會獨享,往往大家共同分享,規模大的甚至能攜帶千家百家,生意小的也能攜帶幾家幾十家共同致富。
有位徽商叫許孟潔,這個人親族觀念極強,他在外生意做得非常紅火,於是親戚朋友紛紛去投靠他。凡來投靠者,他都加以提攜,於是他的親戚朋友也就個個致富。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徽商宗族之間是何等的休戚與共!
千人同心,則得千人之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
相互提攜自然也就形成了一種團隊精神,在商場競爭中造成了一個集體優勢。
近代徽州人胡適早就認識到徽商宗族團體的優勢,他聽說家鄉績溪准備編纂縣志時,就說:“縣志應該注重縣裡人移動轉徙經商的分布與歷史,縣志不能夠只見小績溪,而不看見那更重要的‘大績溪’,若無那大績溪,小績溪早已不成個局面。”胡適所說的“大績溪”實際上就是靠宗族紐帶聯系的散落於各地經商的績溪人團體。宗族意識隱含的強制性在這裡起著關鍵性作用。
比如說,一旦出現一些不顧家鄉的族人,族中一些長老就會百般對他們進行勸誡,說:“我們徽州家鄉一直保留著千百年的祖墓,千百年的祠堂,千百戶的鄉村。這些在其他地方是沒有的啊。假如你們背離了家鄉,即使子孫可以長保富貴,但是他們在外地已成為孤家單親,假設出現家業敗落的情況,就會無依無靠。這種輕易背離家鄉的事情,你可要謹慎地好好想想!”這些輿論說教再加上道德和宗族法規的制約,使宗族和鄉緣之鏈堅實而牢靠,也就使徽商的團隊精神愈加發揚,團隊力量也就愈加壯大。
正是由於徽商具有強大的團隊精神,他們在挫敗競爭對手後,憑自身實力往往進一步變一般經營為壟斷經營,謀取高額利潤。如兩淮的鹽業、北京的茶業、松江的布業等,差不多都是由徽商壟斷的。
此外,明清商人畢竟處在封建時代,由於封建意識的狹隘性,商業經營者之間往往對經驗和技術相互加以保密。但是,在具有“以眾幫眾”團隊精神的徽商內部,這種情況卻很少存在。雖然商人深知商業經驗的價值,一般不會輕易傳人,但是徽商是通過血緣和地緣關系建立起來的商幫集團,經驗的傳授也就順理成章了。再加上徽商的行業宗族化和行業地緣化的特點,商業的成敗、興衰直接與本族、本地利益息息相關,所以前人也就樂於向後人傳授經驗。這種以鄉族親緣為紐帶的關系網絡,使徽商具有同時期其他商幫所沒有的信息交流優勢。
不做“茴香蘿卜干”
敬業精神是從業者對所從事職業具有的一種執著的信念和深深投入的意識。
明清徽州地區從事商業活動的人口很多,幾乎超過全地區人口的一大半。明清筆記體小說《豆棚閒話》說:徽州風俗慣例,一般人一到16歲左右就要出門學做生意。徽州還有一則民諺說: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
一般人家生活貧困,小孩長到十五六歲,就要隨鄉族長輩出外學做生意,尋覓謀生之路。一開始他們多半是在自己的長輩或親戚的店鋪裡當學徒。學徒一般歷時三年,三年的學徒生活是相當辛苦的。吃苦倒是小事,關鍵要能圓滿結束學業,否則就要被人嘲笑。
在外學徒以及日後獨自做生意,最忌諱被人稱作“茴香蘿卜干”。因為“茴香”諧音為“回鄉”,“蘿卜”諧音為“落泊”,意為在外學無所成或者經營不善落泊回鄉。所以徽商無論拜師學徒還是日後獨自闖蕩商海,他們都會兢兢業業、勤勤懇懇,一旦生意不成功,他們寧願客死他鄉,也不願輕易回家。
徽商對商業的執著和專注,在中國商業史上可以說是相當罕見的。許多人離家別妻,一年到頭奔波於外。明萬歷《休寧縣志》說:休寧縣百姓往往身揣資本,出外四處經商謀生。他們做生意一般講究公平,往往以物美價廉取勝。他們在商海經營往往一直到老才罷休。經商期間,按照徽州的風俗,經營者一般每年回家探親一次,然而那些離家遠的三四年才能夠回家與父母妻兒團聚一次。探視之後又要出門繼續經營生意。
雖然如此年復一年地在外操勞,黑發出門白發回,但他們依然無怨無悔。甚至有的徽商外出,數十年而不歸。
健婦持家身作客,黑頭直到白頭回。兒孫長大不相識,反問老翁何處來。
上面這首新安竹枝詞就是徽人經商的真實寫照。出門時孩兒還在襁褓中,回來時孩子都已長大成人,他們腦中的父親往往只是個概念而已,如今父親回來了,他們自然不認識。
民國《歙縣志》說:“我縣習俗重經商。經商必然遠離家門。每每離開家門,往往幾年才回來一次,有時甚至長年在外不回家的。剛剛結婚,丈夫就離家經商的情況,在這裡比比皆是,都習以為常了。”
清代婺源縣有一位商人姓詹,他在兒子出生幾個月後就離家出外經商,結果一別就是17年。兒子長大後決心追尋當年父親的蹤跡,把父親給找回來。於是兒子深入四川、雲南等山區,又遍尋湖北、四川成都等地,最終把父親給找到,父子相攜而歸。還有一位歙縣商人程世铎,六歲便隨父親出外經商,直到27歲才輾轉回家。所以有人說,新安商人“出至10年、20年、30年不歸,歸則孫娶媳婦而子或不識其父”。徽州商人一生無怨無悔投身於商業經營的行為,充分體現了他們的敬業精神。
徽商的敬業精神,不僅僅表現在徽商個人的一生無悔投入商業的行為方面,更體現在商人家族對商業世代不懈、前赴後繼的執著和追求。
徽州居民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聚族而居,往往一村甚至一鄉都是一個家族,所謂“千丁之族,未嘗散處”。他們宗族觀念濃厚,宗法成為維系家族關系的紐帶。同樣,在經商中,宗法在族人中同樣起著重要的關聯作用,往往出現“舉族經商”的情況,族人之間在經商中相互提攜、相互關照。
舉族經商的結果,是在徽州形成了一些著名的商人家族,譬如歙縣的汪氏家族、江氏家族、鮑氏家族,休寧的吳氏家族,婺源的朱氏家族等等。這種舉族上下成百上千人對商業的投入和專心,在明清時期的其他商幫中是不多見的。其中許多家庭都是幾代人前僕後繼,勤懇敬業,潛心經商。
譬如祁門倪國樹,頗具經商才能,曾販木饒河,後不幸溺死在一處渡口。其子起蟄當時還在襁褓中,長大後立志繼續父志,努力學習經商,經商中不圖厚利,往往以義為利,聲名遠播,最後成為一名富商。
在徽州《許氏家譜》中,還記載了一段更為感人的“家庭創業史”:許氏家族中有一人名叫許道善,年輕時曾在清源經商,因為他善於經營,贏利累至千金,在當地商人中名列前茅。後來中途回家,商業隨之中斷,家中逐漸困頓。道善看著兒子們漸漸長大,於是決心復出經商。他命兒子永京主持家事,自己只身前往臨清經商。不久,因遇騷亂,道善所帶資金耗竭,又染病不愈,竟客死異鄉。其子永京為了振興家業,毅然繼承父志,告別母親與妻兒,循著父親的足跡出外經營。沒想到他這一去就是幾十年,最後也是死於異鄉。永京的兒子長大成人後,母親拿出自己的私房錢,命他繼續出門經商,完成爺爺和父親未竟的事業。結果功夫不負有心人,許家終於在商業上獲得成功,家業重新振興起來。這樣的事例在徽商中還有很多。
熱門文章
熱門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