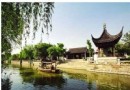梁思成、林徽因合著的《晉汾古建築預查紀略》
日期:2016/12/15 1:22:04 編輯:中國古代建築
本文節選自梁思成、林徽因合著的《晉汾古建築預查紀略》,原題為《太原縣晉祠》,全文載《中國營造學社匯刊》1935年第五卷第三期。
晉祠離太原僅五十裡,汽車一點多鐘可達,歷來為出名的“名勝”,聞人名士由太原去游覽的風氣自古盛行。我們在探訪古建的習慣中,多對“名勝”懷疑:因為最是“名勝”容易遭“重修”的大毀壞,原有建築故最難得保存!所以我們雖然知道晉祠離太原近在咫尺,且在太原至汾陽的公路上,我們亦未嘗預備去訪“勝”的。
直至赴汾的公共汽車上了一個小小山坡,繞著晉祠的背後過去時,忽然間我們才驚異地抓住車窗,望著那一角正殿的側影,愛不忍釋。相信晉祠雖成“名勝”卻仍為“古跡”無疑。那樣魁偉的殿頂,雄大的斗栱,深遠的出檐,到汽車過了對面山坡時,尚巍巍在望,非常醒目。晉祠全部的布置,則因有樹木看不清楚,但范圍不小,卻也是一望可知。
我們慚愧不應因其列為名勝而即定其不古,故相約一月後歸途至此下車,雖不能詳察或測量,至少亦得浏覽攝影,略考其年代結構。
由汾回太原時我們在山西已過了月余的旅行生活,心力俱疲,還帶著種種行李什物,諸多不便,但因那一角殿宇常在心目中,無論如何不肯失之交臂,所以到底停下來預備作半日的勾留,如果錯過那末後一趟公共汽車回太原的話,也只好聽天由命,晚上再設法露宿或住店!
在那種不便的情形下,帶著一不做、二不休的拼命心理,我們下了那擠到水洩不通的公共汽車,在大堆行李中撿出我們的“粗重細軟”——由杏花村的酒壇子到峪道河邊的蘭芝種子——累累贅贅的,背著掮著,到車站裡安頓時,我們幾乎埋怨到晉祠的建築太像樣——如果花花簇簇的來個乾隆重建,我們這些麻煩不全省了麼?
但是一進了晉祠大門,那一種說不出的美麗輝映的大花園,使我們驚喜愉悅,過於初時的期望。無以名之,只得叫它作花園。其實晉祠布置又像廟觀的院落,又像華麗的宮苑,全部兼有開敞堂皇的局面和曲折深邃的雅趣,大殿樓閣在古樹婆娑池流映帶之間,實像個放大的私家園亭。
所謂唐槐周柏,雖不能斷其為原物,但枝干奇偉,虬曲橫臥,煞是可觀。池水清碧,游魚閒逸,還有後山石級小徑樓觀石亭各種襯托。各殿雄壯,巍然其間,使初進園時的印象,感到俯仰堂皇,左右秀媚,無所不適。雖然再進去即發現近代名流所增建的中西合璧的丑怪小亭子等等,夾雜其間。
聖母廟為晉祠中間最大的一組建築;除正殿外,尚有前面“飛梁”(即十字木橋),獻殿及金人台,牌樓等等,今分述如下:
晉祠聖母廟大殿,重檐歇山頂,面闊七間進深六間,平面幾成方形,在布置上,至為奇特。殿身五間,副階周匝。但是前廊之深為兩間,內槽深三間,故前廊異常空敞,在我們尚屬初見。
斗栱的分配,至為疏朗。在殿之正面,每間用補間鋪作一朵,側面則僅梢間用補間鋪作。下檐斗栱五鋪作,單栱出兩跳;柱頭出雙下昂,補間出單杪單下昂。上檐斗栱六鋪作,單栱出三跳,柱頭出雙杪單下昂,補間出單杪雙下昂,第一跳偷心,但飾以翼形拱。但是在下昂的形式及用法上,這裡又是一種曾未得見的奇例。柱頭鋪作上極長大的昂嘴兩層,與地面完全平行,與柱成正角,下面平,上面斫幽頁,並未將昂嘴向下斜斫或斜插,亦不求其與補間鋪作的真下昂平行,完全真率地坦然放在那裡,誠然是大膽誠實的做法。在補間鋪作上,第一層昂昂尾向上挑起,第二層則將與令栱相交的耍頭加長斫成昂嘴形,並不與真昂平行的向外伸出,這種做法與正定龍興寺摩尼殿斗栱極相似,至於其豪放生動,似較之尤勝。在轉角鋪作上,各層昂及由昂均水平的伸出,由下面望去,頗呈高爽之象。山面除梢間外,均不用補間鋪作。斗栱彩畫與《營造法式》卷三十四“五彩遍裝”者極相似。雖屬後世重裝,當是古法。
這殿斗栱俱用單栱,泥道單栱上用柱頭枋四層,各層枋間用斗墊托。闌額狹而高,上施薄而寬的普拍枋。角柱上只普拍枋出頭,闌額不出。平柱至角柱間,有顯著的生起。梁架為普通平置的梁,殿內因黑暗,時間匆促,未得細查。前殿因深兩間,故在四椽栿上立童柱,以承上檐,童柱與相對之內柱間,除斗栱上之乳栿及割牽外,柱頭上更用普拍枋一道以相固濟。
按衛聚賢《晉祠指南》,稱聖母廟為宋天聖年間建。由結構法及外形姿勢看來,較《營造法式》所訂的做法的確更古拙豪放,天聖之說當屬可靠。
獻殿獻殿在正殿之前,中隔放生池。殿三間,歇三頂。與正殿結構法手法完全是同一時代同一規制之下的。斗栱單栱五鋪作,柱頭鋪作雙下昂,補間鋪作單杪單下昂,第一跳偷心,但飾以小小翼形拱。正面每間用補間鋪作一朵,山面唯正中間用補間鋪作;柱頭鋪作偽雙下昂,完全平置,後尾承托梁下,昂嘴與地面平行,如正殿的昂。補間則下昂後尾挑起,耍頭與令栱相交,長長伸出,斫作昂嘴形。兩殿斗栱外面不同之點,惟在令栱之上,正殿用通長的拂檐枋,而獻殿則用替木。斗栱後尾惟下昂挑起,全部偷心,第二跳跳頭安梭形“栱”,單獨的昂尾挑在平榑之下。至於柱頭普拍枋,與正殿完全相同。
獻殿的梁架,只是簡單的四椽栿上放一層干梁,梁身簡單輕巧,不弱不費,故能經久不壞。
殿之四周均無牆壁,當心間前後辟門,其余各間在堅厚的檻牆之上安直棂柵欄,如《營造法式》小木作中之叉子,當心間門扇亦為直棂柵欄門。
殿前階基上鐵獅子一對,極精美,筋肉真實,靈動如生。左獅胸前文曰“太原文水弟子郭丑牛兄……政和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座後文為“靈石縣任章常柱任用段和定……”,右獅字不全,只余“樂善”二字。
飛梁正殿與獻殿之間,有所謂“飛梁”者,橫跨魚沼之上。在建築史上,這“飛梁”是我們現在所知的惟一的孤例。本刊五卷一期中,劉敦桢先生在《石柱橋述要》一文中,對於石柱橋有詳細的伸述,並引《關中記》及《唐六典》之中所記錄的石柱橋。就晉祠所見,則在池中立方約30厘米的石柱若干,柱上端微卷殺如殿宇之柱,柱上有普拍枋相交,其上置斗,斗上施十字栱相交,以承梁或額。在形制上這橋誠然極古,當與正殿獻殿屬於同一時期。而在名稱上尚保存著古名,謂之飛梁,這也是極罕貴值得注意的。
金人獻殿前牌樓之前,有方形的台基,上面四角上各立鐵人一,謂之金人台。四金人之中,有兩個是宋代所鑄,其西南角金人胸前鑄字,為宋故綿州魏城令劉植……等於紹聖四年立。像塑法平庸,字體尚佳。其中兩個近代補鑄,一清朝,一民國,塑鑄都同等的惡劣。
晉祠范圍以內,尚有唐叔虞祠,關帝廟等處,匆促未得入覽,只好俟諸異日。唐貞觀碑原石及後代另摹刻的一碑均存,且有碑亭妥為保護。
晉祠離太原僅五十裡,汽車一點多鐘可達,歷來為出名的“名勝”,聞人名士由太原去游覽的風氣自古盛行。我們在探訪古建的習慣中,多對“名勝”懷疑:因為最是“名勝”容易遭“重修”的大毀壞,原有建築故最難得保存!所以我們雖然知道晉祠離太原近在咫尺,且在太原至汾陽的公路上,我們亦未嘗預備去訪“勝”的。
直至赴汾的公共汽車上了一個小小山坡,繞著晉祠的背後過去時,忽然間我們才驚異地抓住車窗,望著那一角正殿的側影,愛不忍釋。相信晉祠雖成“名勝”卻仍為“古跡”無疑。那樣魁偉的殿頂,雄大的斗栱,深遠的出檐,到汽車過了對面山坡時,尚巍巍在望,非常醒目。晉祠全部的布置,則因有樹木看不清楚,但范圍不小,卻也是一望可知。
我們慚愧不應因其列為名勝而即定其不古,故相約一月後歸途至此下車,雖不能詳察或測量,至少亦得浏覽攝影,略考其年代結構。
由汾回太原時我們在山西已過了月余的旅行生活,心力俱疲,還帶著種種行李什物,諸多不便,但因那一角殿宇常在心目中,無論如何不肯失之交臂,所以到底停下來預備作半日的勾留,如果錯過那末後一趟公共汽車回太原的話,也只好聽天由命,晚上再設法露宿或住店!
在那種不便的情形下,帶著一不做、二不休的拼命心理,我們下了那擠到水洩不通的公共汽車,在大堆行李中撿出我們的“粗重細軟”——由杏花村的酒壇子到峪道河邊的蘭芝種子——累累贅贅的,背著掮著,到車站裡安頓時,我們幾乎埋怨到晉祠的建築太像樣——如果花花簇簇的來個乾隆重建,我們這些麻煩不全省了麼?
但是一進了晉祠大門,那一種說不出的美麗輝映的大花園,使我們驚喜愉悅,過於初時的期望。無以名之,只得叫它作花園。其實晉祠布置又像廟觀的院落,又像華麗的宮苑,全部兼有開敞堂皇的局面和曲折深邃的雅趣,大殿樓閣在古樹婆娑池流映帶之間,實像個放大的私家園亭。
所謂唐槐周柏,雖不能斷其為原物,但枝干奇偉,虬曲橫臥,煞是可觀。池水清碧,游魚閒逸,還有後山石級小徑樓觀石亭各種襯托。各殿雄壯,巍然其間,使初進園時的印象,感到俯仰堂皇,左右秀媚,無所不適。雖然再進去即發現近代名流所增建的中西合璧的丑怪小亭子等等,夾雜其間。
聖母廟為晉祠中間最大的一組建築;除正殿外,尚有前面“飛梁”(即十字木橋),獻殿及金人台,牌樓等等,今分述如下:
晉祠聖母廟大殿,重檐歇山頂,面闊七間進深六間,平面幾成方形,在布置上,至為奇特。殿身五間,副階周匝。但是前廊之深為兩間,內槽深三間,故前廊異常空敞,在我們尚屬初見。
斗栱的分配,至為疏朗。在殿之正面,每間用補間鋪作一朵,側面則僅梢間用補間鋪作。下檐斗栱五鋪作,單栱出兩跳;柱頭出雙下昂,補間出單杪單下昂。上檐斗栱六鋪作,單栱出三跳,柱頭出雙杪單下昂,補間出單杪雙下昂,第一跳偷心,但飾以翼形拱。但是在下昂的形式及用法上,這裡又是一種曾未得見的奇例。柱頭鋪作上極長大的昂嘴兩層,與地面完全平行,與柱成正角,下面平,上面斫幽頁,並未將昂嘴向下斜斫或斜插,亦不求其與補間鋪作的真下昂平行,完全真率地坦然放在那裡,誠然是大膽誠實的做法。在補間鋪作上,第一層昂昂尾向上挑起,第二層則將與令栱相交的耍頭加長斫成昂嘴形,並不與真昂平行的向外伸出,這種做法與正定龍興寺摩尼殿斗栱極相似,至於其豪放生動,似較之尤勝。在轉角鋪作上,各層昂及由昂均水平的伸出,由下面望去,頗呈高爽之象。山面除梢間外,均不用補間鋪作。斗栱彩畫與《營造法式》卷三十四“五彩遍裝”者極相似。雖屬後世重裝,當是古法。
這殿斗栱俱用單栱,泥道單栱上用柱頭枋四層,各層枋間用斗墊托。闌額狹而高,上施薄而寬的普拍枋。角柱上只普拍枋出頭,闌額不出。平柱至角柱間,有顯著的生起。梁架為普通平置的梁,殿內因黑暗,時間匆促,未得細查。前殿因深兩間,故在四椽栿上立童柱,以承上檐,童柱與相對之內柱間,除斗栱上之乳栿及割牽外,柱頭上更用普拍枋一道以相固濟。
按衛聚賢《晉祠指南》,稱聖母廟為宋天聖年間建。由結構法及外形姿勢看來,較《營造法式》所訂的做法的確更古拙豪放,天聖之說當屬可靠。
獻殿獻殿在正殿之前,中隔放生池。殿三間,歇三頂。與正殿結構法手法完全是同一時代同一規制之下的。斗栱單栱五鋪作,柱頭鋪作雙下昂,補間鋪作單杪單下昂,第一跳偷心,但飾以小小翼形拱。正面每間用補間鋪作一朵,山面唯正中間用補間鋪作;柱頭鋪作偽雙下昂,完全平置,後尾承托梁下,昂嘴與地面平行,如正殿的昂。補間則下昂後尾挑起,耍頭與令栱相交,長長伸出,斫作昂嘴形。兩殿斗栱外面不同之點,惟在令栱之上,正殿用通長的拂檐枋,而獻殿則用替木。斗栱後尾惟下昂挑起,全部偷心,第二跳跳頭安梭形“栱”,單獨的昂尾挑在平榑之下。至於柱頭普拍枋,與正殿完全相同。
獻殿的梁架,只是簡單的四椽栿上放一層干梁,梁身簡單輕巧,不弱不費,故能經久不壞。
殿之四周均無牆壁,當心間前後辟門,其余各間在堅厚的檻牆之上安直棂柵欄,如《營造法式》小木作中之叉子,當心間門扇亦為直棂柵欄門。
殿前階基上鐵獅子一對,極精美,筋肉真實,靈動如生。左獅胸前文曰“太原文水弟子郭丑牛兄……政和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座後文為“靈石縣任章常柱任用段和定……”,右獅字不全,只余“樂善”二字。
飛梁正殿與獻殿之間,有所謂“飛梁”者,橫跨魚沼之上。在建築史上,這“飛梁”是我們現在所知的惟一的孤例。本刊五卷一期中,劉敦桢先生在《石柱橋述要》一文中,對於石柱橋有詳細的伸述,並引《關中記》及《唐六典》之中所記錄的石柱橋。就晉祠所見,則在池中立方約30厘米的石柱若干,柱上端微卷殺如殿宇之柱,柱上有普拍枋相交,其上置斗,斗上施十字栱相交,以承梁或額。在形制上這橋誠然極古,當與正殿獻殿屬於同一時期。而在名稱上尚保存著古名,謂之飛梁,這也是極罕貴值得注意的。
金人獻殿前牌樓之前,有方形的台基,上面四角上各立鐵人一,謂之金人台。四金人之中,有兩個是宋代所鑄,其西南角金人胸前鑄字,為宋故綿州魏城令劉植……等於紹聖四年立。像塑法平庸,字體尚佳。其中兩個近代補鑄,一清朝,一民國,塑鑄都同等的惡劣。
晉祠范圍以內,尚有唐叔虞祠,關帝廟等處,匆促未得入覽,只好俟諸異日。唐貞觀碑原石及後代另摹刻的一碑均存,且有碑亭妥為保護。
- 上一頁:梁思成談曲阜孔廟
- 下一頁:敦煌壁畫中的唐代建築
熱門文章
熱門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