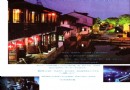陝西大荔石墓群:村民曾因建房將石墓拆除搬回家
日期:2016/12/15 1:18:57 編輯:中國古代建築大荔縣沙土下的八魚石墓群,半個世紀來屢遭盜竊、破壞,發掘十多年鮮被世人所知。但這個被譽為明清同期同類等級最高的石墓群,卻訴說著一個家族的興衰,同時也記錄了陝商甚至一個時代的變遷。
“故日的沙塵埋沒了鮮為人知的家世,一段有趣的考古發掘卻續接了先輩與後世的對話”。正如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秦漢研究室主任田亞岐所寫,埋葬在大荔縣沙土下的八魚石墓群,半個世紀來屢次遭到盜竊、破壞,發掘十多年卻鮮被世人所知。但這個被譽為明清同期同類等級最高的石墓群,卻訴說著一個家族的興衰,同時,也記錄了陝商甚至一個時代的變遷。
2015年清明節臨近,40歲的富平人徐世強為了給朋友的祖上刻墓碑,在富平縣宮裡鎮一些石雕廠轉悠。
富平縣宮裡鎮北部,有延綿東西的喬山山脈,蘊藏著豐富的青石資源。其最上乘的青石稱為“墨玉”,墨黑色的石頭如同一面鏡子,其光亮可照人。敲之響聲朗朗,余音似磬,又叫“磬石”,是石雕的上乘原料。
產石之地,自然也是雕刻大師雲集之所。
徐世強拿著幾張微信朋友圈裡下載的照片,找當地一位五旬的雕刻大師,詢問是否有圖片中石雕的手藝。大師看了片刻搖搖頭說,這圖片是假的,因為民間早已經沒有這種手藝了。
徐世強手機中的照片,來自鄰縣大荔縣八魚村的一片石墓群。
村民建房將整座石墓拆除搬回家
2001年2月,八魚村村民張福平以建房為名,將村子附近一座古墓徹底拆除。
拆除的石墓構件,從他們家院子一直擺到家門後的村裡街道上。盡管過去幾十年中,村裡人對於到村外“財東”墓地取石頭已經習以為常,但這種行為還是引起了村支部書記李志義的重視。
事情雖然過去14年,2015年3月12日,李志義依然記得當年的情景。他當時立即將此事報告給八魚鄉政府(現在撤鄉並鎮,並入羌白鎮)。
緊接著的2001年 2月11日,陝西省文物局突然接到渭南市文物局的緊急報告:在位於大荔縣縣城以西15公裡處的八魚鄉八魚村,村民在取土場挖土時,發現一個用石材擺布的地下空間結構,上面還有精美的花卉與雕刻圖案。
省文物局當即決定派田亞岐作為省上專業人員會同當地主管部門去現場了解情況。田亞岐後來也沒想到,他這個“秦漢”考古專家,後來因為這件事,變成了半個“明清”專家。
2015年3月10日,身為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秦漢研究室主任的田亞岐回想當年的一幕 :“當日午飯前我就趕到當地與同行會合。當我從水洩不通的圍觀人群擠進臨時圈起的保護現場時,眼前的景象確實讓我吃驚,我從來沒有見過如此細琢考究的石質材料,盡管整體結構已坍塌或被移位,但基本布局和架構仍在”。
田亞岐看到,很多雕刻精美的青石材料搭建出一個個地下庭院,有斜坡通道、院落、門前兩側影壁、中庭、偏房、洞室等,每個單元的整體空間約四五十平方米。根據現場看到的棺板朽木與門側的石刻楹聯判斷,這肯定是墓葬。
田亞岐聽村民說,早先曾在附近另一處同樣結構的墓室中取出墓志,至今仍在農戶家中當做捶布石使用,隨後考古隊員見到了墓志。從模糊不清的志文看出該墓葬的主人系清代李氏家族成員。
石墓主人為“李氏家族”的消息立刻在村裡傳了起來。村支書李志義回憶,村裡當時有約3000人,而且90%的人姓李,難道這是我們祖先的墳墓嗎?
石墓的後人在哪裡?
2015年3月14日,八魚石墓文管所所長石西陽說,“這些被拆掉的石墓構件一件不少地被從村民張福平家搬運過來,但是,大伙兒怎麼也不能把其按照原樣拼起來”。最後,大家找到了村裡一位“能人”,才勉強拼石墓予以還原。
田亞岐回到西安後,考古所當即向省文物局提交書面報告,確定了進行全面性考古調查與搶救性考古發掘的工作方案。
那麼,墓主是誰?村裡的李姓村民是否就是石墓的後人?
2001年3月1日,華商報曾刊登過古墓發現的消息。那篇題為《渭南發現清代望族墓群》約200字的消息,雖然只提到“渭南某縣”,但是第二天,還是有不少自稱李氏後人的人趕到八魚村,阻止發掘。
“我是搞秦漢研究的,秦漢古墓的發掘從來就沒有後人來,突然遇到這些古墳的後人,令我們措手不及。”田亞岐說,“業界確實曾有一種認識,說清朝以後都不能算是考古,但這一次卻是特殊的例外”。此次發掘,是陝西省明清時期一項重要的考古發現,由此將陝西省考古工作的下限由元代延伸到清代。
不過,這些“後人”頗有素質,不打不鬧,在經過一番勸說後,默默地燒完紙錢就離開了。
田亞岐後悔當時沒有留下這些“後人”的聯系方式。到底誰是李氏家族墓的後人,這個問題一度讓田亞岐困擾。
但後來,村裡一位老人的說法,給了他一些線索。老人說,他的爺爺輩已經開始給李氏家族守墓,他也曾經幫李氏家族守過墓。他隱約記得這個家族的後人住在大荔縣奓(這個字字典中讀zhā/zhà,當地讀tuo)巷。
田亞岐在當地土地部門的配合下,又經過地契最終找到了奓巷這家人的住處,但是,住在這家院子的人說他們不姓李,只是替院子的主人看房子。房客說,房東在西安交通大學當老師,年齡在60多歲,女性。
李氏族人外出“不吃別家飯,不住別家店”
最終,田亞岐找到了這個姓李的女老師。她叫李映麗,是西安交通大學醫學院教授。
2015年3月9日下午3時,西安交大醫學院家屬樓。75歲的李映麗耳聰目明、頭發烏黑,看不出是七旬老人。
她的家中,除了書就是各種古玩。“都是假的,當時考古隊說會從我祖上的古墓中挑一兩件東西留給我當作紀念,可是後來就沒人提起了”,李映麗笑著說。
對於祖上的一些事情,李映麗隱隱約約還能記起一些。“新中國成立前,每到春節,來自全國一些我們家族商鋪的人(掌櫃的),就會過來報告一年經營的狀況。他們來的時候,都會給我們這些孩子帶一些當地的特產和小吃”,所以李映麗記憶深刻。
李映麗聽奶奶講過,他們家的商鋪遍布全國,李氏家人外出可以做到“不吃別家飯,不住別家店”。她還記得,小時候,他們家房屋閣樓上曾擺放大量皇上賜的“頂戴花翎”和官服。
文革時期,李映麗在大荔縣和西安市的家中,遭到多次抄家。“家裡的字畫在一次抄家後被焚燒,燒完後的畫軸,提了幾筐子才收拾完。”
李映麗至今收藏著清代考場作弊的“夾帶”,她說這是在一次抄家後遺留在院子裡的,當時還是小姑娘的她悄悄收了起來,留作紀念。
李映麗結婚前,奶奶曾經拿出一籃子鑲著鑽石的手表,讓李映麗挑一塊當作結婚禮物。“那時的我不懂事,沒有要”。
李映麗的堂哥李武華出生在1932年,畢業於上海音樂學院,現在是西安音樂學院研究小提琴的教授。
李武華曾經難以接受自己祖墳被挖的現實,但後來慢慢接受了。
“我們知道,靠我們的能力無法保護好祖墳,最終還是接受讓政府管理”,李映麗說。
村裡李姓人都不是石墓後人
八魚石墓李氏家族的後人找到了,那麼八魚村數千李姓的村民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
田亞岐在一篇回憶錄中提到,明代中期以前,由於自然環境惡劣,“沙苑”(大荔縣當地的沙土地帶)一帶幾乎沒有固定居住戶,明末之後,居住於同州府(今大荔縣城)的大戶人家(當地稱財東)開始在此地開辟田宅,招募佃戶。
田亞岐認為,當時在這裡通過耕田達到收獲的目的只是一種借口,真正的用意是由於當時戰亂的原因,他們想在這兵卒不達、荒無人煙的地方建立各自的家族墓園。
考古專家已經勘探出,起先李姓家族在今八魚村建立首座莊園,隨後趙姓、安姓、詹姓等諸多大戶也相繼在與八魚毗鄰的王閣、東半道、東羌白、黃甫、王店、南莊等地開辟各自的莊園。剛開始莊園的主人不常駐,後來家族部分成員也慢慢住進。莊園管理者從各地招募雇工或逃戶,看守墓園。
隨著時間的推移,歷史的印記逐步從人們的記憶中消失。現今的八魚村歸羌白政府所轄,是一個擁有400多戶的大行政村。
村中有位70多歲的李姓老人告訴田亞岐,他的祖輩是上世紀30年代黃河決口之後從河南逃荒到大荔的,有的是40年前因三門峽庫區建設移民過來的。早先來這裡的人曾被李家收留並作為看墓人帶到八魚村莊園,新中國成立後,盡管他家不再有這個義務,但每逢清明節到來之際,李家人一定會從縣城、省城或其他地方趕來掃墓,還會帶著禮品拜望他家,像走親戚一樣。
現在八魚村的絕大多數人家雖然都姓李,但是他們與石墓主“李氏家族”沒有一點血緣關系。
李氏祖上疑似“關中大地震”移民
在進行搶救性發掘過程中,考古隊員們也對流散在當地村民處的一些石質文物進行回收,一個月就回收了200多件石質構件。
其中,一塊回收的墓志銘引起了專家的重視。墓主人叫李圖南(諱鵬,字仲鲲,號圖南),顯示其生卒年代是1720年到1797年,享年78歲。根據大量的其它出土碑文記載,李圖南是家族壽命最長的一位。
專家根據墓志銘了解到,李圖南所處年代為乾隆盛世,一生主要在廣東一帶經商,是李氏家族發展商貿事業的奠基人之一。
墓志銘還刻畫出李圖南的“疏財仗義,輕財樂施”。每到了“凶歲薄收”,他都拿糧物赈濟窮人。對於一些無力償還貸款的窮人,甚至一把火將借契燒掉。
田亞岐根據其他相互印證的碑文認定,李圖南的父親是李增輝,祖父是李鳳翔,曾祖父是李訓。李訓的生卒年代已經沒有記載。
李訓再向上已沒有文字記載。 但是,李圖南的碑文上的一句話,給了田亞岐無限的想象。“其先山西晉陽人也。後徙居關中”。晉陽是中國古代北方著名的大都會之一,故址在今山西省太原市晉源區。
田亞岐推測:一次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災難,讓晉陽的李訓祖上,徙居陝西關中。
1556年1月23日夜,我國渭河流域發生的一次巨大地震,估計震級為8級。據史書記載,以陝西華縣、華陰和山西永濟等地的震災最重 ,故稱為華縣地震,83萬人喪命。
田亞岐說,大地震後,關中人近乎絕跡。多年後,朝廷首先鼓勵河東(黃河以東)的民眾徙居關中。田亞岐推測,李訓的祖上最早來到關中的是老哥倆。他們極可能還是有較高文化的教書先生。
這一點在李訓的後人中有人任教育局長,有人“生而穎異,長具宏達識”中可以推斷。絕大部分墓碑上能看到,李氏家族的後人受過良好的教育。
李訓以上已經缺乏相關依據了。但是《大荔李氏家族墓地》記載:“從明末清初僅傳說而無家譜記載的三輩祖先,再從清初以後到民國時期有家譜記載的十輩人,總共十三輩人”。
遭遇戰亂盛極而衰族人流落四散
已經發掘的3號石墓,墓主叫李樹德(字滋亭)。根據墓志銘記載,李樹德讀書時,凡接受過的詩文經傳,先生稍加提示即可融會貫通。大約1830年以後,李樹德以優異成績且“捐職”任興平縣“教谕”,相當於現在的教育局長。
從李訓開始,李家發展到李樹德這一輩人,已經是有權有勢,富甲一方,可謂是大荔縣首富。
李樹德繼續發揚祖上“樂善好施”的優良傳統,先後出巨資修繕同州試院(大荔師范的前身),修補灞橋,修整縣城和八女井村(八魚村古稱)破敗的城牆廟宇。20余間李氏宗祠煥然一新。
為了能讓八魚村及其周圍家境貧寒的學童有讀書的機會,李樹德施捨良田80余畝,創辦義學,出資聘請德才兼備的老師。每遇到災荒年間,李樹德就要開倉赈濟。
李氏家族在那個年代,不但對平民如此慷慨,對朝廷也是捐贈不斷,但也因此埋下殺身之禍。清同治年間的戰亂中,李氏家族因為捐贈朝廷以及家庭的巨額財富,成為了起義軍首選的攻擊目標。李家宗祠、房捨被付之一炬。
1869年,擔驚受怕的李樹德撒手人寰,終年66歲。他被悄悄地下葬在生前就已經修建好的石墓內。從此,他的後人便舉家出走,流落四散。他們多數人落足於全國各地所開的商鋪內,有的則隱居於窮鄉僻壤。
此後,偶爾有李氏家族的後人回來。匆匆埋葬親人屍骨或者在墳前燒燒紙錢後又匆匆離去。
李氏家族和當時眾多的陝西商幫一樣,從此走向衰退。
這裡所說的僅僅是墓地內靠村莊約6萬平方米范圍內勘探出的16座墓葬(這個范圍外還有)。整個墓地南北長約1700米,東西寬約1200米,總面積達204萬平方米。
李氏家族墓地石室絕大多數石構件的面上都雕刻有內容。八魚石墓文管所所長石西陽說,其雕刻的圖案大約400多幅,分為人物故事、山水、花草、動物意想圖案和博古圖案。從雕刻手法上可分為圓雕、高浮雕、淺地刻和陰刻。
中國國家畫院院長、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昔日曾任西安美術學院院長的楊曉陽曾評價,八魚村李氏家族墓地,是目前所挖掘的同期同類家族墓葬中,規模最大、墓葬結構最為奇特、等級最高、墓葬時刻藝術品最為豐富的封建家族墓地,充分顯示了明清時期陝西關中民間石刻藝術的高超技藝。
400畝地上百個墓堆,有的高達15米
關於李氏家族墓園的具體情況,因為上世紀六十年代大規模的“平墳”運動,已看不到昔日墓園的景象,李氏家族的歷史逐漸被人們淡忘,只有幾位老者能遙想孩童時在墓園嬉耍時的情景。
當時墓園規模很大,足有400畝地,墓堆有上百個,按堂系分成若干個群落,有的墓冢很大,足有15米之高。
田亞岐聽一些老人說,以前的墓地環境優雅,園中地面擺放著石質香案、香爐等,每年除清明時節進行濃重的家族祭奠之外,春節前夕、娶親、蓋新房等也要前往祭奠。此外,李氏家族還有不成文的約定,凡在外地干事者,途經大荔或者回鄉後第一件事就是去墓地憑吊。
2015年3月12日,68歲的八魚村村民韓有娃回憶,他11歲的時候,曾經和其他孩子多次爬進石墓內。當時進入一個石墓內,裡面有5個棺木,還有石雕的金童玉女、木制方桌、大立櫃、書架等。
韓有娃還記得,一個棺材上方石頂上,還鑲有一個銅燈。印象最深的是一個棺椁上蓋有一塊綢緞,韓有娃悄悄地拿回家,“母親後來給妹妹做了兜肚”。
大荔中學退休老師李秉乾也是八魚村人,他也記得小時候到墓室“尋寶”的事情。石室有大門進不去,有人將最薄弱處的石窗戶砸開,從窗戶進入。有人發財了,“拿走了墓主人的一個眼鏡”。
有一年生產隊需要石頭,八魚村5組出動了30多名精壯勞力,開始明著破壞石墓。棺木被拿去做了生產隊飼養室的大門,很多石塊被燒石灰和水泥,有的修水渠時用掉了。
現在的石墓內,幾乎所有石雕人像都沒有了,石西陽說,當時石人頭部都是鍍金的,一些村民或者盜墓賊嫌刮金速度太慢,就直接將石人頭部敲掉,回到家再慢慢將上面的鍍金刮掉。
石牌樓被拉倒後,“保護電話”來了
現年59歲的村支書李志義 ,八九歲時也曾進入古墓裡面。他看到大立櫃裡面還有衣服。
但是他記憶最深刻的還是墓室外的一個石牌樓。他記得大概1968年左右,有一天鄉上開來了個大型拖拉機,有人上去將一條鋼絲繩綁在石牌樓的一角,然後大家躲得遠遠地,拖拉機就開始給勁。拖拉機開動得冒黑煙,一聲脆響,才將石牌樓的一個角角拉掉。
於是,一個男子再次爬上石牌樓,系好後,拖拉機再次發力。鋼絲繩繃得緊緊的,一聲巨響,10多米的牌樓轟然倒下。
“石牌樓剛倒,省上的電話來了,讓鄉上一定要保護好這座牌樓。可惜,一切都晚了”。韓有娃和李志義都記得那個遲來的電話。
2015年3月12日,華商報記者找到了當時開拖拉機拉倒石牌樓的老人唐林憲,已經74歲的老人承認自己當時按照“上面命令”拉倒石牌樓,過去的事情,他不願意再提起。
很多人記得那個牌樓上有精美的雕刻圖案,至於雕的什麼都記不起來了。有的說,是華山各個景點的縮影,但已無法考證。華商報記者從一位昔日西安美術學院學生保留下來的照片看得出,昔日的石牌樓大約有15米高,分三四層。牌樓正面能清晰看到四個大字“皇恩浩蕩”。
孩子七八歲時,父輩已給修建石墓
2013年5月14日,大荔八魚李氏家族墓地,被國務院核定列入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7年前,石西陽部隊轉業輾轉多處後到此工作,由於游客稀少,石西陽無事之時就潛入石墓揣摩,對每個圖案都能爛熟心中。閒來無事時,他便和村裡一些長輩閒聊。這種東逮一句,西逮一句的閱歷,也促成了他獨有的講解風格。
石西陽說,這些石墓大多是墓主人生前自己修建的,有的在七八歲的時候,父輩已經給孩子修建了。
在4號石墓,有一副對聯,“深深庭院隔紅塵,郁郁泉台埋白玉”,橫批是“夢一場”。這個石墓內藏有墓主李懷珍(字聘清)和他的女人,這個女人沒有名分,一直在深深的庭院內似乎和外界隔絕。
晚上無事,石西陽經常會一個人拿著手電筒鑽入墓室,從不同的角度看著一幅幅山水、花鳥或文字。他隱約感到石頭會有水滲出來,冰冷的石頭突然會變得非常柔和和水靈。
他說石頭是有生命的,那些滲出來的水,是不是石墓主人的淚珠呢?
從“李氏家族”看明清陝商
3月24日,華商報記者采訪了西北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李剛。李剛是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的專家、陝西省秦商研究會副會長、西北大學陝商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曾是“天下第一商幫”
華商報:你能介紹一下當時陝西商幫的崛起、鼎盛和衰落嗎?
李剛:陝商興起於明代初年,明政府在陝西實行了“食鹽開中制”,把陝西的糧食販到邊關去換鹽引(鹽引又稱“鹽鈔”,是販鹽憑證),然後拿鹽引去江南販鹽。一個人販鹽力量很有限,就需要大家相互聯系,形成商人集團,這是中國形成最早的商團,我給它一個定位“天下第一商幫”。
華商報:根據你的觀點,1818年以前,中國的財富占據世界的30%,而在中國,70%的財富在江南。那為何當時的三大商幫卻在經濟不是很發達的陝西、山西和安徽?
李剛:陝西商幫的形成是政府引導的結果,當時明政府為了保障邊疆安全,在陝西邊界上駐扎24萬邊防軍,那麼就需要讓商人幫助政府解決邊防軍的後勤供應。於是,以讓商人參與食鹽販運為條件,刺激商人的積極性,要把江南的鹽運回來。在這種情況下,就要推出一種新的經濟政策,叫制度創新,將食鹽和邊疆建設結合在一起,將“鹽政”和邊政結合。
人硬、話硬、貨硬
華商報:當時的三大商幫叫“徽駱駝、晉算盤、陝棒槌”這說的是什麼意思?
李剛:“徽駱駝”指的是安徽商人像駱駝一樣吃苦耐勞;“晉算盤”指的是山西商人非常精明。“陝棒槌”說明陝西人直來直去,直爽地就像棒槌一樣。當時陝商也叫“三硬商人”,即人硬、話硬、貨硬。誠信是陝西商人的最大特點,他們說一不二。
華商報:你在文章中多次提到“秦晉大賈”“山陝商人”,這是什麼意思?
李剛:這是陝商和晉商的實力變化的一種表達方式,在明代時,陝西商人的實力遠在山西商人之上,所以叫“秦晉大賈”,秦在前,晉在後;清代,晉商利用清政府的政治資源,迅速崛起,幫滿族打天下,後來貴族給晉商豐厚的回報,把八大晉商調到北京,晉商最火的時候是1831年辦了票號,所以在清代時叫“山陝商人”。
因“鄉愁”而熱心慈善
華商報:在大荔縣八魚村李氏家族墓志銘上,能看到每個墓葬主人的善舉,樂善好施,當時,陝西商人為何要這麼做?
李剛:慈善是一種結果,而起因是鄉愁,但陝商的鄉愁更加濃郁,這和他們的制度有關系。因為陝商當時實行的是股份合作的企業經營方式。“東西制”,“東方”就是“財東”光投資不經營;掌櫃就是“西方”,從東家手裡領取資金,所以他們也叫“領東掌櫃”、“帶肚子掌櫃”。
出去10年為一個屯周期,也就是說一個商人12歲離開家,到60歲告老還鄉,中間48年只能回來4次,每次住一年。同時,東家為保證投資安全,就把掌櫃的父母妻兒放在家裡,這也是一種投資保險制度。
那麼掌櫃的不在家的日子裡,他就要為家裡人營造一種良好的人際氛圍,等家裡遇到事情時,鄉黨鄰裡也會出手相助,所以就要進行大量的家鄉建設,結緣鄉黨。
徽商不存在這個現象,因為徽商走到哪裡都可以把家人帶著,晉商和陝商相似,但沒有陝商嚴格。
華商報:明代松江府(今上海蘇州河以南地區)嘉興鎮就有“機聲扎扎連夜操,關中賈來價更高”的歌謠,說的是關中商人做生意不斤斤計較,不在乎價格,是這樣的嗎?
李剛:這說明陝西人做生意很大氣,不計較分毫,和現在的煤老板有點相似。因為明清時期陝西商人多是從農民起步的,或多或少帶有暴發戶的色彩。但是,他們更看重商機和機遇,他們能看得更長遠,所以往往忽視小利。
李氏家族的興衰,也見證了陝商的興衰
華商報:有關陝商的史冊上,大量記錄了陝商和其他商幫比賽往河裡扔銀子的故事,這些說明了什麼?
李剛:陝商和晉商以及陝商和晉商聯手抵觸徽商的競爭從未停止。河南社旗鎮是河南布匹的主要交易市場,唐河的水運為棉布交易提供了便利的條件,所以從清代初葉起,山陝商人就到社旗壟斷棉布貿易。最初,山西商人勢力興盛,一王姓晉商獨占著社旗的布匹生意,陝西韓城黨家商人很不服氣,要與晉商一爭高下,於是雙方約定往唐河裡扔銀子,誰扔得多,誰就獨占市場。
華商報:八魚李氏家族世居同州府(府治今大荔縣),當時的同州商人在陝西商幫中是什麼地位?
李剛:明清時代出現的陝商是以同州府的商人為核心。陝西的財東、大商人都集中在渭北一代(大荔、富平、泾陽、三原等地),因為這些地方是產糧大縣,陝西商人也是完全依據明清時期“食鹽開中制”的政策,農民進城經商所形成的商業集團。
華商報:當時的陝西商幫都做什麼生意?
李剛:明清時期,陝西商人經營八大產業:食鹽、布匹、皮貨、藥材、水煙、木材、典當、釀酒。陝商把陝西定邊花馬池的鹽販到伊蒙草原、甘肅、青海、鳳翔、漢中等地,然後把伊蒙草原的皮革加工成皮革制品販到江南,回來又把江南的布匹帶回來;把陝西的藥材、水煙販賣到江南,將江南的茶葉帶回。
史料記載,八魚村毗鄰的羌白鎮,明清曾經是著名的皮制品生產和交易地。這些原料多來自甘肅和陝北,加工後銷往天津和北京。除了牛羊皮外,還有少量的虎、豹、狼、狐皮。
其實,一個八魚李氏家族的興衰,剛好見證了明清陝西商幫的興衰。他是陝西商幫的真實寫照和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