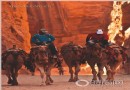金陵六朝古都的不張揚之美
日期:2016/12/14 17:54:28 編輯:古建園林 這座曾被稱作金陵的城市,雖為六朝古都,卻從來都不是一座張揚的城池。她的味道可以無關縱橫時光的歷史,也可以無關闖蕩格局的現在,宏觀如當年規劃得幾近完美的理想首都,微觀如當下仍蕩漾在大街小巷的丹桂沁甜,恰如淺吟低唱的昆曲,婉轉反復,回蕩在金戈鐵馬之外。她將各種不溫不火、不疾不徐的氣質一並收留,留予我們一唱三歎。
城東:自然況味,良辰美景奈何天
清晨的光線筆直地穿透半空中交錯遮天的梧桐樹冠,打散的光束粗細不等,斜斜地支撐在起伏逶迤的植物園路上,沿路前行不遠,便是明孝陵。
已經記不清是第幾次鑽進這個入口了,幾乎每次來到南京都要進紫金山,去看看在四季的輪回中微妙變化的梧桐大道,而明孝陵便是心間默認的第一進庭院。
紫金山的確是南京城東一個十分奇妙的所在。它是帝王、領袖、先驅的陵園、墓冢,極盡肅穆的拜谒憑吊之處,也是自然風景區,是徒步、騎行、野餐、游戲撒歡兒地,是極盡歡樂的全民健身娛樂中心。這樣的混搭即使在紫金山自己看來應該也並不是一種沖撞——沒有人規定陵園就一定要冷清蕭索。
明孝陵的前世今生有太多故事,神道上的石象路也早已成為一張深入人心的南京旅游名片,很多人對南京的印象都是由一幅深秋神道濃郁而靜美的畫面開始的。
而石象路幾乎是紫金山最充滿意趣和韻味的一段。對稱排列的12對石獸神態溫潤、祥和恬靜,掩映在落英缤紛中,尤能讓人安神。神道的四季是一席流動的盛宴,春有梅花競放,燦若雲霞;夏有濃蔭蔽日,清涼舒爽;金秋最為馥郁,叢叢簇簇金黃的銀杏葉與艷紅的楓葉此起彼伏,飒飒秋風與幽幽蟬鳴吟哦不歇;冬日裡,此路竟別有一番蕭簡氣氛,人從四方城進來,一路慢行至此,與古人的對話已完成過半。
從明朝到民國,在此山步行半小時左右即可實現。當身邊的游人漸漸多起來,我便知道,先生近了。
“青山有幸埋忠骨”,說的當然是革命先行者孫中山的陵寢。中山陵總設計師呂彥直幼居巴黎,酷愛藝術,青年時在清華大學和美國康奈爾大學修習建築,後成為著名美國設計師墨菲的助手,這師徒二人是南京建築設計與城市規劃當之無愧的功臣。顯而易見,呂彥直的設計理念是將陵墓巧妙地融於紫金山的自然環境之中,依勢造景,讓中山陵的總體結構呈現為一座大氣懾人的“自由鐘”。
從古意缱绻的明孝陵一路上來,時空與心神都在不慌不忙地悄悄完成一趟穿越。順應傳統的中軸線對稱布局,打破傳統的藍瓦白牆,中山陵的設計體系自成一體,邏輯周全。而每一個拜谒中山陵的來訪者也會漸漸明白,什麼是先生畢生追求的自由、平等、博愛。
城南:市井真味,賞心樂事誰家院
南京的市民文化可以追溯到六朝時代。城西石頭城作為當時的軍事要塞,是南京城發展的起點,政權的轉移伴隨著民眾的遷徙,南京自古便是移民城市。
這座城還有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從建城之始便有明確的城市分區。推演到春秋戰國時,吳越爭雄的戰場就在今天的溧陽,南京城的百姓便是由南部環太湖流域的蘇州等地逐漸北上而來。
秦淮河流域蔓延開的南城即是金陵最早的市民居住區,市民文化和秦淮文化的誕生地。直到清朝,南京的市民生活圈才逐漸隨生產生活的需要由秦淮河流域推至今天的白下路-建邺路為限,至於新街口成為市中心,那著實是20世紀70年代之後的事情了。
我乘地鐵直抵明城牆南門中華門,以這裡為起點,沿著十裡秦淮向上回溯,探訪城南。世人都知道明城牆是全世界最長的一座磚砌城牆,卻鮮少有人知道中華門是全國所有古城中最大的一道城門。早在修築這工程的六百年前,巴黎城的周長還不足30公裡。
這條舉世聞名的人工屏障高度一般在14至21米之間,最高達60米,相當於20層樓房。城基的寬度約14米,頂部寬度在4至9米之間,最寬處達25米,可任戰馬馳騁。大部分城牆都先用花崗或石灰巖的條石作基礎,條石上用大磚壘砌內外兩壁,壁間以碎磚、礫石和黃土層層夯實,再以大磚鋪出牆頂並砌成城垛。磚縫裡澆灌的都是以石灰、糯米汁、紅糖與桐油攙和而成的“夾漿”,此種夾漿凝固後的附著力極強,能使城牆經久不壞,六百年過去依然堅固如初。
尋訪老城南,門東和門西是常碰到的概念。外秦淮河從無到有,皆因為明城牆的修建,它作為人工開鑿出的護城河與交通運河,將舊時相連的長干裡隔斷;而內秦淮河的歷史幾乎永遠比想象中更加豐富,它與中華門相連,在城牆內形成兩個三角形片區,中華門東面的三角區稱為門東,中華門西面的三角區稱為門西,叫法由此傳開。
南京的老城和國內其他幾個兄弟古都命運相仿,自改革開放以後便迎來了“舊貌換新顏”的一波波改造和重建。遺憾的是,人們還來不及認真地評估老城中各個歷史街區、文保單位的無量價值,城市發展的進程已將這些見證過數百年峥嵘歲月的古董匆匆吞沒,取而代之的是參差不齊的水泥盒子、混凝土搭起來的仿古建築,新漆新瓦,全無感覺,徒留噱頭。
2006年,城南顏料坊、牛市、珍珠巷等多處歷史街區、文保單位、古井齊刷刷地被列入“消失名單”,為一座即將動工的購物中心騰地。同年8月,作家薛冰、南京大學教授姚遠等16位知名人士發出《關於保留南京歷史舊城區的緊急呼吁》,得到溫家寶總理的批示,才使拆除工作一度告停,推翻之前的規劃,請參與規劃、整治北京南鑼鼓巷、國子監-雍和宮保護區,福州三坊七巷等地的清華大學建築學院教授張傑重新設計城南歷史街區改造項目。
如今,改造項目正在進行,街巷裡的明清老屋經過修繕,獲得了統一的外立面顏色,甚至是統一的屋檐。鑽進門西的一條老巷子裡,偶然撞見一扇門,戲台臨河而建,只是連同身邊的一串河房被改造一新,唯有一處暗灰色的舊河房夾在其中格外搶眼,馬頭牆清風偉岸,訴盡歷史。
門西是城南最早的居民聚集區,遺留下大量古建民房,六朝以來形成的道路系統尚未破壞,單從路名就可以清楚地判斷房子的朝代。六朝、南唐、宋、明、清,走到哪裡都是故事。如果身邊有一位好導游,街巷裡的城南舊事是一天都講不完的。
推薦閱讀:
天津天後宮維修4天正月十四再開放
建築師爆北京鐘鼓樓旁四合院將被拆
阮儀三:歷史風貌老建築也是一種文化
西藏和平解放後的西藏寺廟維修
城西:人文深味,家住六朝煙水間
到漢中門的時候陽光正好,抬手看了看表,距跟薛冰約定的采訪時間還早一個小時,離約定的地點——莫愁湖邊的咖啡館也並不遠,索性坐在城牆下曬一會太陽。
遵照南京“顯山,露水,現城牆”的規劃原則,每逢一處獨立的城門,都會遇見一處或大或小的城牆公園或市民廣場。身後兩處三棵成幫的銀杏樹颀長豐碩,頂著大團金黃燦燦的樹冠在微風中閃耀著炫目的光澤,身前的桂花樹雖然已過花期,卻依然飄散著暗香,葉片在風中沙沙作響。目之所及的草坪邊緣,一個十三四歲的女孩在父母的陪伴下遛兔子,靜默的城牆下,生活千百年來就這樣慢慢流淌。
薛冰的家住在莫愁湖邊,誠如他那一本《家住六朝煙水間》的立意,當我拋出第一個關於南京貴族氣的問題時,他笑答道,“南京沒有貴族氣,只有煙水氣。”
這煙水氣,恐怕還要從城西清涼山的文脈說起。
吳敬梓說南京“菜傭酒保都有煙水氣”並不為過,在那個精神生活可以擊節稱賞的的時代,清涼山就是精英文化的源頭。南朝宋武帝在清涼山建離宮;五代時楊吳在此建興教寺;南唐後主李煜在此建避暑宮……清涼山素為歷代帝王、文人墨客垂青之所,烏龍潭更是歷代歷史文化名人的精神家園。住在清涼山上的魏源講烏龍潭,“林陰橫滿地,夜影忽過牆。忘卻月已轉,翻移樹易長。積雨有余氣,老荷始自香。空林如積水,清夜意難忘。”如今的烏龍潭公園雖已很小,再看不到黑龍出沒,卻因為眾多遺墨而成為歷代文人永久的憑吊所在。
薛冰說,石頭城本是軍事區,當時的石頭城是騎在長江上的,就像現在的采石矶和燕子矶,占據著重要的軍事要塞位置。到了六朝以後,特別是南唐,長江逐漸西移,石頭城的軍事地位慢慢退化。在此之後,很多詩人紛紛到這裡來懷古,留下詩文,石頭城才慢慢變成文化人的主要活動場所,順而成為南京的一個文化區。
“隨園是袁枚建的,袁枚在當時的地位很高,相當於巴金、茅盾這樣的文學泰斗,他在這兒,全國的文化人都要到這兒。袁枚很重視生態保護,隨著自然的地勢修建這個園子。這個園子是沒有圍牆的,誰都可以進來玩,誰都可以到園子裡采果子,誰都可以在牆上寫詩。到了乾隆以後,道光年間,寫《海國圖志》的魏源就住在清涼山下的龍蟠裡,寫《校廬抗議》的馮桂芬當時在惜陰書院當老師,就是現在的江南圖書館,在魏源家的對門。這個江南圖書館是當時的兩江總督征得朝廷同意官方修建的,花了幾十萬兩銀子買書,包括很多大藏書家的書,這些書到現在還是南京圖書館古籍部的底子。後來南京大學在這裡,金陵中學在這裡,南京師范大學還要近,河海大學更近,直到變成一個大學區,成為今日精英文化的聚集地。”
從清涼山回到近在眼前的莫愁湖,薛老講的掌故脈絡清楚,妙趣橫生:“莫愁湖一開始是借了六朝南齊莫愁女的名,在梁武帝的《河中水之歌》中就有這個美麗的傳說。之後關於莫愁女的景點越修越多,也增添了更多引人入勝的傳說。很多人來看、來玩,再寫出很多東西,這個文化積累越來越厚,就有了今天這個詩意盎然的莫愁湖。”想來莫愁湖的一瓢水裡都應該蕩漾著詩文,而那些亦真亦幻的傳說故事才是莫愁湖的靈魂。
推薦閱讀:
天津天後宮維修4天正月十四再開放
建築師爆北京鐘鼓樓旁四合院將被拆
阮儀三:歷史風貌老建築也是一種文化
西藏和平解放後的西藏寺廟維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