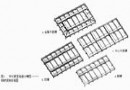徽州園林藝術簡論
日期:2016/12/14 22:54:21 編輯:古建築結構《中國大百科全書》對園林作了如下界說:“在一定的地域運用技術和藝術手段,通過改造地形(或進一步築山、疊石、理水)、種植樹木花草、營造建築和布置園路等途徑創作而成的美的自然環境和游憩境域。”按照園林的隸屬關系分類,中國古典園林可歸納·為三個主要類型:皇家園林、寺觀園林、私家園林。在古代徽州,寺觀園林和私家園林分布范圍廣,持續時間長,形成了自己的地方風格,是徽州園林的主體。如果用發展眼光看,徽州傳統的風景名勝區,如黃山、齊雲山,以及歙縣西干等,既有自然之美,又具人文之勝,與古典園林關系十分密切。另外,徽州傳統村落,散布在新安大好山水之間,村民對村落水口刻意規劃,精心營建,使之成為一座座開敞的園林化空間,發揮著重要的環境效益和社會效益,是古代的公共綠地。隨著園林學科的發展,兩者亦應包括在內,其內容另有專文介紹,不在本文討論范圍。
寺觀園林,即佛寺和道觀附屬的園林,包括寺觀內外的園林化環境。“徽俗不尚佛、老之教,……所居不過施湯茗之寮,奉香火之廟。求其崇宏壯麗所謂浮屠老子之宮,絕無有焉”(許承堯《歙事閒譚》)。徽州是程朱理學的故鄉,宗教發揮的作用受到限制,所以宗教建築與世俗建築沒有太大差異,梵剎紫府實際就是住宅的擴大和宮殿的縮小,寺觀園林亦與私家園林幾無區別。寺觀大多建在風景優美地帶,濃綠參天,花木掩映,亭榭雍容,池台明麗,寺、觀建築與幽雅的園林及寺觀外圍的自然風景相結合,成為人們游憩佳處。清同治《祁門縣志》記載南宋紹興元年(1131)岳飛率軍過祁門縣,憩東松庵,題記壁上:“三山環聳,勢凌碧落,萬木森郁,密掩煙甍,勝景潇灑,實為可愛。”岳飛於軍旅倥偬中為後世留下了文情並茂的游記,使我們從中領略到徽州寺觀園林的魅力。
明弘治《徽州府志》載:“本府有寺觀,則始於晉,歷唐及宋元而益熾洪。”徽州最早見於史籍的寺觀,佛寺為建於東晉太興二年(319)的休寧縣萬安南山庵,道觀為建於唐乾封一年(666)的歙縣乾明觀。明至清中葉,建築日漸增多,徽州名勝之地均有寺廟。據清道光《徽州府志》記載,當時徽州府屬6縣有寺院庵堂435處。道教建築也陸續興建,明清之際,僅當時已成為江南道教中心的齊雲山就有宮觀47處,道房36處。、道教的流行,使寺觀園林也開始興盛。因此,徽州寺觀園林的出現似乎可以上溯到東晉。唐以降,比較著名的寺觀園林有太平興國寺、星巖寺、玄天太素宮、慈光寺等。

太平興國寺,唐名興唐寺,俗稱水西寺,位於府城外西干,唐至德二年(757)建。唐貞元末(804),張友正撰《歙州披雲亭記》描寫興唐寺:“回廊翼旋,飛閣雲褰,萬家井邑在我宇下,實一方之勝概也。”唐代詩人張喬亦有詩:“山橋通絕境,到此憶天台。竹裡通幽徑,雲邊上古台。鳥歸殘照出,鐘斷細泉來。為愛澄溪月,因成隔宿迥”寺已不存,唯長慶院塔尚在。
星巖寺,舊名周流寺,俗稱小南海,位於歙縣岑山,五代吳天佑八年(911)始建。岑山兀立漸江之中,“郁然孤峰,溪水環之”(弘治《徽州府志》)。清康熙年間,岑山渡人程且碩返裡,記其勝雲:“松桧插天,四時青翠”,“有師山讀書樓及鄭公釣台……文昌閣”,“殿右小閣日昙汛,境最幽邃”(《歙事閒譚》)。星巖寺園林風景絕佳,名播遐迩,明代王善慶《過周流寺》詩:“雲埋殿閣周流寺,春水沖撞復到山。僧衲掛枝庭樹老,禅床措石洞雲閒……”十年浩劫中毀於愚昧,歙人言及薏歡笸蟆
玄天太素宮,位於休寧縣齊雲山,宋寶慶二年(1226)始建,後代屢有修葺。1966年後毀壞殆盡,90年代恢復正殿。太素宮建築群共三進,山門外為“玄天金阙”坊,六柱五樓門樓式。過山門經渡仙橋,跨虛危池,穿二進殿門,即至正殿。殿前兩側有廊庑、鐘鼓樓,神道左右各植柳樹,楊樹。太素宮選址絕妙,背倚齊雲巖,左峰石鼓,右峰石鐘,夾屏兩峰為辇辂,宮前香爐峰“挺然拔出莽蒼中,不與群山相屬”(明·程敏政《游齊雲山記》),峰巅明初鑄建鐵亭。雄麗的道觀建築座落在群峰環峙之中,“香爐捧出仙人掌,辇辂行來織女橋”(宋,程從元《雲巖》),園林化的環境真是氣象萬千,目不暇接。難怪90年代初出版的《中國古典園林史》將太素宮作為寺觀園林10例之一予以介紹。
慈光寺,位於黃山朱砂峰下,舊名朱砂庵,始創於明隆慶間(1567-1572),萬歷三十年(1611),神宗賜額“護國慈光寺”。現有建築為80年代後建。寺周群峰盤結,古木環抱,“日光篩落,如行荇藻中”。而“磬韻香煙,穿石而出”,“地忽平曠,有佛捨巍然”(清·劉大櫆《黃山記》、明·徐霞客《游黃山日記》)。慈光寺殿宇莊嚴,殿前有池,中界石橋。藏經樓附近有木本蓮花,樹大如拱,芳氣襲人。《寄園寄所寄》的作者趙吉士有一首七律,描寫了慈光寺內外景致:“客到山門噪白鴉,佛光四面現昙華。鐘魚隱隱傳天梵,台閣層層簇石霞。百啭時聞山樂鳥,一株獨放木蓮花。長空碧落流丹液,如向雲中泛月槎。”明代造園家計成認為“園地惟山林最勝”,“千巒環翠,萬壑流青”(《園冶》),隱於此間的“松寮”(即僧捨),印證了一句古話:天下名山僧占多。
私家園林,徽州大多稱之為園、園亭,它屬於官僚、地主、官商,以及文人所私有,實際是第宅的擴大與延伸,是園主人日常游憩、宴樂、會友、讀書的場所。徽州私家園林多數為宅園,依附於第宅,也有少數單獨營造。另外還有數量不多的書院園林,其內容與私家園林相類。
中國私家園林最早見於漢代,以後各代都有發展,至宋代,造園風氣更盛。明、清兩代分別在中葉形成造園高潮,私家園林達到了高度的技術和藝術水平。清末隨著封建社會的解體,中國園林結束了它的古典時期,進入現代園林發展階段。
徽州私家園林最早可能出現在宋代,當時徽州商業資本日益活躍,特別是南宋建都臨安,對徽州商業的發展起了很大促進作用。同時,為應科舉及傳播朱子理學之需,教育發展也很迅速,文風昌盛,儒學蔚興,科舉及第者眾多。經濟文化的較快發展,為園林的興盛提供了必要條件。加上宋高宗在臨安大興土木,建造宮殿花園,僅御花園就達40多處,其他貴族大臣競相效仿,流風所及,徽州不能不受其影響。北宋見於史籍記載的徽州私家園林主要有:崇寧年間(1102-1106),休寧縣汪若楫於藏溪建秀山書院,這是徽州創立最早的書院,汪氏有“秀山十景詩”。政和年間(1111—1117),績溪縣許潤於沈山建樂山書院,構天月亭、南樓數楹,可望覽。南宋徽州私家園林較多,著名的有:休寧縣商山吳儆建竹洲吳氏園亭。紹興二十九年(1159)以前所建的黟縣碧山汪勃別業培筠園,內有“白鶴館”諸景,詩人張九成(1092-1159)詩碑今尚存。休寧縣尚有朱權建首村朱氏園亭,有芳洲景星樓、濯纓亭、拂雲亭等居休游樂之所;趙戴建龍源趙氏園亭,有雲屋、省心亭、翠侍亭、問道亭、有有堂,多名士題詠;吳欽建璜原吳氏園亭,有延桂樓、臨清橋、花圃、觀化亭,吳氏自宋亡即營此自娛不仕。歙縣風雩亭,紹熙二年(1191)舒磷辟學捨後圃,依山城而建,為士子藏修游息地。
元代民族壓迫與階級壓迫特別殘酷,社會經濟受到嚴重破壞,徽州私家園林發展也處於滯緩狀態。弘治《徽州府志》僅載數處:婺源縣慶源圓鏡山房,詹復心隱居之所,有八景,其婿詩雲:“鏡峰園林尚如昔,苔源石徑迷行跡”。休寧縣朱伯初建月潭朱氏園亭,有石門、臨清閣、觀瀾亭、釣雪舟、平林小隱、桔隱堂。休寧縣尚有嶺南黃一清所建秋江釣月樓,會裡程天經所建醉經堂。
明、清時期徽商興盛,稱雄商界數百年。徽商賈而好儒,“雖為賈者,鹹近士風”(《戴震集》),文化素質普遍較高。民國《歙縣志》謂“商人致富後即回家修祠堂,建園第,重樓宏麗”,“所居廣園林,侈台榭”(《歙事閒譚》),形成了徽州造園的高潮。歙縣豐南山水平遠,風景秀麗。吳氏家族世代業鹽,在故裡築室卜鄰,“園亭樹石,錯落分布於其間”,園墅麇集,頗為繁盛。歙縣《豐南志》載有園林41處,明代豐南十大名園,大抵在其中。另外,明、清時期“揚州以園亭勝”,而“揚州之盛,實徽商開之”(陳去病《五石脂》)。徽商世代僑寓揚州,園林多為徽州人所建,據李元庚《山陽河下園亭記》載淮安河下的園亭有65處,其中徽商程氏所建即占三分之一。明末江南名園中的影園、休園、嘉樹園、五畝之園,園主皆為歙籍鄭氏四兄弟。清康熙年間揚州八大名園亦近半數為歙籍人所建。揚州園林之盛,徽商“與有力焉”。反之,徽州和各地的園林藝術交流,又促進了徽州私家園林的發展。明、清時期徽州私家園林很多,僅民國《歙縣志》所載當時歙縣就有20余處,更多的園林已湮沒無考。茲例舉數處,以見大概。歙縣豐南曲水園、果園、十二樓、清晖館。十二樓為明代吳養春別業,園內石假山仿倪雲林疊獅子林式;清晖館為明代吳肇南別業,吳氏自為記。歙縣尚有潛口水香園,唐模檀干園,雄村竹山書院、非園,西溪不疏園。非園為清代乾隆年間曹文埴建,有欲榜齋、排青榭、曠如亭、水香台等十二景,清代詩人袁枚有詩雲:“牆外風帆入座飛,林中怪石迎人揖。層層水木湛清華,對景懷人意倍加……”。不疏園為清代乾隆初汪泰安經營創建,有勤思樓、黃山一角、六宜亭、山響泉、不浪舟等十二景,園內有豐富的藏書。許承堯《歙事閒譚》提及明代的名園還有歙縣遂園,休寧縣荊園、季園、七盤園,“人清後則名園寢多矣”。
徽州傳統住宅不少富有園林情趣,天井、庭院處理頗見匠心,不妨將其視為宅園。如黟縣西遞西園,桃李園、枕石小築,宏村德義堂、承志堂,以及歙縣徽城王宅等。
從以上史料中可以發現,徽州私家園林的發展歷史大致與中國私家園林的發展同步,它表現出江南園林的共同特點,又具有地方特色,以下就竹洲吳氏園亭、溪南曲水園、雄村竹山書院、西遞西園加以分析。
竹洲吳氏園亭,位於休寧縣商山村,南宋淳熙五年(1178)前後吳儆建。吳氏舊居之前有竹洲,“因其地勢窪而壩者為四小沼”,“又乘地之高,附竹之陰,為二小亭”,其一面溪山。亭南為堂,堂北為仁壽齋、靜觀齋。有堤“高出氛埃,旁臨曠野,溪流其下”,“據堤為二亭”。園內藝菊植荷,種四時果蔬,杉為“直節蒼梅乃“梅隱庵”。吳氏自為記雲:“柳子厚謂‘凡游觀之美,奧如也,豁如也。’是洲蕞爾之地,而高下曲折,幽曠隱見,殆具體而微者。”此園不以築山取勝,而以水景、花木見長,體現了宋代園林簡遠、疏朗、雅致、天然的風格特點,簡約是宋代藝術的普遍風尚,吳氏園亭受其影響,景物以少勝多,整體性強,不流於瑣碎。園內建築密度低,且多單體,無游廊連接,不以建築圍合或劃分景域,植物配置亦以叢植為主,虛實相襯,於幽奧中見平曠。由於造園諸要素刪繁就簡,從疏布局,益見開朗。吳氏園亭景題多取義詩文,寓情於景,直抒胸臆。如以杜甫詩句命名的“靜香”亭,袁明道詩句命名的“靜觀”齋,以及寓意操守的“直節”、“梅隱”等。景題的“詩化”,拓深了園林意境,點出了象外之音。該園尚“有竹千余”,並大量種植菊荷蘭蕙,作為園林雅致格調的象征。吳氏園亭因山就水,利用原始地貌,稍事改造,即臻其妙。園內並設果園菜圃,既表現了園林的天然野趣,也增加了濃郁的生活氣息。
曲水園,位於歙縣豐南村,明中葉吳玙建。明代詩人、劇作家歙人汪道昆(1526—1593)有《曲水園記》,描摹如畫。全園以水榭為中心(榭即日“中分”),環池再錯雜使用走廊、林木、假山等手法,分隔成三個景區:“池南則‘萬始’(亭)盡‘御風’(台),池北則自步榈(即走廊)盡‘藏書’(樓),東自‘高陽’(館)盡‘止止’(室),三分鼎立”,又聯為一個整體。曲水園以水景見長,園“修廣不啻十畝”,“其中鑿池,坼南北為天塹”,引圳水,經澗人池,“句如規,折如磬”,曲折有致。水面處理,有聚有分,澗上跨橋,池中築堤、並布置矶、嶼,與橋、堤一起分隔水面,使水面等空間相互滲透,似斷而續,曲折深邃。明代園林的特點是疊石盛行,徽州私家園林亦莫能外。曲水園山景主要有四處:萬始亭北,“累白石”為群玉山;洞房北“當戶一卷石”,特置孤峰;三秀亭南“累黝石為小山”;高陽館南“聚美石為山,震澤產也”,即以江蘇太湖石掇山。這座湖石假山臨水而構,山水相互襯托,疏茂相屬,高下相錯,峰巒回抱,洞壑幽深。曲水園建築與山、池、花木相互協調,有機聯系,共同組成園景。屋宇類型有堂、館、樓、閣、亭、台、榭、廊等,其中廊還有閣道,即復廊。這些建築環池布置,互為對景,形成完整的構圖。曲水園花木配置也頗具特色,百品千章,林木翳然,這從園記中多次使用“穿薄”一詞,可知園景蒼古深郁。明代園林承傳兩宋而繼續發展,由於文人參加造園實踐,私家園林更多地追求雅逸和書卷氣,以抗衡園林的“市井氣”和“富貴氣”。徽州私家園林雖多為富商巨賈所建,但徽商亦儒亦賈,文化素質較高,有些還延聘著名文人為之籌劃經營,所以園林風格雅而不俗,並影響到寺觀園林。如和曲水園同時、同地而建的果園,“花木敷纡,泉石幽邃”,相傳為唐寅、祝枝山所規劃,事見乾隆二十六年(1761),程讀山《雨窗絕句》。園林風格的這種微妙變化,汪道昆已敏銳察覺,他在園記中指出:“若王公貴人,游閒處士,諸所建置備游觀者,大較可得而言,已庳則苦而儉於文,已美則甘而傷於雅,鴻胪君(吳玙)乃得中制,不有足術者乎。”正由於吳氏“得中制”,曲水園雖“佳麗甲於吾土”(明·吳肇南《清晖館記》),卻庳而文、美而雅,達到了很高的藝術水平。
竹山書院,位於歙縣雄村,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曹干屏、曹喚青兄弟所建,清代詩人沈歸愚撰有《竹山書院記》。書院建於雄村水口桃花壩上,東臨漸江,遙對竹山。書院南為講堂,北為園林,園東隅增辟一門。由東門人園,至眺帆軒,軒濱江。園三面由建築圍合,形成主景庭院。西為清曠軒、百花頭上樓,軒、樓之間隔以小天井,以廊連接。軒前有露台,置石雕低欄。軒南為“千竿滴翠”,循廊南行,則為牡丹圃,姚黃魏紫,極盡妍麗。圃一隅掇石山,旁逸古梅;另一隅植山茶,楚楚動人。這一組建築延纡園的西、南面,曲檻迥廊,敞軒小閣,虛實相間,錯落有致,構圖生動活潑,極富變化。園北聳峙凌雲閣,上祀文昌,書院園林主題隱喻其中。園東作開敞式處理,面山臨江,僅以矮牆分隔內外。數峰掃黛,一水揉藍,绛雲繞園,風帆入座,極盡借景之能事,相傳是清代詩人袁枚的設計構思。清曠軒露台下有池曰“秋葉”,池畔植杏,池水蜿蜒流經凌雲閣前石橋。園內平崗疊石,淺溪駕梁,金粟飄香,風铎悠揚,與園外景致渾然一體。從乾隆到清末,私人造園活動遍及全國,從而出現各種不同的地方風格。竹山書院是清中葉江南園林中較有代表性的地方園林,故《中國古典園林史》將其作為清中葉至清末江南園林的十三個實例之一加以介紹。其園林藝術主要特點是;構圖的天成之趣,意境的象外之旨,技法的簡遠之致。竹山書院選址極佳,所謂“相地合宜,構園得體。”(《園冶》)徽州村落水口是村落形態中園林情調表露最集中、最突出的地方,雄村水口“緣溪之曲,築平堤,藝佳樹,蒼翠無際、隱隱為畫圖”,並建有“崇功報德祠”、“武帝行宮”、“雄村上社”,以及方勝亭等建築,竹山上的慈光庵也隔江在望。書院建在水口,則使一座僅二畝余的園林獲得無限深遠的觀賞效果。盡管園內建築物較多,凌雲閣體量又大,但由於選址巧妙,書院成為雄村水口的園中園,故並不感到建築密集,體量厚重,園林空間的經營達到了很高境界。竹山書院對借景技巧的運用已臻極致,《園冶》雲:“夫借景,林園之最要者也。”書院虛其臨江之面,以“延山引水”手法,將新安大好山水景致攝取人園,作為主要觀賞對象;而園林本身的山池僅稍事點綴,與優美的自然環境融成一體,“自成天然之趣,不煩人事之工”。清光緒年間歙縣知縣譚復堂記竹山書院:“缭以短垣,面新安江,峰壑如屏。帆纜上下,擅勝在遠,山澤之姿,可以坐嘯”(《歙事閒譚》),深谙此園之妙。江南園林重意境蘊涵,不僅借助造園要素來傳遞意境信息,還采用詞賦、匾額、刻石、楹聯等文學藝術方式深化意境內涵。竹山書院以多種手法表現意境,將書院園林的主題發揮得淋漓盡致。栽杏象征杏壇講學,植桂以寓蟾宮折桂,壁間刻賦,廊內嵌碑,文思優美,書法精妙,與園林情景相互交融。竹山書院園林藝術由於受明末清初形成的“新安畫派”影響,保持了宋、明以來園林軒爽清秀的風貌。園內建築采用徽州民居傳統形式和處理手法,飾以高古的磚、木、石三雕,質樸自然,雅健明快,頗類境界開闊、寓偉峻沉厚於清簡淡遠之中的“新安四家”的作品。如清曠軒與百花頭上樓之間的小天井,面積不過四、五平方米,疊壁山卻甚峭偉。所謂以壁為紙,以石為繪,“收之圓窗,宛然境游也。”竹山書院是碩果僅存的清代徽州私家園林,其價值自是不言而喻。
西園,位於黟縣西遞村,清道光年間(1821—1850)胡文照建。西園為徽州四水歸堂式住宅,三單元並列,每單元前有庭院,以花牆分隔,辟地穴相聯系。庭院僅130平方米,進深不足5米,但就在這樣一個很小空間裡,通過花牆、漏窗、地穴等手法的運用,成功地擴大了景域空間,豐富了層次。西園庭院中點綴花木、盆景、魚缸、石幾,洋溢著雅致的園林情調。“井花深處”小院內的水井,更為庭院平添了濃郁的生活情趣。西園的漏窗、匾額制作十分考究,尤其是“松石”、“竹梅”兩石雕漏窗,構圖生動,雕工精湛,增加了園林婉約多姿的藝術效果。西園不僅僅將住宅冠以“園”名來傳達意境信息,並運用景題,將文學藝術與造園藝術完美結合起來,虛實映襯,妙趣橫生,意境蘊藉,回味無窮。“種春圃”、“井花香處”、“雲林送思”等匾額文字表達和深化了園林意境內涵,獲得象外之旨。清中葉以後,邸宅在一定程度上園林化,居住建築和園林更密切結合,使“咫尺山林”的園林審美意識進一步升華,西園正是這一時期的佳構。
徽州園林目前保存下來的數量十分有限,且都屬清中葉以後遺構。它們固然不能充分反映徽州古代園林的卓越成就和高度藝術水平,但仍能總結出許多成功經驗和優秀手法。徽州園林和我國其它各地園林相士匕較,有著很多相同的共性,這種共性即《中國古典園林史》所概括的中國古典園林四個特點:一、本於自然、高於自然。這是中國古典園林創作的主旨,這個特點在人工山水園的掇山、理水和植物配置方面表現得尤為突出。二、建築美與自然美的融糅。建築無論多寡,也無論性質、功能如何,都能夠與山、水、花木三個造園要素有機地組織在之中,彼此諧調,互相補充,達到人工與自然高度和諧的境界。三、詩畫的情趣。中國古典園林是時、空綜合藝術,它運用各個藝術門類之間的觸類旁通,融鑄詩畫藝術於園林藝術,使園林包含著濃郁的詩情畫意。四、意境的涵蘊。中國古典園林將文學藝術、書法藝術與園林藝術直接結合起來,寓情於景,見景生情,達到高度情景交融的境界。共性之外,徽州園林還具有不同的個性,作為主要地方園林之一,它有著獨特、鮮明的地方風格。
充分發揮新安大好山水的優越條件,因地制宜,巧於因借,將天然風景裁剪人園,富有徽州山區特色,這是徽州古代園林的一個主要特點,其風格似與天然山水園相近。中國古典園林如果按照園林基址的選擇和開發的不同方式,可分為人工山水園和天然山水園兩大類型。前者以城鎮居多,基址平坦,以豐富多采的造園手法,創造摹擬天然野趣,所謂“城市山林”,“雖由人作,宛白天開”。後者建在城郊或村野,基址選天然山水片段,因勢利導地改造地形、地貌,適當配置造園諸要素,“自成天然之趣,不煩人事之工”。徽州的基本屬地,在我國皖南丘陵地帶,明末詩人錢謙益游黃山時曾記入山途中風物,許承堯以為“摹寫最真,可為吾鄉總贊。”錢氏之記雲:“其地勢坡陀荦確,擁崖據壁,溪流萦折,漘岸相錯。……溪水清激如矢,或噴沸如輪。文石錯落,深淺見底。百裡之內,天容沆寥,雲物鮮華”,而徽州的“士夫巨室,多處於鄉”,因此,徽州園林大多建在鄉村,或村郊水口,或山麓田間。徽州各村,“村村入畫”(明·吳士奇《豐南溪山記》),如珍珠般散落其間的徽州園林,將水容山態,村霭墟霏,盡收園內。下面再試舉數例。
《歙事閒譚》轉錄清代胡心泉《水香園記》大意雲:“吾縣西山水平遠,居人復工選勝,園亭樹石,錯落分布於其間,與川巖相映發”。
清代吳定《娑羅園燕集序》,記明代所建的娑羅園雲:“園之木既古,而地尤曠,北臨豐樂之溪,水鳴锵锵,石露拳拳。遙望黃山天都、雲門諸峰,如堂如防,游者多愛之。”
清代王灼《游歙西徐氏園記》:“園之外,田塍相錯,煙墟遠樹,歷歷如畫。而環歙百余裡中,天都、雲門、靈金、黃羅諸峰,浮青散紫,皆在幾席。蓋池亭之勝,東西數州之地,未有若斯園者。”
明代汪承《玩芳亭記》:“築別墅於富資之陽,構祠宇數楹,後倚崗阜之隆,前挹溪山之秀。”辟蔬圃,鑿方池,建亭臨眺,“環植群木,列莳眾卉。周圍數裡缭以垣牆,俨然一林苑也。”
明代吳·肇南《清晖館記》:“阻巨浸而遙對眾山……右天竺,左天馬,或危巖蒼郁,或萦青缭白,皆隱隱雲間。前山則崗聯隴屬,……橫亘如帶,中多良田,溝渠绮分。主人憑虛而眺,則五谷垂穎,田家之至樂也。”
清《巖鎮志草》記“萊園”建亭台上,“名曰‘問稼’。一望西疇,波平繡錯,秧針濯雨,麥浪乘風;倚檻課耕,可與農人勸相。”
“樓台荒廢難留客,林木飄零不禁樵”,這是清代阮元在嘉道年間描寫揚州園林的衰敗景象。清道光年間,徽商開始衰落,徽州園林也同樣呈現衰頹跡象,遺存至今的已屬鳳毛麟角。但就在現存有限的珍貴歷史遺產中,我們仍能體會到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涵蘊。徽州古代園林已為當今園林建設所借鑒,尤其是徽州園林化的村落水口規劃理論與營建,更是新園林體系可批判繼承的財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徽州古典園林曾走出國門,成為中、德兩國的文化使節,今後徽州古典園林也必將對中國,乃至世界園林文化的發展作出新的貢獻。
- 上一頁:中國古建築知識 - [歷史建築]
- 下一頁:古代建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