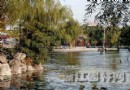新安漢函谷關遺址
日期:2016/12/14 12:40:42 編輯:古代建築有哪些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裡長征人未還”,每當吟誦唐朝詩人王昌齡的這首《出塞》時,不由讓人產生一睹漢時關雄風的渴望。歷史車輪滾滾,帶走了多少功名與塵土,曾經的雄關,今又何在?撥開2000多年歷史的塵埃,我們回首望去,唯有位於河南洛陽新安縣境內的漢函谷關至今仍可見一絲風采,雖已殘破凋敝,卻以“全國唯一留有關樓遺址的漢代關隘”屹立猶存。
古絲綢之路第一道門戶
對於函谷關,很多人並不陌生。相傳老子騎青牛出關,在此留下《道德經》。歷史上所謂關東關西,就是以函谷關為界。河南靈寶有一座函谷關,俗稱秦函谷關;河南洛陽新安縣境內也有一座函谷關,俗稱漢關,也稱漢函谷關,據說是漢武帝時期靈寶函谷關整體搬遷而來。函谷關東移這件事,在《漢書·武帝紀》中有記載:西漢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冬,“徙函谷關於新安”。東漢人應劭對此進行了注解:“時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恥為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以家產給用度。武帝意亦好廣闊,於是徙於新安,去弘農三百裡。”原來,漢函谷關是樓船將軍楊僕移來的。楊僕是西漢名將,老家在宜陽南灣村,今屬新安縣鐵門鎮。當時國都在陝西,函谷關或潼關以西被稱為關中或關內,以東則被稱為關東或關外。楊僕只因是“關外民”,戰功雖顯赫,卻不能獲得關中的封地,於是他提出自己出資東移函谷關,獲批。楊僕初建的漢函谷關是什麼樣子呢?南北朝時的郦道元在《水經注》中有描述:關樓高聳,兩側雞鳴、望氣二台相對而立,左右關塞橫亘,南貫洛水,連接宜陽,北越丘陵,直抵黃河,宛若綿延百裡的長城,十分壯觀。自此,漢函谷關作為各朝各代重要的軍事要塞,占據著重要的地位。漢武帝初(公元前138年),張骞出使西域,絲綢之路正式開通。洛陽成為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漢函谷關成為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和歷史見證。東漢中平元年(公元184年),朝廷曾置八關都尉,漢函谷關居首。南北朝時,北周武帝保定五年十月,朝廷改漢函谷關為通洛防,大將賀若敦以中州刺史鎮守關防。隋炀帝時期,曾在此營造顯仁宮。唐顯慶五年,朝廷曾在漢關附近建合璧宮……由此可見,漢函谷關一直都是有史可載的關城,因地勢險要,易守難攻,大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歷來為東都洛陽的門戶,控東西兩京的要道,抵御異族入侵的屏障。
隨著歷史的變遷,關塞逐漸退出歷史舞台,變成了歷史的見證。“暗淡了刀光劍影,遠去了鼓角爭鳴”,漢函谷關作為軍事要塞的作用逐漸淡去,也漸漸淡出人們的視線。宋以後的800多年間,漢函谷關或毀於天災,或毀於戰亂,風雨剝蝕,屢遭破壞。今存漢函谷關遺址為1923年張钫重修後保留,殘高15米,底部關壇高9米,南北長25米,東西寬20米,壇上有兩層樓閣,一層為四面相同拱式門洞,且四面門洞均有楹聯,可惜已殘破不可尋。
漢函谷關不僅發揮著軍事要塞的作用,是東西方交通的重要驿站,也是一座重要的東西方貿易之城。東漢蘭台令史李尤在《函谷關賦》中說的“上羅三關,下列九門。會萬國之玉帛,徕百蠻之貢琛”,就是對此的生動描述。上世紀80年代初,漢函谷關附近出土了幾十件文物,其中有獨具西域特色的牽駝俑、胡俑、駱駝俑等,證明當時的漢函谷關是古絲綢之路上一個重要的關隘,東西方使者和客商絡繹不絕,來往十分頻繁。
為保護這座古代關隘,2007年10月,新安縣漢函谷關遺址被列入絲綢之路申遺捆綁項目預備名單,2012年又被列為“絲綢之路”項目的遺產點,2013年5月,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不僅是關隘,也是一座城
雖然史籍詩作中對漢函谷關不吝辭藻,現存遺址也可粗略想像其當年的恢宏氣勢,但漢函谷關的規模到底有多大?形制到底如何?一直以來並沒有明確的答案。為配合漢函谷關保護規劃的編制和“絲路”申遺工作順利實施,2012年,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開始對遺址進行考古調查和發掘。經過一年多的工作,勘探鑽探總面積約13.9萬平方米,發掘遺址面積3300平方米,發掘城牆遺跡5處,夯土台2處,古道路2條,建築遺址2處,並對鳳凰山和青龍山上的夯土長牆進行了勘探。


馬道及排水渠

石砌護堤
“這是一次主動性的考古挖掘,因為漢函谷關古代號稱‘洛陽第一關’。只有搞清楚漢函谷關的總體情況,才能進行下一步的保護和申遺工作。”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漢魏研究室主任嚴輝說,這一次考古發掘最大的收獲就是搞清了漢函谷關的整體布局:它是一處內、外城結構的小型城邑。內城平面為長方形,東西長約160米,南北寬約110米;外城東牆與南北兩側山上的長牆相連接,關城卡在峽谷之中,關城東牆與南北山上的夯土長牆相連接,完全控制了峽谷的東西交通,達到軍事防御和控制交通的目的;關城中部的古道路東西向貫穿關城,是唯一的通關道路;遺址南部、皂澗河北岸是主要的生活區。
嚴輝認為,以往對漢函谷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史籍文獻的考辨,“這次發掘證明了文獻中的那些記載很多是符合史實的。”比如函谷關的雞鳴、望氣二台,以往只是文獻、地方史志記載,或者當地百姓口口相傳,“根據出土遺物和對遺跡的解剖,可以確定雞鳴、望氣二台及台基西側夯土牆和關城東牆,都是西漢建關時修建,關城南牆為漢代增建。”嚴輝說。
以往的考古工作對關隘的研究非常匮乏,並且集中在邊關,對地位如此重要的內陸關隘系統地考古發掘更是第一次。嚴輝說,此次考古發現,為秦漢關隘制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料,也為漢函谷關遺址的保護提供了重要依據。
關城內的生活足跡
此次考古發掘的重大突破還在於:在漢函谷關關城內發現了房屋基址、排水渠以及數十枚函谷關遺址的代表性遺物——“關”字瓦當等。其中,關城房屋基址位於遺址區西南側,成組排列;房址南側,靠近皂澗河的地方發現有石頭壘砌的排水渠,房址北側有水井。在關城東牆上,文物工作者發現用石頭壘砌的南北向的水渠,從城牆穿過。根據出土遺物初步判斷,應該是唐代遺跡。
此次考古發掘還出土了大量陶器、瓷器、骨器、石器、鐵器、銅器及銅錢等各種物品。這些物品中,以陶制建築材料為主,包括瓦當、筒瓦、板瓦、空心磚、方磚、條磚及建築構件,其中板瓦最多,筒瓦次之。瓦當包括雲紋瓦當、“關”字瓦當、“安世”瓦當和“安世萬歲”瓦當,其中“安世萬歲”瓦當是第一次出土。此外,出土錢幣總計108枚,有107枚銅錢及1枚“道光通寶”鐵錢,包含漢、唐、宋、清四個時期的錢幣。還發現了銅镞、鐵戟等兵器。
“眾所周知,漢函谷關是漢代的,漢代之後它有一個演變過程,三國時期、南北朝時期、大一統王朝時期和軍閥割據時期,這個關的功用是不一樣的,它的演變究竟是怎麼樣的,希望下一步的考古發掘能解開這些謎團。”嚴輝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