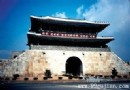藥王廟位於涿州市南關大街,始建於明嘉慶年間,清道光二十五年、民國二十八年重修。1949年後廟廢。1978年原涿縣政府將此地賣與中鐵十八局,廟內建築始遭破壞,僅存一座後殿“大放光明”殿。1983年,此地復歸屬地方,現為涿州市文物保管所駐地。
藥王廟主體建築大放光明殿為高台式建築,台高3.35米,寬37.8米,進深27.5米。台上建五開間殿宇,磚木結構,硬山單檐布瓦頂。裝修走馬板上彩繪故事,其內容有“雲龍”、“乾隆出巡”、“請佛遇仙”、“擇地建廟”“古城街景”、“羅漢”等圖案。涿州藥王廟現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殿台之左有殘斷的清道光25年重修藥王廟碑。此碑為清末書法家何紹基篆額並書丹。因何紹基書法流傳於世的多為晚年的篆隸或行草,這篇楷書成為不可多得的藝術珍品。
藥王廟歷史上建築規模宏大,後又將東側保慶寺改建為清行宮,成為接待迎送之所。據“重修藥王廟記”碑載,“顧涿州為祗谒陵寢常所經臨,四方來京師道路,畢合於廟之西南,遠近瞻仰,攸系茲廟固密迩。”清行宮占地近50畝,總體布局為左、中、右三路。中路為行宮主體建築,沿中軸線由南向北依次排列為宮門、二門、假山、正殿、亭、游廊、丘山、花園等建築。左路為太後宮,右路為皇後宮,兩路又各有殿、閣、軒、樓等建築,其中正殿(正大光明殿)匾額、楹聯皆為御書。院內假山疊景,古柏參天,樓榭重重,清雅幽深。
建國後,電影《古剎鐘聲》曾在此拍攝外景。行宮大部分建築在1978年拆毀,僅存正殿、假山。由於北京市良鄉黃新莊行宮已毀,涿州清行宮已成為京南第一處存有主體建築的皇帝行宮。據此,可以證實藥王廟的歷史影響、歷史作用和它特有的歷史價值。
名稱:藥王廟-大放光明殿
地點:保定市 涿州市
年代:明嘉慶年間-清道光二十五年-民國二十八
級別:河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類別:古建築
推薦指數:★★☆☆☆(2星)
悼涿州清行宮和藥王廟
作者:沉思修
藝術價值高的古建築,被人視為凝固的音樂,持久地散發著賞心悅目的絕響。那些氣勢恢弘、雕梁畫棟、美侖美奂的建築物,更是一種古典文化的傳承載體,延續的是極具民族特色的可觸可感的文脈。而河北涿州的清行宮和藥王廟,正是這樣一組罕見的古建築群,現卻幾乎被人為破壞殆盡。屬劫後余生的藥王廟大放光明殿、清行宮正殿殘體,卑瑣地龜縮在辦公樓、家屬樓的陰影裡,艱難地訴說著昔日的輝煌。面對這片幾近廢墟的龐大建築群,在旅游業被譽為朝陽產業,蒸蒸日上時,人們不禁痛心疾首,惋惜連連,悲從中來。是啊,於歷史文化遺產的損毀、破壞,我們需要反思的東西太多了!
清行宮和藥王廟位於涿州南關,既獨立又緊密相連,總占地面積80多畝。藥王廟建於明嘉靖,後在東院開設叢林,定名為“保慶寺”。該廟道光時改為三進院落,前祀神農、中祀彌勒,後奉觀音。原有四門,配殿四座,主體古建築共八座。大放光明殿屹立在3.2米的磚基上,高大肅穆,氣魄雄偉。清行宮由明保慶寺改建,乾隆帝體恤民情,為防大興土木,勞民傷財,就地取材,為皇帝南巡或皇室到西陵祭祖的駐跸之所。行宮分左、中、右三路。中路依次為宮門、二門、假山、正殿、亭榭、游廊、丘山、花園等。左路為太後宮,右路為皇後宮,有殿、閣、軒、樓等。宮門或曲徑通幽,或游廊相連。據《日下舊聞考》記載:行宮正殿匾額為“繡野迎熏”,聯為“春色芳菲入圖畫;化機活潑悟魚鸢”。西軒、觀風樓等處也有匾額和楹聯,皆為乾隆御書。
縱覽這組古建築,規模宏大,氣勢磅礴,古柏參天,殿台高峻,山石疊嶂,翠竹芭蕉,古雅幽深。尤其是行宮,正殿前假山掩映在一片綠蔭之中,若隱若現,奇峰異石,宛如蓬萊仙境。古籐盤山環樹,山石斑駁交錯,平添幾分仙氣。乾隆帝曾在此寫下許多御制詩,如《涿州覽古》:“燕雲易水帶晴川,涿鹿城南彈客鞭。村指樓桑聞勝碣,河流挾活始通船。道元故宅詢遺老,千秋名勝以人傳”。如《上元後二日駐跸行宮觀燈火作》:“節度上元方兩朝,排當煙景聽群僚。共稱墟裡裹糧夕,況尚錢王買燭霄。一晌千行燃火樹,半空百道接星樓。團栾寶兔騰東海,不負燈前奏六麼。”從這首詩可以看出,古涿州八景之一的“通會燈市”那時已負盛名。
民國時期,畫家月舟和尚主持保慶寺,為涿、宛、良、房四縣佛教分會所在地。每年夏四月、冬十月設南關廟會,商賈雲集,游人如織,藥王廟香火盛極一時。建國後電影《古剎鐘聲》曾在此拍攝外景。1979年,涿縣與鐵道部十八局簽定協議,以區區28萬元將這片古建築群出售。省、地區文化部門聞訊到涿州制止,縣委置若罔聞,分管領導竟說:“向文化局請示什麼?過去拆那麼多大廟,請示誰啦?!”於是嚴密封鎖消息,共拆古建11座,砍伐古樹141棵,內有直徑一米以上的古柏46棵。事件發生後,國務院、省、地多次提出嚴厲批評,但涿縣置明令禁止於不顧,在1982年又發生第二次強拆事件,拆毀古建3座,僧房3間,行宮正殿門窗和配殿被拆毀。河北省主管副省長發現後,電告省文物局派人制止,但這片龐大的古建築群,僅剩下行宮正殿框架、假山及藥王廟大放光明殿。保定地委勒令涿縣縣委做出深刻檢查,並對縣委主要領導、主管領導及有關責任人,分別給予了黨、政紀處分,《河北日報》頭版刊登了《涿縣縣委出賣拆毀古建築影響極壞,事情一拖再拖至今尚未解決》的文章,並以《無知的教訓》為題發表了評論。
清行宮和藥王廟,就這樣在愚昧的操縱、蠅頭小利的驅使下,令人痛心得難以置信地拆毀了,人類無知造成的惡果有時比天災更可怕。涿州歷史悠久,物阜民豐,人傑地靈,名勝古跡遍布城鄉,老祖宗留給涿州人的文化遺產何其寶貴、瑰麗、豐厚!但上世紀初至八十年代,絕大部分遭人為破壞,已近蕩然無存。始建於明景泰年間的古城牆,由於居民建房任意盜磚取土,南、東面城牆因征地建樓、修路而全部拆毀,今西、北城牆僅余殘垣1600米;作為古涿州標志性建築的雙塔,南塔被晉奉軍閥混戰的炮火打殘;明代建築通會樓,“文革”中為造反派盤踞,上架機槍,為“武斗指揮部”,貯存的學宮“藏經閣”數千冊古籍,或賣作廢紙,或付之一炬。不久,通會樓也被拆毀,樓內所存石碑被毀,明代鑄鐘及大小銅像被砸碎賣作廢銅爛鐵;始建於唐代的學宮被改建成家屬區,碑林被推倒,全部祭器、石刻、畫像被毀;城內三義廟、關帝廟、觀音堂等二十余座寺廟宮觀,或被拆毀,或改校捨,或作民居;城外的古寺廟,“文革”中大部分被毀,石碑用作建橋、蓋房、壘豬圈的石料,古樹被砍伐,法器、鐘鼓被賣;建於唐乾寧四年的三義宮在破“四舊”中被拆,數十通古碑被砸被賣,一百多棵直徑1米以上的古柏遭破伐,鋸成木板後,一部分為“武斗”死難者攢了棺材,其余被瓜分。元代宮廷雕刻家劉元制作的松木雕像,被劈作木柴分給村民,僅劉備的半個頭像就做了一挑豆腐;桓侯廟此時亦被毀,古碑被推倒棄置田間;1974年,在平整土地中,清涼寺由當時西河公社下令拆毀,高八丈的古塔被炸,觀音閣、迎春亭毀於拖拉機的隆隆聲中……。
眾多的文物古跡損毀了,逝去了,它們躲在並不遙遠的歷史背後,瞪大雙眼,目不轉睛地注視著我們。在非理性的年代,文化的傳承、延續,是孤立無援、疲弱無力的。近在“日邊”的涿州人歷來最講政治,“左”得幼稚可愛,“文革”中物質文化遺產幾乎被破除干淨了,還滿以為自己最堅定、最革命。今天要大力發展旅游了,游人對麗江、平遙等古城趨之若骛時,涿州人才如夢方醒,但也只能阿Q似地講:“從前我家也闊過”,滔滔不絕地說起昔日的輝煌。想至此,徹骨的涼意油然而生。對於傳統文化的損毀、破壞乃至割裂,需要悼念的豈止是清行宮和藥王廟呢?在涿州、在全國,因人禍已經逝去或行將消失的文物古跡又有多少?在人類社會發展中,與文明形影相隨的愚昧無知所造成的損失又怎樣估量,如何統計?清行宮和藥王廟,只不過是其中的滄海一粟。面對這片近乎廢墟的遺跡,不得不令人扪心自問:難道我們現在就真正變聰明了嗎?我們會不會成為下一個千古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