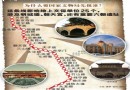考古遺址公園是考古遺址展示的主要方式
日期:2016/12/15 1:17:59 編輯:中國古代建築
50多歲的劉惠文是北京朝陽區惠新西裡的居民,多年來,她一早一晚都要到離家不遠的元大都遺址公園鍛煉。“應該以前是元代的都城吧,具體不大了解。”面對記者的采訪,對於元大都遺址,在此活動了多年的劉惠文依然不甚明了。
另一邊,作為其考古遺址公園的一部分,湖北大冶銅綠山四方塘遺址擬投入1.2億元建新館,廣東梅州預投入18億元建獅雄山秦漢遺址公園,甘肅天水預投資5億元建大地灣考古遺址公園……各地“砸大錢”建考古遺址博物館和考古遺址公園的現象蔚然成風。
“考古遺址公園是考古遺址展示的主要方式。”
每年,各地文物部門均會開展多項考古發掘,比如去年,收錄國家文物局編著的《2015中國重要考古發現》的就有40項,其他算不上“重要”發現的考古發掘則更多。考古遺址發掘完之後,若沒有進一步展示的規劃,為保護遺址,一般都會整體進行回填。
將要建考古遺址公園的內蒙古敖漢旗興隆窪遺址目前就處於回填狀態。該遺址先後經過7次大規模考古發掘,共揭露遺址面積3萬余平方米,清理出不同期別的半地穴式房址170余座、窖穴400余座、居室墓葬30余座。它是目前發掘的保存最完整、年代最早的原始村落,出土的目前所知中國年代最早的玉玦,為探討中國玉文化的源流提供了實證,出土的目前中國最完整的蚌裙服飾在世界范圍內也很罕見。更為重要的是,通過對其出土資料的分析,可以確認該地區的文明進程以及在東北亞地區所占的地位,也為確立西遼河文化與黃河文化平行發展以及對人類起源多元一體論提供了史證。記者近日探訪該處遺址發現,發掘現場除了標示的遺址區域,基本上就是一片草地。當地考古人員指點著“草地”講述的很多發掘信息,大部分聽不明白。對於普通民眾來說,確實需要直觀的闡釋,才能理解其中蘊含的巨大價值。
“考古遺址要進行展示,普及其中蘊含的文化內涵,並為當代人所用。考古遺址公園是展示的主要方式。”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系教授陸建松對記者說。
近年來,考古遺址公園建設得到國家層面的支持。2012年以來,國家文物局陸續出台了《國家考古遺址公園規劃編制要求(試行)》、《關於進一步規范考古遺址公園建設暨啟動第二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評定工作的通知》,對考古遺址公園建設進行規范。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已經被《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列為人文城市建設的重點。
“我們的考古遺址展示場所不是建得太多,而是太少了。”
具體到近日引起民眾熱議的銅綠山四方塘遺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陳建立贊同建新館。四方塘遺址自上世紀70年代發掘以來,發掘西周至西漢末的采礦井、巷360多個(條),古代冶銅爐7座,是目前我國采掘時間最早、冶煉水平最高、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處古銅礦遺址。早在1984年,銅綠山古銅礦遺址博物館就建成開放。然而,2006年,因遺址所在山體裂隙沉降,該博物館停止對外開放。
與此同時,遺址發掘不斷有重大收獲。2014年,遺址首次發現的墓葬區,是中國礦冶遺址中首次發現的古代礦冶生產者的墓地,使其呈現了采礦、洗礦、冶煉、安葬等完整的礦冶鏈條,對於中國冶煉史研究意義重大。“古銅礦遺址新館的設計方案已編制完,初步設計為采礦展示館、冶煉展示館等6個主題館,展示一條完整的礦冶之路。”銅綠山古銅礦遺址管委會相關負責人表示。
“四方塘遺址已發掘了40多年,發掘成果重大,將其價值揭示出來並展示給民眾,意義重大。”陳建立表示。而對於各地的興建熱潮,陳建立認為,相比中華民族燦爛悠久的文化,我們的考古遺址展示場所不是建得太多,而是太少了。比如每年從重大考古發掘中遴選出的十大考古新發現,目前已有260項入選,其中每一個項目都是我們民族的“根”,但是民眾對其又了解多少?
“同時要注意,遺址尤其是土遺址,一般比較脆弱,很容易遭到破壞,且可視性和可觀賞性也不強。這類遺址是否要投入大量資金建博物館或考古遺址公園,需要慎重考慮。”中國人民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韓建業提醒。河南內黃縣的三楊莊遺址就是其中一例。這處被譽為“中國龐貝古城”的遺址,建考古遺址公園展示後,遺址出現了成片青苔和霉變,遏制青苔和霉變使用的防潮藥水,又讓遺址內出現強烈的嗆人喉鼻的味道,且觀眾反映根本沒有看到這處古代遺址的震撼。
“很多考古遺址展示學術支撐不足,包括信息采集、還原研究不到位。”
然而,很多建成的考古遺址公園或者博物館,展示效果卻不理想,不斷被觀眾吐槽“看不懂”“看不下去”。韓建業一針見血地指出:“國內現在遺址博物館展示做得好的鳳毛麟角。而很多考古遺址公園,基本上等同於公園,市民去了就是休閒,遺址的作用沒有體現出來。”
“很多考古遺址的展示學術支撐不足,包括信息采集、還原研究不到位。”陸建松說,考古挖掘時很多信息,比如遺址地層關系、墓葬結構等,可以反映那個時代人們的生產、生活以及審美,但是很多都沒有采集,導致可以吸引民眾的故事講不出來。“比如良渚古城遺址,挖掘出7座貴族墓和140座平民墓後,就對其墓葬體量大小、隨葬品的數量與精美程度、有無棺椁痕跡等進行采集,以在展示時告訴觀眾什麼是已經出現了階級。”陸建松還進一步表示,很多遺址考古發掘完成後,需進行多學科研究,以還原遺址原來的面貌,再體現在遺址展示當中。“很遺憾,現在我們在這方面做得不夠,所以展示就不可能盡如人意。”他說。
陸建松認為,學術支撐是基礎,接下來的展示也並不是把出土文物一擺一放,而是需要詳細、嚴謹地編寫腳本,把學術的東西通俗化、理性的東西感性化、知識的東西趣味化、復雜的東西簡明化,根據展示的規律和表現方式,把遺址的故事“講”給觀眾,而這也正是目前考古遺址展示所缺乏的。
“國外遺址博物館的經驗值得借鑒,比如他們會考慮觀眾來此到底干什麼,會引導觀眾參與遺址知識普及的活動中,讓觀眾進去就‘閒’不下來。而我們很多就進去轉一圈,半懂不懂就出來了,導致很多資源的浪費。”韓建業從觀眾的角度提出建議。
陳建立認為,遺址展示還應積極運用數字化方式,讓展示更加生動。圓明園考古遺址公園就運用很多數字方式進行展示,觀眾可以在殘跡遺址前,掃描二維碼,那些被燒毀的屋宇庭院、亭台樓閣立刻“再現”,還可借助移動導覽系統,觀看收聽圖文並茂的全景環視、數字影片等,其效果受到業界一致好評。
另一邊,作為其考古遺址公園的一部分,湖北大冶銅綠山四方塘遺址擬投入1.2億元建新館,廣東梅州預投入18億元建獅雄山秦漢遺址公園,甘肅天水預投資5億元建大地灣考古遺址公園……各地“砸大錢”建考古遺址博物館和考古遺址公園的現象蔚然成風。
“考古遺址公園是考古遺址展示的主要方式。”
每年,各地文物部門均會開展多項考古發掘,比如去年,收錄國家文物局編著的《2015中國重要考古發現》的就有40項,其他算不上“重要”發現的考古發掘則更多。考古遺址發掘完之後,若沒有進一步展示的規劃,為保護遺址,一般都會整體進行回填。
將要建考古遺址公園的內蒙古敖漢旗興隆窪遺址目前就處於回填狀態。該遺址先後經過7次大規模考古發掘,共揭露遺址面積3萬余平方米,清理出不同期別的半地穴式房址170余座、窖穴400余座、居室墓葬30余座。它是目前發掘的保存最完整、年代最早的原始村落,出土的目前所知中國年代最早的玉玦,為探討中國玉文化的源流提供了實證,出土的目前中國最完整的蚌裙服飾在世界范圍內也很罕見。更為重要的是,通過對其出土資料的分析,可以確認該地區的文明進程以及在東北亞地區所占的地位,也為確立西遼河文化與黃河文化平行發展以及對人類起源多元一體論提供了史證。記者近日探訪該處遺址發現,發掘現場除了標示的遺址區域,基本上就是一片草地。當地考古人員指點著“草地”講述的很多發掘信息,大部分聽不明白。對於普通民眾來說,確實需要直觀的闡釋,才能理解其中蘊含的巨大價值。
“考古遺址要進行展示,普及其中蘊含的文化內涵,並為當代人所用。考古遺址公園是展示的主要方式。”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系教授陸建松對記者說。
近年來,考古遺址公園建設得到國家層面的支持。2012年以來,國家文物局陸續出台了《國家考古遺址公園規劃編制要求(試行)》、《關於進一步規范考古遺址公園建設暨啟動第二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評定工作的通知》,對考古遺址公園建設進行規范。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已經被《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列為人文城市建設的重點。
“我們的考古遺址展示場所不是建得太多,而是太少了。”
具體到近日引起民眾熱議的銅綠山四方塘遺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陳建立贊同建新館。四方塘遺址自上世紀70年代發掘以來,發掘西周至西漢末的采礦井、巷360多個(條),古代冶銅爐7座,是目前我國采掘時間最早、冶煉水平最高、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處古銅礦遺址。早在1984年,銅綠山古銅礦遺址博物館就建成開放。然而,2006年,因遺址所在山體裂隙沉降,該博物館停止對外開放。
與此同時,遺址發掘不斷有重大收獲。2014年,遺址首次發現的墓葬區,是中國礦冶遺址中首次發現的古代礦冶生產者的墓地,使其呈現了采礦、洗礦、冶煉、安葬等完整的礦冶鏈條,對於中國冶煉史研究意義重大。“古銅礦遺址新館的設計方案已編制完,初步設計為采礦展示館、冶煉展示館等6個主題館,展示一條完整的礦冶之路。”銅綠山古銅礦遺址管委會相關負責人表示。
“四方塘遺址已發掘了40多年,發掘成果重大,將其價值揭示出來並展示給民眾,意義重大。”陳建立表示。而對於各地的興建熱潮,陳建立認為,相比中華民族燦爛悠久的文化,我們的考古遺址展示場所不是建得太多,而是太少了。比如每年從重大考古發掘中遴選出的十大考古新發現,目前已有260項入選,其中每一個項目都是我們民族的“根”,但是民眾對其又了解多少?
“同時要注意,遺址尤其是土遺址,一般比較脆弱,很容易遭到破壞,且可視性和可觀賞性也不強。這類遺址是否要投入大量資金建博物館或考古遺址公園,需要慎重考慮。”中國人民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韓建業提醒。河南內黃縣的三楊莊遺址就是其中一例。這處被譽為“中國龐貝古城”的遺址,建考古遺址公園展示後,遺址出現了成片青苔和霉變,遏制青苔和霉變使用的防潮藥水,又讓遺址內出現強烈的嗆人喉鼻的味道,且觀眾反映根本沒有看到這處古代遺址的震撼。
“很多考古遺址展示學術支撐不足,包括信息采集、還原研究不到位。”
然而,很多建成的考古遺址公園或者博物館,展示效果卻不理想,不斷被觀眾吐槽“看不懂”“看不下去”。韓建業一針見血地指出:“國內現在遺址博物館展示做得好的鳳毛麟角。而很多考古遺址公園,基本上等同於公園,市民去了就是休閒,遺址的作用沒有體現出來。”
“很多考古遺址的展示學術支撐不足,包括信息采集、還原研究不到位。”陸建松說,考古挖掘時很多信息,比如遺址地層關系、墓葬結構等,可以反映那個時代人們的生產、生活以及審美,但是很多都沒有采集,導致可以吸引民眾的故事講不出來。“比如良渚古城遺址,挖掘出7座貴族墓和140座平民墓後,就對其墓葬體量大小、隨葬品的數量與精美程度、有無棺椁痕跡等進行采集,以在展示時告訴觀眾什麼是已經出現了階級。”陸建松還進一步表示,很多遺址考古發掘完成後,需進行多學科研究,以還原遺址原來的面貌,再體現在遺址展示當中。“很遺憾,現在我們在這方面做得不夠,所以展示就不可能盡如人意。”他說。
陸建松認為,學術支撐是基礎,接下來的展示也並不是把出土文物一擺一放,而是需要詳細、嚴謹地編寫腳本,把學術的東西通俗化、理性的東西感性化、知識的東西趣味化、復雜的東西簡明化,根據展示的規律和表現方式,把遺址的故事“講”給觀眾,而這也正是目前考古遺址展示所缺乏的。
“國外遺址博物館的經驗值得借鑒,比如他們會考慮觀眾來此到底干什麼,會引導觀眾參與遺址知識普及的活動中,讓觀眾進去就‘閒’不下來。而我們很多就進去轉一圈,半懂不懂就出來了,導致很多資源的浪費。”韓建業從觀眾的角度提出建議。
陳建立認為,遺址展示還應積極運用數字化方式,讓展示更加生動。圓明園考古遺址公園就運用很多數字方式進行展示,觀眾可以在殘跡遺址前,掃描二維碼,那些被燒毀的屋宇庭院、亭台樓閣立刻“再現”,還可借助移動導覽系統,觀看收聽圖文並茂的全景環視、數字影片等,其效果受到業界一致好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