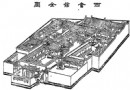南洋遺韻
日期:2016/12/14 23:56:49 編輯:古代建築名稱
鋪前鎮,海南島最北邊的一個鎮,當年第一代闖蕩南洋的文昌華僑,經歷了常人難以想像的艱辛困苦,賺到錢後就紛紛回鄉建大宅,如今,華僑們的血汗凝結成了鋪前老街的古老風景。
班車停靠在鋪前汽車站,下車後,沿公路向前走50米,十字路口的一側便是勝利街,正午的陽光很烈,明晃晃地照在斑駁的牆上,看的人的眼睛有些疼。一條長不過四百米的街,兩旁清一色的南洋騎樓建築,始建於1895年,歷經百年風雨,有一部分因缺乏保護已經顯得破舊不堪,斑駁的牆體,殘缺的拱券,寂寥落寞中,往日豪宅的氣息僅依稀可尋。
鴉片戰爭後的一百年間,中國東南沿海的勞工大規模地出國謀生,足跡遍及世界各地,形成了“海水到處,便有華僑”的格局。據記載,僅清光緒二年至二十四年(公元1876-1898年),從海南出洋的就有24萬之眾,他們中有一部分人是以自由人的身份去往南洋的,但大部分通過“契約華工”的方式出國,“霧起在南方,霧落在南方,重重迷霧鎖南洋”。

如今那段令人心酸的歷史早已經翻頁,唯有殘破的騎樓在陽光下靜靜伫立,當海風帶著鹹腥味徐徐吹來,孤獨的老人沉默地坐在自家門口獨自想著心事,挑擔的魚販子沿街叫賣卻遲遲沒有人幫襯生意,老式的理發店店門大開,卻不見一個人影,只有風采車在街前不停得繞圈兜客,叮叮當當的鈴聲劃破了長街的寧靜寂寥,不知這些騎樓的主人如今身在何處?在他們的身上曾經發生過怎樣的驚心動魄、辛酸曲折的故事?遙想當年,那些衣錦還鄉的游子們只將風光的一面帶回給家鄉,卻把沉重的痛苦深深埋在那個久遠的年代裡,一任歲月的滄桑將其漸漸侵蝕、吞沒。
從勝利街坐上一輛風采車,幾分鐘就到了溪北書院,書院的隔壁就是鋪前文北中學。鋪前鎮以前的名字叫溪北,因而鎮上這座書院就叫溪北書院。我去的時候,文北中學的學生們正在書院的第一進院子裡開會,滿滿一院子的學生坐在矮凳上,一棵參天大樹團團遮陰,青春的氣息和盎然的古意交相輝映。靜靜地站在書院門口,仿佛聞到了一股濃濃的書卷氣。一百多年前,這裡就曾經書香滿溢,規整的古樸庭院,樹下的石桌石椅,工整古拙的匾額,木窗棂透出的點點光線,空氣中似乎隱隱傳來上課的鐘聲,中國式的治學氣息,頓時讓我肅然起敬。

穿過庭院是一組四合院式的建築,正堂名“經正樓”,前殿和正殿之間以及東西二廊相互連接。中軸線的兩側和正殿的兩翼對稱地分布著後配殿和齋捨,殿內設有“講堂”,這裡是書院訓導學生的場所,我蹑手蹑腳地走進去,好像一下子就會迎面撞上一個表情嚴肅的老先生似的。配殿和齋捨已經破敗不堪了,門庭荒蕪,雜草叢生,有點聊齋中書生棲身的破廟的氣息,但其實那時的學子深夜苦讀,必定不是電視劇裡演繹的那番光景,水中開滿蓮花,映襯著安靜而古舊的朱紅色圍牆。圍牆外不遠處,便是煩囂市井,現實世界與精神世界只隔了一條小馬路。
旅游小貼士:從文昌汽車站乘坐到鋪前鎮的中巴車,海口汽車東站有發往鋪前的班車。從海口或文昌去鋪前,路程差不多遠。
到了鋪前,一定要嘗一嘗“糟粕醋”,這是鋪前特產,以酒糟發酵而成的酸醋為湯料,將一些海菜、蔬菜等燙焯之後,用鋪前糟粕醋拌起來吃,酸酸甜甜,非常可口。
鋪前鎮離海南島最北端的木蘭角很近,打摩的三十分鐘左右車程即到,那裡有一座亞洲最高的航標燈塔,有時間的話可以租看一下。
鎮上有一兩家小旅館可以提供住宿,不過條件都很一般。
- 上一頁:中和古鎮追尋一代文豪蘇東坡
- 下一頁:洋浦古鹽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