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鎮新場拍照
日期:2016/12/16 18:12:32 編輯:古代建築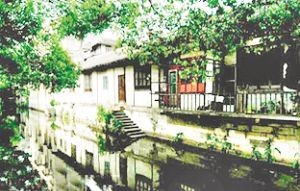 |
新場鎮位於滬南公路南匯段中間,是上海所轄南匯區的中心地帶,距上海市中心36公裡。車從從容容地開,也就是四五十分鐘,便到達了古鎮的“心尖兒”部位——古街口。在此矗立著一座沙石混建的三層牌樓,仰視之,見上面刻有“恩榮”“三世二品”“九列名卿”等字樣,好一個“三世二品”,難怪要樹如此氣派豪華的牌樓!細端詳,樹碑立傳者為明萬歷年太常寺卿朱國盛。明代的牌樓,古董啊!同行的幾位攝影愛好者早已披掛上陣,對著牌樓選取好角度,“咔嚓咔嚓”地拍上了。我端望著這牌樓,覺得它氣勢確是不凡,可建造工藝著實不敢恭維,便斷定它是仿建,果然得到導游小姐的確認。這導游小姐是新場人,她不無驕傲地告訴我們,這牌樓,已重建過兩次,只有它才能標識出我們新場的古老,民間有這樣的話“十八牌樓九龍環,小小新場賽蘇州”,說的就是明清時期新場的繁華。
過了那蠻震唬人的“三世二品”牌樓,我們進入了一條由寬變窄的老街。腳下的石板小路已裂紋斑駁,放眼望去,路旁的店鋪樓雖高高低低,卻是一水的青磚木板小二樓。細看兩側,家家都似上門板的《林家鋪子》,唯有不同的是各家鋪子顏色各異,有墨綠,有銹黃,有黑褐,扎眼一點的也就是原色,這些顏色混合出老街的味道,在古舊的背景之下,再綴上幾串高挑的紅燈籠和繁體字牌匾,於是,整個街面便充滿了故事……
“張姐,您看這家雜貨店好像在《色戒》裡出現過。”我聞聲而至,眼前的“益記煙雜店”還真是似曾相識,這歷盡滄桑的小店,簡直就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最經典的街景!李安選擇這裡作為《色戒》的拍攝地,或許看中的正是這古鎮傳承至今的那份寵辱不驚的煙火氣……“咔嚓!”我立馬按下了快門,爽得好似把身穿旗袍的美女王桂芝連同歪戴帽斜瞪眼的汪偽特務一同收進了自己的奧林巴斯560。
正當我們幾個舉著相機,站在老街中央,對著那些當鋪、藥房、古董店等頗具特色的景物猛拍時,忽然聽到導游小姐喊道:“等會再拍吧,咱們先進前面的院兒裡看一個展覽。”大約半小時後,當我們從那個院落出來的時候,對新場這地兒的歷史變遷已知一二:原來我們置身的這個新場古鎮已有千年歷史,該地原為鹽場,後逐漸成為鹽民居住和交換商品之地。新場又名“石筍裡”,城鎮之時,正值這裡的鹽業鼎盛之際,商人鹽販紛紛聚集於此,於是人口劇增。當時鎮區歌樓酒肆商賈雲集,其繁華程度曾一度超過上海縣城,為當時浦東平原上的第一大鎮。清末以後,戰亂連連,古鎮幾經興衰,然而,歷史的滄桑,始終未抹去江南水鄉的清秀本色和人文氣息。對此,新場人很是引以為豪。
穿過一段狹長的街路,一座石拱小橋出現在面前,上得橋去,我眼前一亮,穿鎮而過的河道寬不過四五米,但河水清澈。高壘的石駁岸,傍水而建的民居,沿河人家那一座座馬鞍形的水橋,眼前這景物真不亞於陳逸飛畫筆下的水墨周莊!良辰美景,人生得意,所有帶相機的人不約而同地打開鏡頭,各取所需。或許是因地方局促,或許是機子的廣角還不夠大,我橋上橋下轉悠了幾個來回,總不能把“小橋,流水,人家”三要素恰到好處地收進畫面,正跟自己較勁,抬頭見一同伴在拍街口橋頭處的木樓飯莊。嘿,有特色,這木樓臨水臨街,古色古香,尤其是樓上的窗子,多是半掩半閉,再有紅色紗燈點綴,仰視之,竟有潘金蓮掉窗桿的遐想……於是,這樓,這窗,在我按下快門的剎那成為了永恆。
當我們要離別古鎮的時候,已是下午的四點多鐘。古鎮新區的商業街上,人來車往,繁華熱鬧。我們乘坐的大轎車吃力地轉彎抹角,終於拐入一條寬闊些的街道。從車窗望去,沿街新建起一排仿古木樓,那款式與老街如出一轍,甚至更漂亮、更整齊,但在我們這些剛剛從古鎮深處走出來的游客眼裡,這些仿建景物已是“形似神不同”了。但願新場不要像有些旅游熱地那樣,在利益的驅動下開發過度,而失去千年古鎮的神韻與風采。
- 上一頁:黃姚古鎮:畫畫的天堂
- 下一頁:江蘇丹徒南鄉古鎮煥發青春活力
熱門文章
熱門圖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