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裡長城第一人”,中國文物保護神--羅哲文
日期:2016/12/14 18:58:56 編輯:古建築保護這些年來,隨著經濟基礎越來越雄厚,我國對數百處國寶級古代建築進行了重大維修,如萬裡長城、西藏布達拉宮、青海塔爾寺、山西太原晉祠、朔州崇福寺等等。作為全國古代建築保護與維修事業的組織者,羅哲文或親自設計,或主持方案評審,或參加竣工驗收,他始終精力充沛地活躍在全國各地的古建維修工地上。在去世前兩年,在86歲的高齡上,他還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天上飛來飛去”。調查研究之余,他先後撰寫了一系列多方面、多角度探索中國古代建築的學術論文和專著。早年我就買過他領銜所著的《中國名塔》《中國名陵》《中國名觀》《中國名關》這系列叢書。除了自身的學術考察與研究,更為重要的是,羅哲文在中央與地方、行政與學術之間,能夠構建起良性互動的橋梁。也就是說,他在調研與實踐中獲得理論認知,成就了巨多學術著作,同時又直接投身於實踐,以實際的努力保護全國各地的重要文物。
中央文史館館員舒乙與羅哲文有多年深交,在他的眼裡,羅哲文“是個小老頭,個子矮矮的……有一半時間在飛機上……不停地出席各地的古建、文物專業聚會,提供咨詢、論證和建議”。
今年是被譽為“萬裡長城第一人”的羅哲文從事長城保護工作60周年的紀念,而其文化遺產保護生涯更可追溯為72年,從1940年追隨梁思成先生算起。
羅老的生平
1940年,年方16歲的羅哲文考入了中國營造學社,從一個放牛娃成為梁思成的入室弟子。事實上,羅哲文當年去投考時並不了解營造學社的具體工作,但是見到考題中有寫字、畫畫等內容,覺得很有興趣,便去考了,居然成為眾多考生中唯一一名被錄取者。從此,羅哲文踏進了古建築學之門。在中國營造學社,羅哲文先後師從劉敦桢、梁思成和林徽因,最初協助整理資料並測繪古建築。
那時,羅哲文還不過是個貪玩的孩子。有一次,他閒來無事在地上畫畫,陶醉其中的模樣感染了恰好路過的梁思成,梁思成讓他畫個民居建築,羅哲文所表現出來的才華和天賦讓梁思成當即決定:由自己直接傳授繪圖技藝。這樣,羅哲文成為梁思成的親傳弟子。梁思成對羅哲文寄予厚望,口傳心授、事無巨細。羅哲文在生前所著的回憶文章裡曾這樣寫到梁思成:“我至今難忘的是他那種對學藝青年耐心細致的傳藝精神,他從繪圖板、丁字尺、三角板和繪圖儀器的使用方法,到削鉛筆、擦橡皮等小技巧都一一手把手地教……”
梁思成把羅哲文引入了廣闊的建築藝術殿堂,他和羅哲文談線條的藝術性、圖紙的藝術性,羅哲文領會著建築藝術的美,開始著迷於古建築研究。而梁思成對羅哲文的關懷是方方面面的,連“羅哲文”這個名字,都是梁先生起的。羅哲文原名羅自福,常被人取笑為“羅斯福”,於是,梁先生給他改名為“哲文”。
林徽因則利用業余時間幫羅哲文補習英文,多年後,羅哲文驚奇地發現,自己查閱、利用英文資料居然得心應手,而這得益於林徽因為他打下的厚實的英文功底。在梁思成等中國營造學社的主力社員的口傳心授下,年輕的羅哲文很快就學會了攝影,也學會了自己沖洗照片,直到去世前兩年,他依然背著相機東奔西跑、爬上爬下,精力和興趣不讓年輕人。梁思成是傳統知識分子,一生踏踏實實治學、樸實無華做人,對金錢、地位沒有奢求,梁思成為人、治學的精神影響著羅哲文,“勤勤懇懇做點事情”也成為他做人的標准,古建築研究和保護成為他畢生追求的事業。當晚年的羅哲文回憶起當初的情景時,依舊動情:“他們很愛護年輕人,給我印象很深。我現在也是這樣,想方設法幫助年輕人多學點東西。”
“文革”中,當梁思成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之後,為了避免受到牽連,很多以前聯系密切的人都疏遠了。然後,某日當梁思成在醫院輸液時遇到學生羅哲文時,他高興得幾乎流淚。在這次見面中,梁思成囑咐羅哲文:“文物、古建築是全人類的財富,沒有階級性,沒有國界,在變革中能把重點文物保護下來,功莫大焉。” 事實上,得益於傳統師徒相授模式的羅哲文,在晚年也開門收徒,用傳統的收徒形式來傳承和弘揚中國古建築的優良傳統與技術工藝,2012年初,他收了第三批弟子,現在羅門弟子共有31人。
1944年夏天,羅哲文跟隨梁思成到重慶。當梁思成用鉛筆在五萬分之一的地圖上標出盟軍轟炸敵占區時需要保護的古建築,並特別提出需要保護的日本京都和奈良古建的位置之後,羅哲文則用繪畫墨水把鉛筆所畫的位置描繪清楚。這份地圖之後被交給美軍,保護了京都和奈良的20余座古代建築。
1946年冬,羅哲文押送圖書資料,隨中國營造學社到了北平。梁思成時任清華大學建築系主任,羅哲文即擔任梁思成的助理,在位於北京清華園的清華大學與中國營造學社合辦的中國建築研究所工作。1948年底,解放軍包圍北平並派人找到梁思成,表達要保護文物古跡的強烈願望,於是,梁思成和林徽因連夜在軍用地圖上一一圈點出禁止炮轟的古建築,這期間,羅哲文一直跟隨他們,協助完成這張特殊地圖的繪制。北平和平解放後,共產黨再次派人向梁思成請教在解放戰爭中如何保護全國的文化遺產,於是,在梁思成的指導下,羅哲文直接參與編寫、刻印、裝訂了長達100多頁的《全國重要建築文物簡目》,這份目錄僅用一個月時間就編印完成,列舉、標注出全國各地需要保護的重要文物,對在解放戰爭中保護文物和古建築起到了切實作用。
1950年,羅哲文被調任到文化部文物局(後改為國家文物局)任職,時年27歲的羅哲文是當時國家文物局最年輕的古建築專家。他先是擔任文物局局長鄭振铎的業務秘書,其後也在文物檔案資料研究室、中國文物研究所等任職。
為長城保護貢獻一生
正是在文化部文物局,羅哲文開始了整整60年的長城保護生涯。當文物局局長鄭振铎找到羅哲文,讓他負責先行制定長城的勘察規劃之後。羅哲文連夜和幾位助手籌劃行動方案,他卻發現,長城雖分布范圍很廣,但經過2000多年的風雨侵蝕和人為破壞,保存完整的段落已不多。因此他建議,先選擇山海關、居庸關、八達嶺三個重點段進行勘察、維修。
此後,羅哲文開始了艱苦的實地勘察。當時,通向八達嶺的山路異常崎岖,攀爬時有隨時掉下山谷的危險,往往羅哲文牽著從當地老鄉家借來的毛驢走上大半天到達山頂時,天已全黑,只得枕著荒地和衣而眠,天亮再開始勘察。三個月勘察之後,羅哲文做了一份針對八達嶺長城的維修計劃,繪制了草圖請梁思成審定。病中的梁思成看完草圖後當即在圖紙上做了審定簽名,並附上維修意見。這張珍貴的圖紙一直是羅哲文的珍藏,他曾說:“老師提的意見,對我以後幾十年的文物維修工作都具有指導意義。他說古建築維修要有古意,要‘整舊如舊’,不要全都換成新磚、新石,不要用洋灰;殘斷的地方,沒有危險、不危及游人安全的就不必全修了,‘故壘斜陽’更覺有味兒。”
依據“整舊如舊”的標准,羅哲文提出修復長城的辦法:廣泛搜集坍塌下來的城磚。用原有材料修復,以保持長城的本來面貌。一塊塊城磚隱藏在沙土、山溝、樹叢、淤泥,甚至是老鄉的家裡,搜集舊磚的工程花費了他們大量的時間精力。因為石頭松動、腳踩空、手抓著的樹木折斷等突發險情,羅哲文和他的助手多次經歷。
修繕後的八達嶺長城在1953年國慶節向中外游客開放,此後,嘉峪關、金山嶺等處長城也得到維修。面對北京金山嶺長城的單面牆,羅哲文只能利用山羊把磚馱上去,一只山羊一次能馱兩塊磚。1984年9月,羅哲文的足跡又留在了慕田峪、司馬台、九門口、玉門關等長城上。
有人說,羅哲文是修復長城的工匠,也是研究長城的學者和大師。事實上,他的研究不僅靠資料,更注重現場調查,羅哲文曾說:“文獻可以參考,但必須結合實際。”五十多年的實地考察,羅哲文爬過很多尚未修復的長城,“有一些地方單用腳上不去,要手腳並用,上面抓著,下面蹬著,才能上去。我曾經也差一點摔死了。”
雖然被譽為“萬裡長城第一人”,但是羅哲文生前力陳“古長城不止十萬裡”。他通過考察發現:關於長城的長度,外國人是用比例尺從地圖上量出來的,這顯然是不准確的,因為長城不是直線,更不是水平線,也不是只有一道,而是曲曲折折、上上下下,由許多道構成的;我國歷史文獻上的記載,雖然比較可信,但沒有把一道長城的雙重、三重、多重的長度計算在內;許多人認為,各個朝代的長城都是在一條線上修築或重修的,其實這並不符合實際,比如秦、漢、明三個朝代的長城,都不在一個起點,也不在一個終點,相去數百甚至上千裡。在70多年古建研究保護以及60年長城保護生涯中,羅哲文無數次親自攀登長城,反復進行實地考察,有的地方去過上百次,更有過許多獨特的發現和見解。1985年,素有文物保護“三駕馬車”之稱的羅哲文、鄭孝燮和單士元起草文本,參加了《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的申報工作,使長城成為被保護的世界文化遺產之一。
保護古運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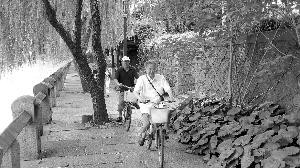
2010年,86歲高齡的羅哲文騎公共自行車沿運河杭州段騎行,鼓勵公眾通過大運河遺產小道保護文物。

羅哲文(左2)在錫考察古運河。
“京杭大運河申遺是羅老最後的牽掛。”昨天,羅哲文的弟子兼助手、《人民日報》記者齊欣回憶起羅老時表示,羅老開創並推動了中國文化遺產保護事業,今天的每個人都是其受益者。為紀念羅老對京杭大運河的申遺情結,大運河遺產小道的北京段和杭州段擬以羅哲文的名字命名。
眾所周知,羅老是上世紀80年代長城成功申遺的功臣,而堪與長城比肩的京杭大運河,其實也完全有資格入選世界文化遺產,最近20年來,羅老一直為此奔走呼吁。“是他開辟和推動了中國文化遺產的申遺和保護,他是開辟了一個時代的人,我們都是他的追隨者。”齊欣放慢語速,字斟句酌地說。
齊欣回憶說,2006年羅老曾以八旬高齡親赴運河沿線考察,但卻很少有人知道,老人家出發前騎自行車摔成了腦震蕩,卻死活不去醫院:“去了醫院,考察就去不成了!”就這樣,在考察團的11天行程內,老人家沒敢洗一次澡,每次吃飯時都在飯桌下偷偷地挽起褲腿晾傷口,以防傷口感染影響行程。
在羅老的支持下,“大運河遺產小道”應運而生,這是一條沿著大運河開辟的供步行和騎行的文化遺產小道,用以體會大運河作為“活的文化遺產”的“真實性”和“完整性”。齊欣透露,這條大河小道的起止兩端——北京段和杭州段,將以“羅哲文小道”命名,來紀念羅老未竟的心願。
5月9日剛從這條大河小道上回來,齊欣便趕赴中日友好醫院陪恩師。齊欣說,老人很堅強,直到最後,年近九旬的他頭上仍有黑發,臉色也很好。“他總是不遺余力地推動各種社會力量保護文化遺產,不僅僅是靠政府和學者。他不會去謾罵和焦慮,更不會放棄不管,他用平常心做著偉大事,這是我從他那裡學到的最值得懷念的精神。”
羅老曾說過,“‘江南憶,最憶是杭州’。我所參與和經歷的許多有歷史意義的工作,都在西子湖畔醞釀、發展並隨之轟轟烈烈地產生巨大價值。”曾與羅哲文、鄭孝燮並稱“運河三老”的朱炳仁曾在杭州陪同申遺專家團考察大運河。他回憶說,羅老已經到杭州去了99次,“我們正計劃下半年邀請他再來杭州,為這第100次搞個活動,沒想到……”
不僅如此,當下全中國的國家級的文化名城,每一座羅哲文都親自考察過,他在實踐中發現,保護古建築離不開周圍的環境,像洛陽、西安這樣的古都,倘若單獨保護一個古跡,很難奏效。於是,他和一些專家提出“歷史文化名城整體保護”的建議,作為政協提案。事實上,羅哲文幾乎參加了中國文化遺產保護的所有重大事件,很多還是由他倡議並參與實施的。從長城保護到大運河申遺,從歷史文化名城到加入《世界文化遺產公約》,羅哲文奔走疾呼、日夜操勞,為中國文化遺產保護作出了傑出貢獻。2009年,羅哲文獲得了由文化部、國家文物局評選的從事60年文物傑出貢獻獎並被授予“中國文化遺產保護終身成就獎”。
羅哲文在彌留之際,還掛念著北京北總布胡同24號梁林故居遭拆遷事件。謝辰生告訴記者:“羅哲文以為是要在原址蓋梁思成紀念館,而且是北京市文物局同意的事情,所以他在接受采訪時說他是同意的,哪想到這都是開發商的說辭。後來,當我上個月在媒體上澄清這個事情之後,羅哲文已經住院了,他在醫院裡還打電話給我,感謝我替他最後把這個事情說清楚。其實,無論他學術觀點上怎麼認為,對於梁林,他從感情因素上來說,都是不可能贊同拆除的。”事實上,羅哲文曾這樣評價過對梁林故居的保護:“我應該這樣做,這個故居是可以恢復的。它是梁先生生命中的一個重要階段,即營造學社的階段。我還考慮到一個因素,就是作為一個建築學家,梁先生居住過的地方很少被定為文物,如曾經住過的長沙、昆明、李莊等都沒有列為文物保護單位。所以,我主張將它(北總布胡同24號)定為文物。”
“斷壁殘垣古墟殘,夕陽如火照燕山。今朝賜上金戎刀,要使長龍復舊觀。”這是羅哲文第一次看到破敗不堪的八達嶺長城時所作的詩句。斯人已逝,其保護文化遺產的智慧和決心則將像此詩句一樣勉勵後人。
保護文物,就是保護文化,保護藝術,保護國之精粹。“藝術是以一種優雅的姿態對待世界的沉思。”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德語作家黑塞如是有雲。文物也好,藝術也好,文化也好,確實都是一種“沒有後坐力的武器”,它所具有的是優雅的姿態與沉思的力量,它需要有活的人的保護。羅哲文先生就是這樣的文物保護者、文化守護神;當今這樣的守護神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太少……
有一組數字與羅哲文密切相關:全國103座歷史文化名城的逐批評定,2351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分批審定,30多處我國境內的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的申報成功——羅哲文都是親歷親為,從而使得我國文物保護事業的廣度與深度獲得了史無前例的拓展。
與文物保護背道而馳的是,某些地方政府不顧長遠利益,對文物的肆意破壞,一味讓位於經濟建設,使很多中國文化的寶貴遺產遭遇滅頂之災。1998年,浙江省定海市大拆大建,古宅老居為新居“讓路”,這座極具江南特色的歷史文化古城,在“舊城改造”中被毀得面目全非。次年,包括羅哲文在內的一批古建築專家前去調查,希望當地政府能保護古建。當地政府置若罔聞,並加快了拆遷速度,0.8平方公裡的古城,轉眼間只剩下0.13平方公裡。羅哲文憤怒地找到媒體,將此事曝光,並得到中央的批示,這座古城的拆遷才被制止……羅哲文認為,零打碎敲的破壞不是最危險的,最可怕的是一個城市的決策者,其權力越大,其毀壞力也更大,“他的一個錯誤決定,就足以使一座城市的文物遭受不可逆轉的破壞”。
- 上一頁:品味黨家村
- 下一頁:羅哲文先生與蘇州城牆的因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