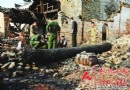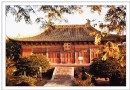背身西湖 尋找杭城歷史之根
日期:2016/12/14 13:11:54 編輯:古代建築有哪些
拱宸橋,運河入杭城的門戶
記得十多年前第一次到杭州,出了車站,已近五點,便徑直奔了蘇堤,為的是一睹西子湖的暮色。那時傍晚的蘇堤已沒了多少游人,就連守侯橋頭的瞎子藝人也收起了胡琴,准備打烊收攤,但見我們遠遠走來,再又端坐橋頭,裝模作樣地拉起了二泉映月。琴聲悠揚,月色也著實的迷人。吸飽吮足之後,慢慢步出了蘇堤,一身皮囊的需求也由肺葉轉到了雙腿和腸胃。哪知眼前仍是一片茫茫的暮色,一不見霓虹,二不見人影,昏暗的路燈下唯有長長的樹影。在錯誤的時刻我們再次作出了錯誤的判斷,向西拐上了楊公堤。余下的行程自不必多說,漫漫一路幽靜地令人生厭的荷湖柳岸。大約走了十公裡後,終才在斷橋一帶見著了可親的燈光和行人,住進了旅店。那時的我們尚不知美麗的杭州原是"三面湖山一面城"。我們伴著夜色走過了三面湖山,終才進到了那面城。
滄海桑田見杭城
"三面湖山一面城",是近兩千來人們對杭州城的描述。天地氤氲,群峰逶迤,既享湖光之旖旎,又得山林之野趣。然而在遠古先民們的眼裡,卻沒有這番景致,他們所能望見的僅僅只是"三面雲山一面海"。那座名為"杭州"的城市尚還為一片滔天惡浪所覆沒,而那灣美麗的西子湖只不過是汪洋中的一片小小海灣。海灣西北二十多裡外的廣袤平原上,才是原始先民們的棲息地,考古學家們稱其為"良渚"。
春秋戰國,杭州故地先屬吳地,再屬越國,後又為楚國所吞並,但最終還是歸入了大秦的版圖。直到此時,杭州城仍還是一片茫茫水色,以至於始皇帝"南巡會稽,至錢唐,水波惡"。時間到了東漢,汪洋漸退,露出大片的淺灘沙洲。為了阻止海水倒灌,錢塘縣吏華信廣募民夫修築防海大塘,終使沙洲灘塗成了可耕墾造屋的平陸,西湖也與大海相隔成了內湖。據說斷橋旁的一方山崖正是當年始皇帝望洋興歎時泊舟纜繩的巨石。後宋僧憑崖鑿佛,築大佛禅寺。今寺中造像殘跡尚存,佛殿僧房也遺有數十間之多,且與游人絡繹的北山路、斷橋咫尺相望,卻因淪為尋常百姓家而少有人識得。
夢尋臨安城
說到杭州,人們總愛念叨西子湖畔的名勝:祭岳墳、游蘇堤、觀平湖秋月、賞斷橋殘雪……多年以來,身後的這座城,似乎僅是游人們進食入眠的巨大營房。時下,讓我們暫且撇開那些詠了千萬遍的西湖名勝、西湖名人,認認真真地看看身後的這座名叫"杭州"的城。

煙霞洞尋佛
杭州古稱臨安,乃帝都,高宗趙構南逃倉皇而建。上溯歷朝的京畿王城,南京承的是民國的規劃,北京襲的是元明清的布局,開封洛陽西安城雖乃古都名城,但累經兵災人禍千余年的洗禮,早已難辨遠古都城的模樣。杭州雖已沒了多少宋時的遺構,但城的格局仍依的是舊制,八百年來未曾更變。南宋臨安倉皇草創,再加之受山形水系的限制,其城的格局已顧不上帝王都"南城北宮"的制式,置皇宮大內於城南,城廂坊肆於城北。就連南北宮門也左右交錯,不在同一軸線上。南宋皇宮憑鳳凰山而築,山中古木參天,奇石峭陳,乃宋時的皇家御苑。如今山中尚存多處遺跡,"月巖"乃高宗皇帝中秋賞月的勝境;"忠實"摩崖石刻乃高宗親筆御書;"聖果寺"系專門負責內廷供奉的殿司衙故址,現仍存三尊被鑿去面目的吳越大佛造像……
北宮門外乃御街,長約十裡。八百年後的今天,南宋御街的繁華依然延續,從五代吳越的千年白塔到元朝末年的鳳山水門,從元初的清真大寺到清末的禮拜聖堂,太多歷史遺構沿著御街向城北鋪排開去。沿街的藥號絲行百貨莊鱗次栉比,或為清末的木構老鋪,或為民初的雕花洋樓。雖然門庭多已更換,但昔日的余韻仍難為今世的喧囂所掩蓋。御街的兩側乃坊巷,共計九廂八十坊。且那九廂八十坊多還延續著舊時的坊名,舊時的烏瓦粉牆格扇門。
四百八十寺
當年蘇東坡寓居杭州期間,除了邀友游湖探幽之外,去的最多的當算是西湖周邊山林間的寺院禅林。杭城佛事興於五代吳越,時有"東南佛國"之譽。後宋室南渡,佛事更盛,梵宮佛剎,遍布湖山之間,時有廟宇宮觀四百八十所,在西湖周圍形成了以天竺靈隱為中心的北山寺廟群,和以南屏淨慈為中心的南山寺廟群。只可惜來了群天國的神兵,東南佛國蕩滌殆盡。經過數十年的重建,杭州城的香火再度興盛。郁達夫曾調侃道:"杭州西湖的周圍,第一多若是蚊子的話,那第二多當然可以說是寺院裡的和尚尼姑等世外之人了……"哪知又一批革命的小將,再次摧毀了重建後的聖地,唯留下靈隱、天竺、淨慈等數座禅寺奉享香火。殊不知,今日的杭城還深藏著許多昔日佛國遺存下來的千年佛跡,它們或隱於林莽,或匿於塵廛,少為人知。莫說外地的游人,本城的居民,就連與其同處一地的僧侶住戶也未必知曉它們的存在。如龍興寺經幢、香積寺石塔、彌陀寺石經、梵天寺經幢、大佛寺佛頭、聖果寺三佛、寶成寺造像、煙霞洞造像、佛國山造像、資賢寺造像、天龍寺造像、通玄觀三茅真君造像……

天龍寺造像
悠悠運河路
大運河,史書中的人類奇跡,現實中的排污溝、垃圾場。大運河的締造者隋炀帝被臭罵了千年,大運河更廢斷流的時代卻始終被頌揚著。藉漕運之利,江南從此富甲天下,同時也造就了揚州、蘇州、無錫、鎮江等無數名城名鎮,杭州也由一個"成陸未久,江海水泉鹹苦"的小小郡縣發展成為東南一大都會。杭州城的繁興得益於大運河,城裡的人們也珍惜這條滋養了他們千年的古老運河。時至今日,運河的河道上依舊跑著長長的鐵駁木船,岸邊那些石橋古埠、寺塔倉廒、街肆集鎮等舊時風物仍歷歷在目。拱宸橋,全長近百米的三孔石拱橋,運河入杭城的門戶;小河直街,古老的河街河埠水碼頭,杭州城北漕糧水產及農副土產的集散地;富義倉,可儲稻谷五萬石的漕運糧倉;金江干,盛極千年的浙江市,時有"小上海"之譽;西興鎮,一座存有無數石橋、古廟、老鋪、河房,卻又行將消失的運河古鎮。
開肆三萬家
北宋宮廷畫師張擇端曾繪有一《清明上河圖》,將汴梁城的城郭樓台、瓦肆鋪席、舟車橋梁等市井風物繪於絹上。後宋都南遷,時人雖未像張擇端那樣以畫筆描繪出汴梁城的繁盛,但卻以老妪敘事般的文字將京師百肆雜陳的景象一一羅列。"自大街及諸坊巷,大小鋪席,連門俱是,即無虛空之屋","處處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彩帛、絨線、香燭、油醬、食米、下飯魚肉鲞臘等鋪"……如今,南宋御街的繁華依然延續,古塔、水門、石橋,沿街古老的廂坊裡巷。尤其是那些接棟連檐的舊時商號,如張小泉剪刀、張允昇線帽百貨莊、孔鳳春香粉店、宓大昌旱煙店、方裕和南北貨店、胡慶余堂、方回春堂、張同泰堂、朱養心藥室、邊福茂鞋店、太昶皮鞋店、翁隆盛茶號、萬隆火腿莊、九芝齋……如此風物,呈現給今人的又何嘗不是一幅現實版的《清明上河圖》。
巷陌深處是人家
自打寫《尋城記》以來,也先後尋訪了許多座城市,但始終未將北京、上海這中國的兩大超級都市納入寫作范疇,原因頗多,但終歸說來還是其城市形態遠不及另幾座城市活潑。京畿北京除了王府大宅門,就是胡同四合院。除去等級高低、規模大小,幾乎就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上海全城襲的是西洋的制式,清一色的公館洋房石庫門,看得多了,也難免疲乏。杭州則生的靈動,且不說西湖邊數之不盡的古跡,山林間深藏的摩崖造像,僅就人的住地而言,就造得頗為豐富。

巷陌深處是人家
巷陌深處是人家
杭州城今仍沿襲的是南宋的九廂八十坊。廂中設坊,坊中置巷,巷中廬捨鱗栉。小青瓦、粉壁牆、飛翼雕檐、走馬回廊,戶戶不同,各有各的妙處。坊巷之間也多典故,如這察院巷,至宋時起就為署衙叢集地;城隍牌樓巷,系舊時登臨吳山的進香古道,康熙、乾隆二帝南巡杭州,也不知來來回回走過了多少趟;五柳巷,舊為南宋皇家的御花園,今倒成了杭州城內最後的一片水鄉;元福巷,曾經流光溢彩的元宵燈市,如今老屋老鋪依舊,只是多了一個個鮮紅的"搬"字;積善坊,百戲伎藝們的聚集地;三元坊巷,屠肆肉鋪雲集的巷陌裡坊,後出了位三元及第的狀元郎,才得了該名;金钗袋巷,曾經茶行貨號林立的南宋茶街;孩兒巷,"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說得就是它……
杭城現存的大宅府邸多集中在城東,即中河的東岸,都是那種左中右三路,前後數進,闊約十余畝的高大牆門。保存較好的就有雲貴總督吳振棫府、刑部尚書梁肯堂府、大學士王文韶府、兵部侍郎朱智府,以及太平天國時期的聽王陳炳文府。府府庭院深深,滿目的雕華。更有錢塘江南岸的長河來氏家族,乃書香世家,兩浙巨宗,僅從其家門中走的進士就多達二十四位。
錢塘門至湧金門一帶的湖濱地,原是清時駐防八旗精兵的滿城,俗稱"旗下營"。旗下營臨西湖而居,高牆壁壘,將杭城人與西子湖阻隔了兩百余年。入民國後,政府拆除滿城,辟新街新市,興建時下最為流行的石庫門住宅,形成一片片聯棟的裡弄,如湖邊邨、星遠裡、勸業裡、大慶裡、思鑫坊、泗水坊、恰豐裡、平遠裡……
西湖的南北兩岸,背山面水,遠離市廛塵囂,自古就為王侯逸士所向往,精心構築園囿別墅、樓榭水閣。民國後,那些南京的政客、上海的大亨、學界的名流們也蜂擁而至,在西子湖畔置上一片湖畔別墅,結下幾間雅捨靜廬,以享受這天堂間的閒情逸趣,於是形成了今日連綿數千米的“北山路民國建築博物館”。
又到了周末,西子湖畔的游人比平日增加了許多,一輛輛巴士、私家車將西子湖死死地圍成了一圈,這是弘一法師怎麼也想象不出來的景象。白市長、蘇市長估計也難有憑湖臨風的雅性來作詩寫詞。人們絡繹而來,興盡而去,流連忘返,但總是忘卻了身後的這座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