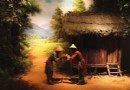裡耶與邊城茶峒:正在剝落的建築遺存
日期:2016/12/15 0:41:47 編輯:中國古代建築原生態的村落消失,傳統文明的村鎮失落……曾經大拆大建的傳統城鎮化游戲規則,摧毀了中國傳統文脈與建築話語體系。而現在,已經到了規則重建的時刻。
彰顯特色,正是這種規則重建的表現。在同一個區域如何實現城鎮的差異化?在擁有同樣歷史文化基因的村鎮,如何實現求同存異?
歸根結底,新型城鎮化終究是需要因地制宜,落於地方特質。


本期主角
古鎮 邊城茶峒、裡耶
選擇理由:這是第一次同時選擇兩座古鎮作為標本,它們是花垣縣邊城茶峒、龍山縣裡耶。
兩者有著同樣的文脈傳承,曾經都是湘西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古鎮。但兩者又有著截然不同的命運,在外來文化的沖擊中,邊城茶峒面臨文明的支離破碎,而裡耶則因為相對閉塞,完好地保存了歷史的傳承。一個共同命題是:在文化傳承的語境下,該如何保持城鎮的經濟活力與生命力?
今城靖港、喬口
選擇理由:與邊遠湘西的邊城茶峒、裡耶相對應,作為參照物的靖港、喬口,地處長沙市望城區,在大都市的裹挾之下,觀察它們如何自處,如何圖存,如何發展,是一件很有意味的事。今城熱水
選擇理由:汝城縣熱水鎮,城鎮建設不盲目求大,而是注重功能,在傳承湘南民居建築風格的同時,嚴格控制城鎮建設尺度,更穩妥,也更理性。
對話專家
湖南大學建築學院院長、教授魏春雨解讀如何讓城市自然生長
牆根剝落,青苔已經褪盡。香爐山崖,清水江邊,褐紅的吊腳樓已經越度百年。
從山腰傾瀉,湍湍劃過湘黔,77公裡。湘西邊城茶峒(茶峒鎮已更名為邊城鎮),逶迤的清水江流,在這一灣歸於寧靜。
數十年前,清湛的江水漫盡黃土卵石壁,撐一支長篙的渡人,是鄰村的鄉人,是他縣的商販。
千帆萬樯終歸邊城茶峒。某一天某一刻,這一切戛然而止。這些碼頭、街道和它們所聚合的生活突然停滯,定格成了某種意義上的標本。
誰懂湘西邊城茶峒?亦如誰懂湘西之裡耶、王村、浦市。在現代的都城前,在高樓鱗次栉比下,帶著滾滾煙塵的吊腳樓、河岸碼頭、烏篷船,看上去一副灰頭土臉的樣子。但它們卻是一個個從遠古演化而來並存留至今的鮮活的城鎮細胞,是一個個刻著經濟、文化、地理、民俗印跡的歷史切片。
每一座古鎮都有自己的文化因子,每一座古鎮都有自己的建築特色。這些文化因子如何融入建築,又如何演化,如何流變,對於今天的我們,需要破譯,需要解讀。
而古鎮的命運,那些深宅大院,那些青瓦木房,是歸於湮沒,還是超拔重生,是出給我們,以及後人們的一道凝重的選擇題。
正在蛻變的邊城
劃過一個山岬,清水江悄悄湍開了碩大的口子,溪流直徑被放大5倍。
拾階上香爐山,站在山巅俯覽,才會清楚地看到邊城茶峒的全貌。三面是連綿起伏的黛色青山,三山環繞的平原,就是邊城茶峒。
清水江帶來了第一批商客,誕生了第一個水碼頭,聚集起了第一個集市,最後生出了一個集鎮。
邊城茶峒是從大江大河中生長出來的集鎮,緊靠碼頭,隨清水江的曲折而略有弧度的石板路,繁衍著世世代代的繁華。
但現在,整個邊城茶峒正在變成一個工地,老房子在整修,新房子在整建。邊城茶峒被割裂成兩種顏色,一種是時間沉澱下來的古老吊腳樓的褐紅色,一種是新房水泥砌瓷的淡淡的灰白色。
一條明確的線從東到西將這兩個世界分割開來。灰白的邊城茶峒是嶄新的,現代玻璃幕牆閃閃發光;褐紅的邊城茶峒是陳舊的,密密麻麻的吊腳樓,矮木房擁擠潮濕。這是邊城茶峒的年輪線。
上世紀八十年代,陸路興起,水運沒落,江岸被抬高十幾個台階。邊城茶峒,這座雙腳伸在清水江裡的集鎮,不得不從水中抽出身子,連連向後騰挪。
百年碼頭只剩下一個架子,吊腳樓孤獨眺望。2013年盛夏,香爐山下,邊城茶峒沿江拆棄待建的空地前,泥沙攪拌,煙塵沖起;空地旁,吊腳樓裡依然有晾著的五顏六色的衣服在飄,那是古鎮中堅守的人家。
“逼”出來的吊腳樓
邊城茶峒應該是一個得上天厚愛的地方。
人類學家說,沿江河和沿海平原、谷地最適合人類生存。這個以苗語命名的集鎮,譯作漢文即漢人居住的小塊平地。
清同治年間編撰的《永綏廳志》記載,這座小鎮“地處湘、川、黔三省之中,因古傳有兩戶漢人居此而得名”。
清朝乾隆年間該鎮設立“協台衙門”。以屯軍為主體的大量漢族移民遷入,墾殖開拓,形成苗漢土家雜居格局。
20世紀30年代中葉,邊城茶峒因沈從文的小說《邊城》聲名鵲起。
在以江河為主要商貿軌跡的往昔時月,因為清水江,邊城茶峒串聯起川渝湘黔。清水江給邊城茶峒帶來的是川貴的五倍子、青鹽、棉紗布匹,帶走的是邊城茶峒的桐油、藥材、雜貨。這幾樣東西支撐起邊城茶峒百余年的富庶。
在老茶峒人的記憶裡,邊城茶峒最繁華的地方曾經就是臨水的街道。因為聚居,沿江的邊城茶峒多是二、三層樓高的吊腳樓。
臨河而建,講究亮腳(即柱子要直要長),屋頂講究飛檐走角。這種獨具民族特色的建築形式,據考證緣於歷代朝廷對苗族、土家族實行屯兵鎮壓政策。
《舊唐書》說:“土氣多瘴疠,山有毒草及沙蛩蝮蛇。”相傳彼時土、苗兩族人多被趕至深山老林居住,由於多毒蛇野獸,加上少田少地,只好修築吊腳樓。吊腳樓下安放碓、磨,堆放柴草;中樓堆放糧食、農具;上樓為姑娘樓,是姑娘繡花、做鞋、讀書寫字的地方。
莫鳳祿從祖輩起,便生活在邊城茶峒,承襲五代。上世紀供職“供銷社”,現在“嚴守誠信經商”經營著沿江老宅的一間雜貨鋪。這位每天閱讀大量報刊書籍的七旬老人,“出生便生活在這屋子裡”。
房子是三層樓的木結構,陳舊的木地板,黑黑的屋頂,堂屋後面是天井、裡屋、陽台。陽台外面就是蜿蜒而下的清水江。背著手,走在堂屋,莫鳳祿跺跺腳示意“全是木頭的”;走進天井,他指著一道約3米高的厚牆說,“這是後來才隔的,另一邊分給侄子了,以前這塊兒可大,兩邊的屋室是門對門,對稱的。”
江上的勁風從窗口灌入,滌蕩整個屋子,水大的時候,就會淹沒房屋下層的石壁。老屋和它的主人就是清水江的一個伴兒,已經相望百年。
老民居PK城市公園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學者、沈從文次子沈虎雛的眼裡,邊城茶峒並非一座普通的古鎮。每一座吊腳樓,每一處河岸碼頭,都承載著邊城茶峒百余年的歷史,是活著的古城鎮印跡。
“小城依山而築,一色青磚黑瓦的民居,從山腰延伸下來直奔河邊,一些仿佛剎不住車的房子沖到河面上去,用無數的木柱支撐著,成了半懸岸邊的吊腳樓。”沈虎雛追憶,“1994年我第一次來時,臨江的吊腳樓從屋頂到支柱,覆蓋著青苔。”
狹窄的石板街道,雕花的欄桿、窗棂依舊記載著邊城茶峒的繁華。然而,這座遠離主流文化中心的偏僻山鎮,邊地的角色注定了它被動發展的宿命。每一輪經濟浪潮的興起,它都會因外來文明的湧入而繁華,爾後又因環境的閉塞導致交流的滯後而重歸平靜。
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一天,停泊在清水江岸邊的數十條商貿船一一消散。
陸路興起,水運沒落,邊城茶峒,這座曾因水運興盛湧出大山深處的古老小鎮,再次因為水運的沒落,被湮入浩蕩青山深處。
上世紀九十年代,曾經清湛的清水江流因錳礦開采,污染嚴重;二十一世紀初,應“山區縣城,都市標准”的地方政府要求,邊城茶峒效仿打造城市公園,古樸的吊腳樓被遺忘擱置。
穿省道,越山路,從湘西另一集鎮裡耶入邊城茶峒。道路的兩廂十余棟民居前,鋼架支立,塵沙灰蒙。在歷經了“文革”陣痛、礦產開發污染後,這座湘西隅的小鎮試圖拾回“書裡邊城”模樣。
據當地風景管理處相關負責人介紹,2006年,邊城茶峒古碼頭入選第八批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同年花垣縣政府出台《邊城茶峒申報國家歷史文化名鎮實施方案》。與古城保護一同進行的,還有一場關於古鎮氣質和經濟活力的重塑發展旅游業,整修新房,興修景區大道,建賓館、停車場。
2012年3月,吉茶高速通車,邊城茶峒旅游開發速度也因此從“省道”的60碼時速,切換到高速公路120碼。
從全國甚至世界各地的游客,因為交通的通達,開始聚集邊城茶峒。6月20日清晨,清水江邊,從重慶過來游玩的王湘毓(音)向記者坦露,“許多老民居已被圍禁入內,大概是在整修,新修房屋的外立面正在包上‘木框’,但終究是水泥房子,沒有濃郁的民族氣息。”
兩座大院的堅守與維新
在厚重復雜的城鎮經濟發展前,“文化存根”往往被誤為矯情的呻吟。但縱其作為社會運行的平衡,也需要一種共識維護城市記憶和遺存,以保全其獨特基因,區別他城。
在邊城茶峒規劃面積6平方公裡的“書裡邊城”景區緊張籌劃與整修的同時,百余公裡外,龍山縣委縣政府會議室正就湘西古鎮裡耶的保護與開發工作展開緊鑼密鼓的商討。
這座曾經繁極一時的古樸小鎮,如今正面臨一眾古鎮一般的境遇在現代經濟浪潮中,在繁復的經濟需求前,如何存護其特有的文化、存留其特色。
清朝到民國至抗日戰爭期間,這個土家族聚居的小鎮成規模有名號的經商戶420戶,巨富商賈20家。其中,“李同發商號”是當時湘鄂川黔邊區第一大商號。輾轉70余年,記載李同發家族榮光的卻遠不止於一道以其命名的街道。李同發巷“同興恆花紗皮布”商號前,25歲的裡耶旅游向導吳婧指著商號二樓高高的拱門告訴記者,“裡耶古街區大多的建築都是明後清初及民國時期的,幾乎都是木屋青瓦,極具土家族特色的建築,只李同發一家區別其他。”
她指的是,“同興恆花紗皮布”商號二樓已跳脫當時“壓低的屋檐、莊重的木欄”的民居格局白色牆壁,高高的圓拱形,屋內也由間隔的小區間,轉換成寬大的通間。吳婧說,“這是李老從上海回來後,責令修葺的,大城市時尚的元素被搬到了湘西小鎮。”
而有意思的是,與“李同發商號”相隔兩個街巷,當地文化世家“瞿家大院”,建築造型是典型土家族特色,南方宗祠建築、莊園建築、民居建築三合一體。
不管是堅守傳統,抑或是繼承發揚,這兩座大院都張揚著自己的特色,並且互不沖突,和諧共存。
有數據統計,裡耶古街區現存較好的民居510棟,1310間,建築面積21940平方米,這些民居依舊保留了明清建築風格和土家族傳統的建築特色。
呵護古鎮最後的碎片
傍晚的裡耶,陽光已經退去。沿江兩排木房之間是狹窄的石板街道,白發老人倚門而坐,小孩當街光著屁股洗澡,擔著擔子的小販靜靜地走過街道。
如今的裡耶,在王澤君的畫本上是一個側躺著的“白”字形。跨過裡耶大橋,現代建築構架成的“長沙街”是“白”字的一撇;2002年挖掘並被保護的裡耶“秦朝古城”是其中一個“口”;形成於明末清初,並最終於民國時期發轫的“裡耶古街區”,則是另一個“口”。
這個“結三五伴,隨意畫畫看看”的常德男人,一路走過洪安、浦市、邊城茶峒,對裡耶有“時空的驚詫之感”。
夯實的城牆,清澈的護城河,古樸的黃土街道,高高的吊橋,是兩千年前秦朝的裡耶;窗棂雕花,青瓦林立,窄窄的門臉後,有寬大的空間,是兩百年前,明清的裡耶。
據裡耶管委會主任彭紹興介紹,長達十余年的時間裡,當地政府曾邀約多方的專家學者、機構,考察、研討裡耶的未來規劃和發展方向。“從2002年發現地下秦城至今,政府對裡耶古鎮的開發工作一直十分謹慎,她是一塊躲進時間裡的瑰寶,但我們不敢輕易雕飾。”
一如一眾專家的言論,在城鎮進化的浪潮中,文明發展既是一個趨同的過程,又是一場求異的抵抗。恰如邊城茶峒、裡耶此般的文明類型,無疑是彌足珍貴的,然而僅僅要求其堅守歷史,似乎並不現實。在他們看來,關鍵的問題在於強勢的後現代文明如何善待歷史,為其支付成本;如何運行一種科學的全面統籌的觀念,避免整個城鎮陷入功利泥沼,存續一種共識維護城市記憶和遺存。
- 上一頁:宏村的古建築保護
- 下一頁:南通博物苑:中國首所公共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