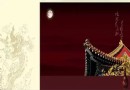從琱生三器銘文看西周的貪賄狀況
日期:2016/12/15 0:29:43 編輯:古代建築史2006年11月,在陝西省扶風出土一批窖藏青銅器,在其中兩件被命名為“琱生尊”(命名尚有其它)的有長篇銘文,這和1959年由張少銘先生捐贈國家博物館的“六年琱生簋”銘文以及現存於美國耶魯大學博物館的“五年琱生簋”銘文敘述的是同一件事,不同的是“五年琱生簋”銘文敘述的是事件的起始,“琱生尊”敘述的是事件的進展,而“六年琱生簋”銘文敘述的是事件的結果。
《琱生五年簋》釋文(略),譯文:周厲王五年正月乙丑日,琱生有事(為官府清查止公多占公田僕庸事)。召伯虎(厲王時重臣,後又輔佐宣王)來參與審理此一侵占公田僕庸案。(琱生告訴召伯虎說,)我給您的母親婦氏贈送了一個珍貴的禮器壺,請她出面說情,我請她擬你父親君氏的口氣對你說:“我老了,止公侵占國家僕庸土田的事,受到司法機關多方偵訊。希望你能從寬處理:如果止公侵占的超額三份,你就設法說成超占二份;如果止公超占二份,你就設法說成超占一份。”(你父母許諾後),我贈送給你父君氏一個大璋,又給你母婦氏贈送了一束帛和一塊禮器璜。召伯虎說:“我已經向群臣征訊過意見了,對案情有所了解。但是,我要服從我父母的命令,我不敢按大臣們的意見處理。我要重新給大臣們傳達我父母的命令。”琱生又給召伯虎贈送禮器玉瑾以作酬謝。(引自馮卓慧《先秦文獻看西周的民事訴訟制度》,下同)
《琱生五年尊》釋文(略),譯文:周厲王五年九月初一,召公之妻姜氏因為琱生送來五锊壺一對,便以宗君的命令說:“我老了,止公是我們的人,他的奴僕附庸土田的占有,受到國家多次偵訊調查。(你)一定要允許他的土田附庸占有不要變化散亡。(如)我們多超額占有三份,你就說占有二份。止公他贈送給我朱紅色的朝觐禮品大章,又給宗婦酬報一束帛,一塊貴重的玉璜,給調查此事的官員和益兩份休閒禮品。琱生因此頌揚我的宗君的美德,因此制作了召公尊,用以祈禱上蒼保佑召伯虎的官錄,使其能保全永終。(此尊)召氏子孫永遠保存作祭祀之用。那些敢不遵守或變亂這個命令的,我說你們的史召人的公就會有明確的法則的。”
五年琱生尊銘文
《琱生六年簋》釋文(略),譯文:周厲王六年四月甲子日,周王在宮,復審在周王在場時進行。(審後),召伯虎來告訴琱生:“我向你報告好消息來了!”召伯虎說:“止公繳納了訴訟費。止公繳納那些訴訟費,都是為琱生你打官司的。這場官司總算有了著落而平息了。官司能夠平息,也都是因為我父母幽伯幽姜出面說了話。我祝賀你啊!我要就止公的僕庸土田的事再次訊問有司們的意見。我雖然有了登錄那些田土的文書,因為還未征訊有司的意見,所以不敢將它們封存於官府。現在我已經征訊過有司的意見了,他們說:“服從幽伯幽姜的命令!”現在我已經把那些僕庸土田之外的土地都一一登記了,把它們送給你。”(因為召伯虎將公田被占為私田的所有權證書給了琱生),琱生又給召伯虎送了玉璧以作報答。
六年琱生簋
六年琱生簋銘文
三篇銘文記述了西周貴族琱生家族因大量開發私田及超額收養奴僕引起民事訴訟。負責調查此案件的官員是召與琱生同宗伯虎,召伯虎的父還是該宗的宗君。於是,琱生先後送給召伯虎及其父母許多財物,如青銅壺、玉璋、玉璜、玉璧、帛等,召伯虎的母親便向召伯虎轉達其父的意思,要求召伯虎看在同宗的分上,就按琱生的意思去辦理,最後的結果琱生如願以償,便鑄造了記載這一事件的簋和尊,希望子子孫孫萬年珍貴地使用,讓它在宗廟裡祭享。
關於琱生三器銘文的記載是否說明了琱生和召伯虎之間存在行受賄的行為,這在學術界一直都是有爭議。多數意見認為,琱生和召伯虎之間是“禮尚往來”,是西周時期“禮”的表現形式,並不存在行受賄行為。我認為即使把琱生和召伯虎之間的行為放在西周時期法律框架內和語境中,也是禁止和受處罰的。而如果以現代法制德標准,從歷史的發展軌跡中縱向探究貪賄的脈絡,就更是一起很典型的行受賄行為了。
從琱生三器的銘文記載,我們今天以一斑窺全豹,依稀看得出西周時期貪賄的一些狀況和特點:
一、西周時期貪賄現象已經普遍存在,並且在一定程度上公開化。有關貪賄何時在中國出現,眾說紛纭:始於“漢時”(見顧炎武《日知錄集釋》卷十三《除貪》);“西周時已有貪污受賄的記載”(見劉澤華、王蘭仲《論古代中國社會中的貪污》,載《天津社會科學》1988年第3期);自“殷商以降,跟著私有財產制度和階級國家的成立,貪污遂成為統治階級的職業”(見翦伯贊《貪污列傳序》,載《新華日報》1945年9月2日);貪官大約在原始社會晚期堯舜時期即產生,迄今已有五千年的歷史了(見周懷宇《貪官傳》序)。以上觀點中,除了早期的顧炎武外,後期學者一般認為貪賄的出現都在西周或者西周之前。從琱生三器的銘文中也可以看出:其一、琱生家族多占公田,在現代語境中,應該屬於貪污;其二、琱生為了讓自己家族的貪污行為不受懲處並且能繼續占有,向負責此案官員召伯虎的父母多次行賄,召伯虎最後也遵父命,做出了有利於琱生的判決。更重要的是琱生三器的記載還揭示了西周時期的貪賄在一定程度上還具有公開化的特點。琱生明目張膽,無所顧忌地多占公田;琱生的行賄也大大方方,一而再地向召伯虎父母行賄,並且在行賄時將自己所要達到的目的表述的清清楚楚;琱生甚至不但不隱瞞自己的行賄行為,反而而將自己行賄的原因、過程和結果刻在器物上,讓子子孫孫銘記。
另《左傳·昭公十四年》有“貪以敗官為墨”,《詩經·大雅·桑柔》中也有“貪人敗類”的記載。因此,以禮治國的西周貪賄並無絕跡,而是普遍甚至公開存在,難怪後來連孔子都說:“禮崩樂壞”。
二、以“禮”為基礎的宗法制嚴重干擾司法,貪賄行為影響司法裁決。“禮”中國古代社會中長期存在的、維護血緣宗法關系和宗法等級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則及言行規范的總稱。一般來說,禮具有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抽象的精神原則,主要是親親、尊尊;二是具體的禮儀,主要有吉禮、凶禮、軍禮、賓禮、嘉禮。西周時期的“禮”,也就是周禮,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法的性質和作用,但和法又有區別。禮與刑是西周法律體系不可分割的兩個組成部分,共同構成完整的法律體系,禮主要是法理學層面的規定,是一種積極的規范,正面、積極地規范人們。而法的具體規定則體現在刑上,處於消極被動狀態,對一切違禮行為進行處罰。“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一般情況下,庶人不受禮的約束,而貴族犯罪也不受法律制裁。
西周時期,以禮為基礎,在家庭內部為區分親疏關系,對源於父系氏族家長制,進行加工和改進,逐漸形成了宗法制,其核心是嫡長子繼承制。在宗法制下,屬於同一原始血緣的後代被分為大宗和小宗兩支系,大宗就是始祖之下的嫡長子及嫡長子系,嫡長子又稱宗子,在同一代中,其余的諸子又稱庶子,在小宗中也有大宗小宗之分。宗法制的目的是在家族內部確立地位、財產的繼承權,大宗在家族內部因繼承了地位和份額較多的財產,所以受到庶宗的敬奉,即所謂的“尊祖敬宗”,反過來,大宗又有保護小宗的職責和義務。
聯系到琱生三器的記載,就可以看出:第一、召伯虎為琱生家族開脫罪責,既有其父母收受了琱生的貴重器物,受人錢財,替人消災緣故,同時也和宗法制度是分不開的。召伯虎和琱生為同宗,並且其父君氏為該族的宗君,而琱生是其宗族的支系,屬小宗。因受賄而枉法裁判的行為被視為是宗族內部的事,是大宗有保護小宗的職責和義務。西周時期的行受賄行為以及徇私枉法可以以禮的形式存在,並以禮的名義進行,雖然這種在形式上符合周禮,但是在內容上卻嚴重違背了周禮的精神實質。第二、召伯虎父母收受賄賂以及召伯虎徇私枉法的行為,是違犯西周法律的。《尚書·呂刑》:“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於五刑。五刑不簡,正於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意思是“原告和被告都來齊了,法官就審查五刑的訟辭;如果訟辭核實可信,就用五刑來處理。如果用五刑處理不能核實,就用五罰來處理;如果用五罰處理也不可從,就用五過來處理。”而“五過”的具體內容是(1)“惟官”,指畏權勢而枉法;(2)“惟反”指報私怨而枉法;(3)“惟內”,是指為親屬裙帶而徇私;(4)“惟貨”指貪贓受賄而枉法;(5)“惟來”,指受私人請托而枉法。凡此五者出入人罪,皆以其罪罪之。而宗君在兩次給其子召伯虎的指示中之所以態度很明確地要包庇止公,是因為他知道這對於自己和兒子的名譽前程等都不受影響。宗法制受西周八辟之法保護。《周禮·秋官·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八辟即後世的八議之法,八種有特權之人享受的司法特權,所謂“刑不上大夫”。另外,召伯虎任高官,也是可享受司法保護特權的。第三、在西周實行分封制的情況下,諸侯若多侵占公田僕庸,便會使周王室收入減少,直接影響王室的利益,故而,琱生家族的行為受到王室高級官員司徒、司馬等多次的稽察,甚至在最後“定案”時,周厲王也親自到場。而即使在和王室利益直接沖突的情況下,召伯虎也不顧一切,依然做出了有利於琱生的判決,宗法干擾司法,貪賄影響司法的情況可見一斑。
三、西周時期的貪官也具有兩面性的特點。召伯虎,從琱生三器的銘文看,是一個受賄且又徇私枉法的官員,這是不爭的事實。但是,在琱生三器未出土前,他的形象卻又是另一個樣子。琱生三器記載的是周厲王五年、六年的事,而我們根據其它記載,看看二十多年後,召伯虎又是怎麼說怎麼做的。
《史記索隱》中記載,召伯虎是西周初周初重臣召公奭之後裔,是留守在岐山故地的一支,世代襲召公之位,在周王室任要職。《史記·周本紀》有載:“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召公谏日:‘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其謗鮮矣,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水。水雍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水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於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這段記載說的是周厲王實行暴政,召伯虎在當時已是重臣,居二相之一,直谏厲王而厲王不聽,導致國人暴動圍攻王宮時,又將太子靖藏在自己家中,以自己的親生兒子替太子死。厲王死後,他擁立太子即位,為周宣王。說明周厲王是實行與民爭利、貪財又高壓百姓之人,導致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共和行政”。這共和行政的二相之一就是召伯虎,也稱召穆公虎。其中“防民之口,甚於防水(川)”幾乎成為千古不朽的廉政經典。
還是這個召伯虎,後來在《詩經·大雅·江漢》有記載,他平定了周王朝的內亂,又率軍隊戰勝和臣服了入侵的淮夷,使周王室的疆域達於南海,國內統治安定。周宣王因此親自到召公奭最初的封地岐周,對召伯虎封賜了山川土田,以“召公”的爵位再封賜給他,讓他繼承。這次封賜,周宣王以對召伯虎先祖召公奭封賜為召康公的高等禮儀對待之。由此可知,召伯虎在周宣王時已上升至“公”一級地位,是主持朝政的主要人物,可以稱得上功著彪煥了,所以史記及其它後世文獻也將他稱為召穆公虎。
現在,可以看出來一個完整豐滿的召伯虎的形象了,一方面,他舉著“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大旗,在歷史典籍中以一個正派人物的形象受到尊重和敬仰,另一方面,琱生三器的銘文卻記載了他辦理琱生一案時收受賄賂,徇私枉法的行為,完全是站在了自己歷史形象的反面。今天,我們再探究召伯虎的行為在當時是否合法,已經沒有意義。縱觀中華民族的歷史,也許召伯虎的行為正是貪賄行為源頭上的一滴,他矛盾而又豐滿的形象,具有很強的被繼承性,時至現代文明制度包裝下的今天,依然被一次又一次地復制著。
(文章來源:陝西省文物局漢唐網2015年8月21日)
- 上一頁:科普帖:中日古建築之不同
- 下一頁:咬文嚼字:考古發掘與考古挖掘
-
没有相关古代建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