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故園:十年朝聖路
日期:2016/12/13 20:11:43 編輯:古建築紀錄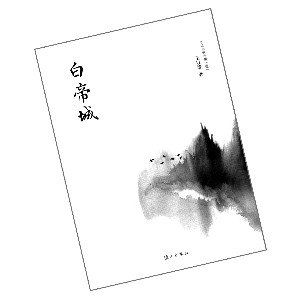
看到王以培,覺得他將隨時遠行。身材高大,背著雙肩包,走起路來健步如飛;沿途采撷,意興盎然。無論到哪裡,他都會帶著一個羊皮殼的小本子。那裡是古鎮的手記:有始龀兒童幼稚的字跡,有耄耋老人顫抖的筆墨。那更是古鎮的隨想錄,記錄了他游訪長江古鎮的所觀所感,點點滴滴。十余年,他在古鎮間游訪,一刻不止。
讀到王以培,覺得他又從未離開。十年游走心系故園,他沒有停止腳步,但似乎又從未走遠。他始終身系大地,始終沒有離開長江這支維系古今的文化命脈,始終沒有離開心靈這處始終純潔與忠誠的所在。
在這套《長江邊的古鎮》之一《江有汜》中,王以培寫道:“我只想這麼一直走下去,不想在哪兒下船,又想在每一站都下去看看。”這是個融進滔滔江流的生命,這是個化入文化長河的靈魂。他慶幸自己喝長江水長大,獲得潔淨的靈魂。冥冥之中,一種力量牽引著他,沿江而行,尋訪古跡。或許,是自己在江邊丟失了什麼;或許,他想提醒古鎮的人,不要丟了什麼東西。於是,就這樣走走停停;白天尋訪,晚上寫字,與江風一起度過幾萬個日日夜夜。
早些年,王以培曾游歷歐洲各國。一日,他來到意大利龐貝古城,在維蘇威火山下,他似乎窺見當年古城的煊赫盛象。恍然間,他頓悟覺醒:這裡曾被火山掩埋;我的故園,長江三峽的古鎮家園,也即將被上漲的江水淹沒。生於南京的王以培,胸中的長江血脈瞬間奔湧起來:我必須回去,記錄現實、歷史,為民族做一點貢獻。2001年,王以培歸國。這十余年,他再沒有去別處,只在長江邊上朝聖,並記錄長江的每一次奔流,每一聲咆哮。他把這千年古鎮,稱作“家裡”。
十余年,他從魚嘴到木洞,從萬州到新田,從白水溪到白帝城,一直沒有停歇,走得滿面風塵。他與漁民們一起登船,與鄉親們一起睡棚屋。他熟悉古鎮的每一個角落,沒有落下任何一個音符,甚至清晰地聽聞到,日夜驅馳的長江,在夜涼如水的小鎮上,一絲絲的嗚咽。白天,他與古鎮人們同行;晚上,就獨自記錄古鎮的點點滴滴,與古鎮夜談,與心中的故園,心中的理想,促膝而談,仿若如鄰。
不僅足跡遍布三峽的幾十個古鎮,關懷故園的心靈,也留在鎮上,每一個有知的生命間、無語的靈魂裡。見到王以培時,他剛剛從三峽回來,發須依稀還挾裹著穿越千年古鎮的風塵。他把長江古鎮稱為“聖地”,而自己,則是常年朝拜的聖徒。因為所謂“聖地”,就是信仰的依托,心靈的歸屬,永恆的故鄉;而在長江岸邊,那些沉入江底的家園,古鎮村落,煙雨樓台,親人墓地,正是王以培畢生所求的聖地、信仰和根基。他為找到這塊聖地而深感幸運。
盡管寫了十二年,王以培並不以此自足。記錄古鎮,思接千載,尋找家園,追回信仰,似乎已經融入他的生命,流進他的血液。“想記錄淹沒區的歷史文化,十二年實在太匆忙,太短暫;但相對於我個人而言,還是卓有成效的,它幫助我找回了失去的信仰,心靈的家園。”
王以培的筆觸是出離憂郁的,甚至是敏感而又焦慮的。故園已逝,他無法掩飾心中的留戀和憂傷。古鎮的人們,未來何去何從?抹去了古鎮的長江,千年文明又將奔向何方?長江在日日常新,長江又將日日堅守。
王國維談作詞,境界一說頗受稱道:“詩人對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入乎其內,故有生氣;出乎其外,故有高致。入乎其內,故能觀之;出乎其外,故能寫之。而眼下這套《長江邊的古鎮》,王以培走訪長江古鎮十余年,觀之思之,訪之念之,心血之作。他徒步丈量千年古鎮的歷史坐標,生意盎然。他身在古鎮,心系故園,理想的高致,也穿越風雨。而不管是入乎宇宙人生之內,還是出乎宇宙人生之外,最終都是為了融入宇宙,回歸人生。王以培深刻認識到了這一點:“與長江命脈相依相存的人和物,離開長江命脈,尋找發展的人,最終還是要回歸。”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長江邊的古鎮》 王以培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