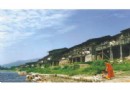張家灣古鎮加裝攝像頭 曾被稱“運河第一碼頭”
日期:2016/12/13 22:40:12 編輯:古建築紀錄新京報訊 作為京杭大運河曾經的漕運終點,張家灣鎮雖曾被稱為京杭大運河漕運的“第一碼頭”,今年卻暫未與萬寧橋、東不壓橋及通惠河、玉河故道等一起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不過,近日新京報記者從北京市文物局相關部門了解到,現在通州區仍然通過加裝攝像頭、與環衛部門溝通清理環境等方式,加強了對張家灣古鎮的保護整治工作。
漕運歷史可上溯至東漢時期
張家灣古鎮在通州城區東南5公裡處,其漕運歷史可上溯至東漢時期。遼金之後,隨著北京成為全國政治中心和運河的開挖,張家灣地區的經濟也日益興盛。特別是明朝永樂時開始大規模建造北京城後,通惠河水勢的淺澀使張家灣鎮成為了運河漕運的終點。
從運往京城的糧食物資,再到建城所需的城磚,以及紫禁城、十三陵所需的木料,都要在此處卸船暫存,再由陸路轉運至京城,所以這裡曾被稱作京杭運大河漕運的“第一碼頭”,現在周邊的皇木廠、磚廠村等,都曾是當年的貨倉。
通運橋面將定期清掃
2012年,北京市文物局公布《大運河遺產(北京段)保護規劃》時,就曾將張家灣鎮及其城牆列入其中,要求進行修繕保護。
而今年6月,大運河首批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兩遺產點、兩河段公布時,張家灣鎮未被列入。7月,新京報記者探訪張家灣鎮遺址時,一切似乎如昨,有村民表示,雖然“申遺”的過程讓更多人明白了城牆及通運橋的文物價值,但並未對生活產生實際影響。
對於“後申遺時代”張家灣鎮的保護情況,近日,北京市文物局相關負責人表示,通州區已經對通運橋及張家灣城牆遺跡采取了一定的保護措施,對保護標志碑進行了維護和基礎加固,並在通運橋南側加裝攝像頭,對文物進行24小時間監控,確保文物本體安全。
同時,該負責人介紹,張家灣鎮政府已與當地環衛部門協調,對通運橋周邊環境進行清理,並派專人定期對橋面進行清掃,指定專人對文物及周邊環境進行看護,加強管理,確保文物及周邊環境整潔。對於張家灣城牆遺跡保護整治工作,目前也正在編制方案。
■ 探訪
“申遺”中村民自發看護遺產
近日,新京報記者探訪通運橋及其周邊時看到,張家灣鎮城牆已經被重新修葺過,橋面石板上還有深淺的車轍印,城牆內則是一片荒地,僅剩黃土雜草。
今年65歲的村民王理(化名)在蕭太後河邊長大,他還記得幼年時下河游泳、魚群圍繞在身邊的場景。他很清楚這條河的由來,“不是大運河,是運糧河。”王理指著家對面的張家灣鎮城牆遺址說,當年牆內是皇家倉庫,稱作“鎮”,牆外則隨著運河碼頭而形成了“村”,名稱由來則是因為最早主持此處碼頭的官員姓張。
橫跨“鎮”“村”之間的,則是一座三孔石橋——通運橋,“400多年了。”王理說,這座橋一直供車輛行人通行,有幾年還在橋面覆蓋了瀝青。
隨著運河申遺規劃的實施,通雲橋的修繕也被提上日程。王理曾見證橋面的瀝青再次被扒開,顯露出留著車轍印的石板。“聽說有開發商想投資。”王理說,投資不了了之,建設也就再無動靜。
近年來的申遺也沒對村民的生活造成什麼影響,除了村民真正意識到,自家門前的那座石橋真的是文物,“看到有可疑的人在附近徘徊會很警覺。”王理說,近年來,通運橋護欄石獅丟失的情況少多了,“丟了的也補上了。”新補的石獅泛著青色,與發黃的“原配”相比一眼便可辨明。
7月,王理在河邊看到有人為橋和城牆安裝了攝像頭,“可能跟遺產點有關。”王理說,但願申遺能夠把這條河變得更好。
■ 追訪
申遺點將分批添加
北京市文物局原局長孔繁峙曾回憶,為了保護運河,通州在規劃城市新區開發建設方案時,都讓建築盡可能地遠離河道,把綠地放在河岸邊。盡管今年“落選”,但通州的諸多運河遺跡點,仍有機會今後分批申遺。
據北京市文物局相關負責人介紹,申遺總體原則是“整體保護,分段申遺”,即本次公布的只是第一批列入名單的遺產點段,今後根據其他遺產點的整治保護情況,還會將新的遺產點公布。
北京市文物局文保處處長王玉偉曾表示,隨著其他申遺點或遺跡點的修繕與保護,無論北京市還是世界遺產目錄,都會增加。“最重要的是轉換思路。”中國文物學會會長、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霁翔認為,對於即將申遺的遺址來說,需要認識到,申遺只是目標,不是目的,“要把承載著中華文明的古老遺產,傳向未來。”
大運河北京段首批申遺成功後,市文物局和通州文委也均表示,將繼續推動通州運河遺跡的修繕。此外,還會進一步改善朝陽、通州段的水質。運河的申遺和保護點,都將繼續增加。
■ 觀點
申遺成果需惠及民眾
“文化遺產保護成果必須惠及民眾。”中國文物學會會長、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霁翔認為,要通過申遺、保護遺產,提高遺產地人民的生活質量,將遺產保護與遺產地人民的切身利益聯系起來。也只有這樣,人們真正認為遺產是有用的,才會更珍愛它,更保護它,“真正融入人們生活的遺產,才能得到更好的保護。”
大運河作為典型的線型文化遺產廊道,其“線性”特征決定了遺產保護是一項龐大的工程,“包括河道、水系、航運、碼頭、船閘、歷史城鎮、街坊社區在內”,單霁翔認為,大運河以線狀或網狀格局均需串聯起極為豐富的文化遺產族群,都作為保護和申報的范疇。
其中,應將文化資源的保護置於首位,同時關注經濟功能的發揮和生態系統的維護,“使文化資源、經濟功能和生態環境三者並舉。”他說。
一邊是高樓大廈平地起,車水馬龍穿行不休;另一邊是喧囂中的古河古閘,為保原貌而提出的限行限高,文保與發展的沖突看似不可避免。而玉河故道的修復和申遺成功,或許可以作為一個案例,“說明文保和城市發展並不矛盾。”王玉偉曾反復介紹,緊鄰南鑼鼓巷的玉河遺址既保留了原貌,又為附近居民的生活提供了良好的環境。
采寫 新京報記者 黃穎 實習生 李丹
- 上一頁:江蘇:走進古鎮民宿,品味“不一樣的周莊”
- 下一頁:湖州:太湖之濱的璀璨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