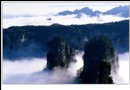杜鵑園:圓明園唯一幸存古建築
日期:2016/12/14 13:31:57 編輯:古建園林 北京,今冬的第一場雪早早到來,據說是四十年來同期罕見的一場大雪,生活在南方的我在北京遇見了她。
雪後初晴,我一個人來到了圓明園。一些雪被掃去,堆積在桑樹柳樹槐樹下,高高地壘著;一些雪匍匐在湖岸邊、小山上;一些鳥雀在雪地上飛起又落、跳躍覓食,喜鵲在樹上叽叽喳喳地不停叫著,偶爾有烏鴉突然飛起,呱呱呱地掠過湛藍的天空。有人在湖裡劃舟清理枯荷,有人用手推車拉走被雪壓折的樹枝。這麼大的一個園子,冷冷清清的,只是這無盡風騷柔婉的絛柳,一場雪後,依然翠綠滿樹,在福海之岸,在曲折迂回的流水邊。在這片大地廢墟上,唯數百年的樹木不老,唯有這流水不斷、湖水不竭,而圓明園之締造者只是史書一頁了。來到圓明園的正覺寺,據說這是唯一幸存下的一座古建築,在這兒,我看到了由清華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復原的這堪稱“萬園之園”時的勝景影像,那繁花滿枝的庭院,那結構繁復的精美建築,那流水琴聲、曲苑荷影,真似天上宮阙在人間,帝王行宮裡的雍容與奢華,縱然在百姓的夢裡也難以追尋。關於這園子的屈辱故事,盡是那三天三夜火燒不熄一樣講述不完,只是枉然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以為永遠不滅的大清帝國偉大心思構想,枉然了舉國百姓的血淚辛勞付出,枉然了千千萬萬能工巧匠的藝術和智慧,枉然了在大火裡冤死的三百多個太監和宮女。若這園子不毀,想來與故宮、頤和園一般,人民創造的成果最終要歸還給人民,如今再是卑賤之人也可堂而皇之進入高深的宮牆,在曾經的帝王行居之所自如散步。
僅百步之外,就是清華大學。1911年在圓明園之近春園內建造了清華學堂,而後,有了朱自清的散文名篇《荷塘月色》。我去過國子監,這個封建王朝的最高學府,之比圓明園,可是簡陋樸素了。1911年,這曾經的皇宮圓明園內,建造了一個學府,然後有了新文化(300336,股吧)、五四運動。不遠處,北京西郊香山頂上,白雪裡裹著紅葉,在陽光下光彩奪目。一度西山雪晴,一度花紅柳綠,香山腳下,舉家食粥酒常賒的曹雪芹用十年的心血成就了《紅樓夢》,據說,書中大觀園來源於江浙一帶園林,來源於這圓明園,姑母嫁給清王爺的曹雪芹有幸進入園子,有幸與祖父在江南度過美好的童年生活。我在香山一帶呆了兩天,呼吸那兒的雪後空氣,那兒可真的可以產生一些好的詩文來。雪後的香山,也是清靜的,全無了不見紅葉只見人頭的洶湧景象了。香山上,碧雲寺內孫中山的衣冠冢依然安好,古木森然;雙清別墅內毛澤東舊居依然安好,清泉汩汩流潺,一棵巨大的杏銀樹冠遮蓋了半個池塘,樹葉在斜陽裡閃著水一樣透明的金黃色光芒,令人陶醉;只是香山寺被英法聯軍洗劫了,走在空蕩蕩的大片廢墟上可以依稀感觸當年建築之宏大精美,看到這些,只有恨在心頭,到底要恨誰呢?細讀一部清史後,卻也理不清個所以然來;而每天,都有大量各色肌膚的歐洲人到這兒游覽,他們與我們一樣花十塊錢門票就進入了香山。在閩,歷史某個名人留下一個腳印、一筆墨痕,亦是彌足珍貴,寫進地方史志,引以為豪;而這燕山京都的地,皇城根兒,一不小心,留下的腳印就與一段重大的中國歷史重合了。
緩緩地,入園內的人多了些,老人居多,也有一些旅游小團隊,在風寒中舉著旗子引路,看西洋樓遺址公園,看那印在初中的美術教科書上一張熟悉的照片,那傷痛歷史記憶來源處。我沒去那兒,今年初已去過一回,只是想來,那兒已落滿了雪,亦是寒碜了。園內的雪,雪地上的絛柳、銀杏、桑樹,歷史過去了,只是它們卻留了下來;在南方,少見這巨大的樹種,這時節,無論站在園裡何處,與它們合影,都是一張絕美的風景畫像。相比一樣美麗如畫過於熱鬧的頤和園,我更樂意到這被帝王廢棄的圓明園來,靜靜地回想著:這歷史,這人世滄桑,這生活。
雪後圓明園,多麼清靜的一個大園子,大地一片白茫茫,真干淨。
推薦閱讀:
麗江木府 納西民族的“紫禁城”
泰國最奢華的宮殿—大皇宮(2)
泰國最奢華的宮殿—大皇宮(1)
泰國大皇宮
- 上一頁:尼泊爾巴德崗:震撼的中世紀王城
- 下一頁:泰國最奢華的宮殿—大皇宮(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