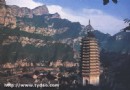站在黃絲橋古城的城門口聽小城故事
日期:2016/12/15 0:08:10 編輯:古代建築名稱
據光緒《鳳凰廳續志》中載:“鳳凰營,足巨鎮干鎮六十裡。有廢城,在坡山西址,建於唐,為渭陽廢縣故治。”這就是建於唐垂拱年間的渭陽城,雄踞湘黔要沖,在苗家人的注視裡已靜默屹立了一千多年。可手中握著的歷史資料所記載的此處風景與我眼前看到的這縱橫的阡陌,迂回的綠水,斜照的夕陽,縷縷的炊煙,卻有著天壤之別。這一派田園詩韻的古城,有誰會想到它曾是西通雲貴要塞的刀戟搏擊之地?
這已是我第二次敲開它巍峨的城門了,我對一個住在城內的老婆婆說我是來看望一位苗家姑娘的,問老婆婆可認得一對附近勾良苗寨賣刺繡的姐妹?老婆婆一邊說著好、認識,一邊又絮絮地向我道著她這片家園的歷史。她帶著我由屋後登上城牆,用手指著,告訴我說,有劇組曾在我們剛進來的那個門那裡拍過《烏龍山剿匪記》,還有近年拍攝的《我心飛翔》也在這裡取過景。她還說這裡的南門因為總是失火早被封死了,北邊的“日光門”只有家中有了喪事才由此門出人,東邊的“和育門”是當官人走的,逛過古城出東門,便能“官運亨通”了……
我不想再去深究那些飛檐翹角是從何時起變得不再雄偉壯觀,那些箭垛炮台又是因為何事曾經氣勢逼人,或者那些苔藓與野草塞滿的石頭城牆是否還殘存著已逝的足音。我問老婆婆:“現在這城牆還是不讓你們隨便上嗎?”她的歎息給了我肯定的答案。我知道這又是一片被旅游開發公司買斷的家園,他們自己的家園如今連上去隨意行走都變
得難以實現。老婆婆沒有再多說什麼,我卻知道古城心底的荒涼與淒冷,是無法同匆匆來又匆匆去的過客言喻的。

“春霞,春霞,有人找你!”老婆婆笑著把在別處看店的春霞領到我面前。“你是……”“你長大了。”這個當年穿著一身樸素苗服,手把手教我學繡花的十九歲姑娘,已蛻盡了滿臉稚氣,出落成不再穿苗服的成熟大姑娘了。春霞把她母親也叫了來為我介紹,她媽媽放下手中為鞋繡著花線的針,抬頭看了看我,又和女兒說了幾句苗話,便對我綻開了她鎖著的眉頭,露出了雪白的牙齒。古城沒有了初次見面那日的微雨,但我看到這眼前的人兒,卻清晰地記起那日微雨中我與春霞和她姐姐一同洗莴筍、淘米、炒菜、站著吃得很香的樣子。我說:“怎麼沒看到姐姐呀?”春霞說:“生孩子出血多,還在醫院住著。”我想像不出她清麗消瘦的姐姐懷孕後的模樣,我只隱隱約約覺得春霞和她姐姐可能永遠都不會再回到她們曾跟我描述過、我在照片中看過的美麗的勾良老家了。 在古城黑暗來臨前短暫的溫暖黃昏裡,我和春霞在一起,聽牛兒的牟牟聲,我贊揚她精致的繡花鞋,我們說到在鳳凰工作的比她大十歲的男友,一起整理貨物,挑水,上門板,換上漂亮衣服和她媽媽說再見,快樂地踩著影子出城門,在回鳳凰的班車上睡覺,遇到戴眼鏡的清瘦背包客,兩個姑娘在老房子吃飯,討論起她的婚期和婚前的失落,以及她如何守著黃絲橋上的稻草、雨季、杏花、燕子、糧食……若即若離且凌亂無序的古城故事,就這樣走人我夢中,變成了我永遠無法擺脫的情結。
到達:
先坐古城到汽車站的臨時班車,之後再換乘去往阿拉方向的班車。過了南方長城後有一段路正在修理中,不是很好走,塵土較大。大部分班車只到阿拉營,因此還需乘坐1公裡左右的三輪蹦蹦車。
游覽時間:
1-2小時。
旅游手記:
1、盡量不要購買城內出售的祖傳古玩器物,一千多年前遺存的文物,究竟有多少可以供當地人一批批地賣給游人,誰也不清楚。
2、黃絲橋古城不遠處還有個小苗寨,去裡面參觀無非也就是看看苗家男女表演的歌舞,學著跳跳竹竿舞,再拍一下漂亮的苗家姑娘罷了。
3.這裡的票價比較有意思,一邊是由旅游公司收購後的售票點,一邊是村民自己辦的渭陽花園的售票點,購買兩種不同的票的區別在於前者可以上古城牆,並且配有免費的講解員,而後者就只有由老鄉帶著站在自家屋頂上望望古城,如果要求老鄉帶你上 古城牆上去看看,那只得等正規售票點的工作人員不注意或他們下班後才可以,這一點對於外來的游客來說恐怕沒什麼大不了的,但對於本地的村民來說就不得不說是恥辱了。
- 上一頁:沉迷在喀斯特的奇幻勝景裡
- 下一頁:拜祭沈從文墓地,在儒者最後思索處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