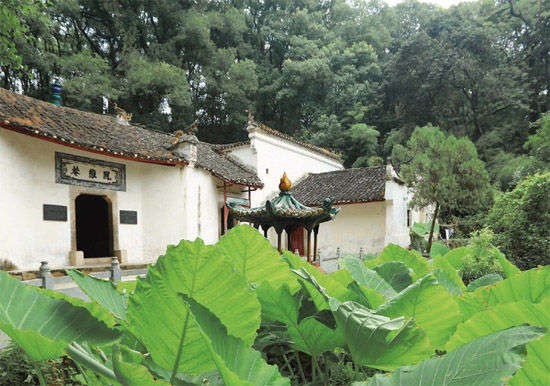荊棘銅駝:對洛陽古建的回憶
日期:2016/12/14 11:52:40 編輯:中國古代建築唐克揚
在《唐代的外來文明》一書中,美國漢學家謝弗(薛愛華)提到洛陽的時候是不一般的艷羨語氣:
“……與它西面的長安城相比,無論規模還是歷史都不相上下,但洛陽還有某種更為溫馨,更加高雅的精神生活氛圍……”
洛陽曾經是一座什麼樣的城市呢?我們在問這個問題的時候,大概已經忽略了一切具體的時間空間,忘記了百代的光陰是無法用一張地圖來描繪的。但是,人們在提到歷史上的偉大城市的時候,多半又都是如此的“印象派”,而且越是深刻的誤會,這理想中的城市便越是光彩奪目。日本室町時代以來,就一直流傳著因洛陽而得名的“洛中洛外”圖繪,那時代的絕大多數日本人從未來過中國,更不用說身臨其境地感受洛陽的繁盛,可是這並不妨礙他們在這樣的圖繪中,霧裡看花,把洛陽當成一切人間錦繡的最高象征。
中國文化的“理想城市”。
中國的“理想城市”也有自己的地形圖。最緊要處,是包容得下各種誤會和暧昧的“自然”,對於洛陽而言,是“花”和“塵”。陽春好景時的“洛陽花下”呼應著不那麼美妙的“衣袂京塵”,它們一起構成了中古中國城市最顯著的景觀,這景觀同時也是“自然”和“人工”的平局,是中國式人生的一對寓言。
“花”對於洛陽來客並不陌生。“洛陽之俗,大抵好花,春時,城中無貴賤皆插花, 雖負擔者亦然”(歐陽修《洛陽牡丹記》),直到今天依然如此。但是,今天的人們不太容易體會的,是拂看花客面而至的“紫陌紅塵”,它們隨著人情的漲落而同時隱現,讓古代的城市變得骯髒、困頓,並在城市的末日裡將它直接埋沒。它提醒著我們,繁盛的時間也對應著過往的苦惱人生,城市如同構成它們的建築材料,在建構、累積的同時也崩塌、污損,而萬古不變的自然將歡笑如初,通過這種對比,“自然”最終揭示和浮現了“人事”的有限。
和短暫的人類生命一樣,城市自有它們的生與死。對於有一類城市而言,“過去完成時”中不可見的過去才是它們對於當代歷史的意義所在。
“花之洛陽”永遠活在對上個春天的追憶中,我們所要講述的北魏洛陽的故事,也恰恰是從它的身後劫灰說起的。
公元547年,也就是哥特王托提拉洗劫羅馬的後一年,一個名喚楊衒之的北平人——此“北平”大概只是現在的河北郊縣吧——公差路過洛陽,這時候,昔日的洛陽卻正是在一片丘墟之中,先前由鮮卑人建立的北魏王朝已經土崩瓦解,連帶著它的都城也就灰飛煙滅。楊衒之依然不過是名小官吏,不過卻由效忠北魏,轉而隸屬它分裂出來的東魏朝廷。慨歎於這壯麗城市的結局,不禁悲從中來,他追懷往事的感喟,最終成就了一本獨特的“倒敘”的城市史:楊衒之記載北魏晚期都城洛陽勝概的《洛陽伽藍記》。對於中國歷史上的來者而言,這是一種綿延不絕的“追憶”傳統的開始。這種“城市追憶”的文體遠至《東京夢華錄》、《夢粱錄》,近至《春明夢余錄》和《鴻雪因緣圖記》。
楊衒之的聲音具有恆久的魔力,不僅是因為《洛陽伽藍記》“過去完成時”的敘述角度,而且還因為它同時應和著“預言”的前定:“將來完成時”的預言,和“過去完成時”的追憶仿佛兩面相對而立的鏡子,鏡子之中無窮折映出的是城市的宿命——“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
“將來完成時”設定於楊衒之時代的兩百多年前,依然是在這座城市的地盤上,有一位出身河西敦煌的著名書法家,已經准確地窺見了洛陽未來的命運——對於將文化當做只有面值而無價值的物品收藏的當代人,索靖的大名聯系著《出師頌》,是2003年拍出2200萬元人民幣高價的書法名作,對於歷史學家而言,索靖被記住卻是因為他1700余年之前的一句谶語:
“靖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荊棘中耳!’”(《晉書·索靖傳》)
“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循環律,為中國城市帶來了奇怪的喜劇和悲劇並存的傳統,或者是現實與它的最終結局間不祥的疊映——歷史時間在此不再是一根綿延的線,而是被壓縮成了一個黑洞般密度的點,通過“星際穿越”般的“蟲洞”,人們既可以站在未來打量現在,也可以立足於此刻,指點一座城市的不同的命運。
這預言可以是通往興盛的吉言——索靖的傳記至少還與另一樁有名的預言故事有關,但是這一次他強調的是“成”而非“壞”,“先時,靖行見姑臧城南石地,曰:‘此後當起宮殿。’至張駿,於其地立南城,起宗廟,建宮殿焉。”(《晉書·卷六十》)。但更多的時候,預言恐怕是不中聽的:在約700余年之後的歡宴上,大文學家蘇轼面對一座新建築的落成,就再次寫下了“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的斷詞(《凌虛台記》)——從新生兒的啼哭看到了千年後的白骨。
對一座城市結局的洞見不僅是政治預言,而且也是大多數中國歷史都市的事實,索靖的噩夢不過是其中一個富有魔力的“蟲洞”,而楊衒之面對的北魏洛陽的殘灰,也絕不是這座城市劫難的終了,在他身後,一座中國城市新的幻象就和它很快崛起的現實一樣飽滿了--那便是唱著“千年萬歲陽春曲”的隋唐東都洛陽。
在索靖的時代,盡管東漢末年董卓等人對於東都的破壞還歷歷在目,但後來者建設的規模、速度、能力均屬驚人,用不了多久,這時候的西晉首都洛陽已重又“宮室光明,阙庭神麗”,壯麗得讓人不相信它能被任何力量所毀壞了。
索靖不幸一語成谶,後來的歷史我們都知道,那就是“衣冠南渡”,它始自公元311年(晉懷帝永嘉年),劉淵、劉曜率領的南匈奴部攻陷和燒毀了一百年內再一次輝煌起來的洛陽。今天,大概沒有多少中國人敢說,這歷史事件與他們毫無關系,因為“永嘉之亂”從北方裹挾了大批的漢人南下,南渡政權在地方僑置的郡縣,給江南帶來了無數與北方有關的地名,類似北美殖民者那一串串的新約克,新奧爾良,新漢普什爾的命名……例如安徽和江蘇接界處的“當塗”,就是以北方懷遠的塗山而得名。今天長江以南的所謂“本地”漢人,高矮白黑,人種之間差異其實不小,有時候便是因為他們骨子裡流的本是洛陽人的血。■
(作者系建築策展人)
從周武王滅商後營建的洛邑開始,洛陽就仿佛墜入了一個周而復始的怪圈。無論城址遷徙,還是改換姓名,任由道德訓誡和興亡成敗的種種教訓,只要洛陽還是神都帝京,就一樣終難逃大起大落的命運。今天人們只知明清北京城的壯麗,卻不太想得到洛陽,這號稱十三朝古都的中國第一歷史名城,毀棄復又興起,這樣的輪回究竟有過幾遭?百代的經營一朝都如摧枯拉朽,今天,這重復耕種的大地上竟已渺無昔日文明的痕跡。
1963年,當紐約市的資本家們在一片爭議中合謀拆除賓夕法尼亞火車站時,《紐約時報》發布社論說:“將評說我們的,不是那些我們所建造的紀念碑,而是那些我們所毀棄的。”
難怪宋人司馬光會說,“欲問古今興廢事,請君只看洛陽城!”
在《詩經》的《王風》中,一首題為《黍離》的詩歌記載了另一座古都的結局: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毛亨的《序》暗示著它可能和《洛陽伽藍記》有著類似的起源——曾經親眼目睹了前朝盛況的官人返回故土,卻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周大夫行役, 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闵宗周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彼黍離離”並不僅僅是洛陽和豐、鎬的命運,和中國歷史上的其他偉大都市相比,上一個千年中國文化的主角北京應該倍感欣慰——畢竟它還剩下了不少可見的“遺跡”,而洛陽已經湮沒無存,哪怕是些幸存的“屍骨”。要知道,使後來拜訪這座城市的北魏小官吏楊衒之發出“《麥秀》之感,非獨殷墟;《黍離》之悲,信哉周室!”的感慨的北魏洛陽,曾經是中國古代最令人瞠目結舌的輝煌都市——“近代以前全球所見范圍最大的城市”(俞偉超語),那個洛陽擁有中國古代最高的木構建築(永寧寺塔),擁有最多數目的佛寺和佛塔,從蔥嶺以西到大海之東,都有絡繹不絕的訪客。但僅僅在北魏滅亡後的十數年後,它所能留給來者的就只有“彼黍離離”,茫茫一派“自然”了。
“彼黍離離”背後聯系的不是“花之洛陽”,而是“荊棘銅駝”,是“城春草木深”。其實城市並沒有消失。因為“自然”依然按照它的形狀在生長,野草侵入闾巷,狗糞塗滿門庭,如同一件陶范界定了它所鑄造的器物的形狀,正負顛倒,荊棘和稗草勾勒出了已經成為空白的城市……只是,這種依托人工范型而成長起來的“自然”,最終將無情地吞沒它的“原型”,今天我們看到的,實際上是古代城市的“陰刻”,如果你拿到一份考古工作者繪就的地圖去實地考察,會發現,似乎是著了魔咒一般,在整座洛陽“內郭城”的遺址四圍,只環繞著一大摞和“都會”無所粘連的“自然村”:
保駕莊、白馬寺村、太學村、義井鋪 ……
這地名間或洩露一點前塵往事,但在偌大的內郭城中,只剩下一片阡陌縱橫的平疇,再無半分都會氣息,昔日的“城市”和今朝的“鄉土”恰好翻轉了個兒,隱約可見的一線土牆拱衛著稠密的“當代”裡剩下的這片空白。
我在一個微雨的夏日莅臨這座“城市”,腳踩像昔日天街一樣漫長的土壟,面向只在虛空中的魏阙和宮門。三春已逝,那花一樣的洛陽,不僅從中國的現實中也從中國人的感受裡被抹去了。
細細想來,對翠樓绮閣的毀棄並不是最值得歎惋的時刻,驚心動魄來自於重新塗寫這片風景的那一刻,一群饑民攀緣而上已經燒為白地的宮室土台,七手八腳地指點著錦繡灰與公卿骨:
“這土細潤,可以挖去蓋俺家後院。”
“這細皮嫩肉女子,干脆帶回家做我婆娘。”
“好大一片空場,翻耕了,明年一定有好收成。”
“這地甚平,或可以做打谷場。”
這驚心動魄的時刻並不是獨一僅有,中國建築史,或許毀棄了百分之九十九只留下了百分之一,而這百分之一的命運如今尚未可知。在同一片建築基址上,拆了又建,建了又拆,或是干脆拆了又拆又拆又拆……終於,荒城只剩下了丘墟,原來那些麗景飛甍的凌雲傑閣,卻不如它們黃泥塗地的台基更為經久,於是,古城就像是一座千年的爛尾樓伫立在原野中,任憑風吹雨打……在粗大骨節的黑手緊握鍬柄後的遠景裡,原本“碧樓金粉”,不過是一堆可以搬來倒去的泥巴而已。
——初次造訪洛陽漢魏故城遺址時,當地考古學者告訴我,當他們開始挖掘土台基址時,卻發現一戶農民已經在其中挖了一個窯洞,住在裡面。顯然,用細細遴選,並遍遍篩過的夯土壘成的宮殿台基,發現了它新的用途。而在北魏洛陽的例子裡,“金銮殿”與“茅草屋”重疊錯置的現象,也比比皆是。
無意在“金銮殿”與“茅草屋”之間分出高下,但最為觸目驚心的,也莫過於這種文明形態無端的錯置與顛倒,那是對於歷史因果的極端蔑視,對於無謂勞動和惡意反復的極端冷漠。無可否認,新的生命成長於斯,新的歷史動力創造於此,但一切卻是以一種粗粝的的方式完成的,這種偉大王朝城市的生與死之歌,與“建築設計師”這一二十世紀寵兒的趣味絕不同調,也與我們對現代都會物質現實的眷慕格格不入。
無可否認的是,“荊棘銅駝”是中國建築的一句谶語,它像極了尼古拉斯·普桑畫中的轶事——借一塊石碑,在淳熙的風景中沉默的死神開口了:在阿卡迪亞(樂園)也有我!如同“花”與“塵”的並存,“城春草木深”般的景象對於中國建築的啟示,並不在於它是某種“親近自然”的理想生活的象征,而在於它是文明的反面。在此,由“自然”和“人工”混合起的廢墟是人造世界的永遠噩夢,是完美現境裡無可消除的一處毒瘤。它揭示出一種高速建設與潦草毀棄之間的矛盾沖突,它既培育了持續進取的熱情又造就了不斷激發的混亂。
它將巨廈摧為瓦礫,它將高塔付之一炬。■
(作者系建築策展人)
-
没有相关古代建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