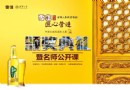媒體:傳統村落成文物竊賊"淘寶地" 整棟房子被拆除
日期:2016/12/14 11:04:08 編輯:中國古代建築傳統村落是中國數千年農耕文明的結晶。近年來,政府和民間都加大了對傳統村落的重視和保護。但在一些農村地區,傳統村落被關注後時常“遭劫”,這一現象成為保護過程中繞不開的“魔咒”。
傳統村落“成名”易招賊
中國於2012年搶救性地啟動傳統村落保護工作,經過4年努力,前三批2555個村落被列入中國傳統村落名錄,並已初步建立指導和管理機制,獲得中央財政平均每村補助300萬元的保護扶持。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總經濟師趙晖表示,當前傳統村落快速消失局面已得到有效遏制,第四批中國傳統村落名錄將新增1602個村落。
江西歷史文化遺產豐富,境內分布著近千個格局保存完整、歷史風貌保存較好的傳統村落,時間跨度從宋代到近代。近年來,江西從保護機制建設、保護資金撥付、立法等層面,不斷加強對傳統村落的保護。
但《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調研發現,這些散落在鄉間的傳統村落大多距離縣城三五十公裡。因為地處偏僻,近年來不同程度地遭竊賊“光顧”。
在江西金溪縣象山公園內的錦繡塔一樓展廳中,陳列著一塊明代的镂空石雕《荷塘情趣圖》。“這塊石雕歷經9年才追回,原本是一棟傳統民居上的構件。”金溪縣文廣新局副局長王新景介紹說,雖然石雕並非文保單位上的構件,但其雕工精致、線條完美,在文物黑市中價格近十萬元。
金溪縣約有150余個傳統村落、數千棟傳統建築,僅浒灣鎮就有900多棟明清建築。這些傳統村落已淪為文物商人的“淘寶地”。據該縣公安局刑警大隊大隊長徐國文介紹,2009年至2016年初,當地警方共破獲相關盜竊團伙5個,實施盜竊行為近百次。
為斬斷伸向傳統村落的黑手,金溪縣每年集中開展一次打擊非法買賣文物、買賣古建築構件的違法犯罪專項行動。目前,文物盜竊案件發案數由2011年的62起下降到2015年的6起。但徐國文說,由於取證難、周期長,“破獲的案件僅是實際發生案件的冰山一角。”
“專家前腳走,毛賊後腳來。”塔前彭家村村民理事會理事長彭松元說,他們村莊2013年入選中國傳統村落後,很多專家、游客慕名而來,但也引來竊賊的觊觎。他介紹,塔前彭家村距樟樹市區35公裡,現存祠堂與古代民居30余棟。祠堂中,原有4塊清代牌匾,如今只剩一塊,許多古民居內的木雕家具、鎏金門窗也在陸續“消失”。
66歲的塔前彭家村村民彭義初說,今年5月看見有陌生人拿著一個東西在村裡到處探,後來就發現祠堂地面被挖了個坑;當地一直有埋老物件鎮宅的風俗,但失竊了什麼誰也不清楚。而一些無人居住的老宅被盜,往往要過很久才能發現。
執法缺乏震懾力
記者調查發現,部分傳統村落成失竊“重災區”,其建築構件被肆意盜賣,甚至整棟房子被拆除或異地遷移。原因就在於許多傳統民居仍處於執法“真空”地帶。
江西省住建廳有關工作人員介紹,目前被依法納入相關法律法規進行保護和管理的,只有不可移動文物、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歷史文化街區保護范圍內的歷史建築。傳統村落中能被納入上述保護范圍的建築只有極少一部分。
“傳統民居中的失竊物品不是文物,只能按照一般物品進行估價。估價也並非文物部門來做,而是物價部門。”宜黃縣公安局政委黎明華舉例說,比如一些祠堂中的柱礎,從材料上看就是石頭,估價遠低於其在黑市上的價格。
江西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梁洪生表示,類似石磨、石水缸、雕花窗戶、匾額等雖不是文物,但都是農耕文化的重要元素,一旦消失,傳統村落的文化體系將不完整。
由於涉案金額達不到量刑標准,大多數偷盜古建築構件案被按照一般盜竊行為處理。黎明華解釋說:“涉案金額不足1500元無法追究刑事責任。而傳統民居的產權均為村民所有,公安機關只能依據損毀私人財物的嚴重程度,進行治安處罰。”
徐國文曾破獲一個針對傳統村落的盜竊團伙,先後偷盜20次,涉案金額8萬多元,判刑最重的也只有三年零兩個月。他去一個文物商人的庫房追回失竊的構件,盡管滿屋子都是疑似“贓物”,但除了拿回當地失竊構件,什麼也做不了。“即使是文物,買方也能以自己不知情為由逃避處罰。”徐國文說,傳統建築構件往往都是異地銷贓,其中很大一部分流向江浙沿海地區。
此外,文保建築上的構件雖受文物法保護,但存在認定難問題。“文保單位上的建築構件屬於不可移動文物,文保部門在配合公安部門查案時,需要判斷構件屬於哪一棟文保建築。”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徐長青介紹說,文物普查往往不會太細,只會對建築整體、重要的匾額構件進行拍照登記,花窗、家具等構件較難進行比對。
記者調查還發現,受農村留守老人多以及地方經濟水平限制,傳統村落村民的保護積極性未能有效調動起來,村民保護有心無力。梁洪生說:“傳統村落所在地區相對貧困,交通相對閉塞,因此,單純地依靠村民不計成本維修古建,幾乎不可能。”
在一些旅游業態相對成熟的傳統村落,基層干部也坦言,能共享紅利的往往是開發企業和少部分村民,而收益分配不均則可能引發村民不滿。
在景德鎮浮梁縣瑤裡風景區的瑤裡村,許多在街頭賣土產的老人告訴記者,村裡真正賺錢的是那些在仿古建築裡開餐館的,而住在老房子裡的村民沒什麼收獲。
亟須完善法律法規強化聯動機制
“目前一些法規或多或少都涉及傳統村落保護,應考慮出台細化的、專門的《歷史建築保護管理辦法》,將未定級的傳統村落民居納入保護范圍。”江西樂安縣博物館館長陳小群說。
黎明華認為,法律法規“禁令”多“罰令”少,建議細化、量化懲處措施,使其發揮切實的震懾作用。金溪縣文物管理所所長吳泉輝說,可考慮將某一年代之前的傳統建築上的構件,視同於文保單位的構件,使得基層執法更易操作。
建立部門聯動機制也成為各地呼聲。一些受訪者反映,部門執法依據不統一、權責不明晰成為辦案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一些地方,曾出現縣級文物部門認定的文物不被法院認可的情況;負責可移動文物的博物館方面與分管不可移動文物的文化執法大隊,在文物鑒定時互相推诿,不肯出具鑒定報告。江西宜黃縣文物管理所所長邵劍飛等認為,在基層警力和文保力量十分有限的情況下,各級政府應加強統籌,明確各部門的權責范圍,建立部門聯動機制,對相關推诿行為進行追責。
傳統村落開發後的村民參與機制也亟待建立。“原住民和古建築是一個整體,讓原住民來打造業態才能避免過度開發。”江西吉水縣文物局局長葉翔認為,古村落的保護與開發不應由政府包辦,但也不能完全交給市場。據了解,江西目前部分景區已進行先行探索,讓村民與旅游公司簽約,出租祖宅後仍可在此生活,公司則負責房屋的修繕等日常管理。這樣使得游客參觀時不再是看一棟空蕩蕩的老宅。
梁洪生建議,村民初期的興奮與認同,有必要轉變並催生村莊內民主管理制度的建立,宗族房派關系應正面被利用於傳統村落的保護當中。同時,傳統村落的開發紅利共享機制需做到公平公正。近年來,金溪縣在全縣重點傳統村落制定了《文化遺產保護村規民約》,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不少傳統建築構件的私自倒賣行為。
呼喚“活態保護”
隨著城鎮化進程加快,農村人口外流嚴重,一些地處偏僻、保存完整的傳統村落“空心化”嚴重,村落歷史文化在加速消失。
“房子還需人來撐”。江西吉水縣燕坊古村老支書鄢和年告訴記者,村裡之所以能留下102棟清代建築和13座牌坊,是因為90%的房子都有人居住。
但鄢和年擔憂的是,十年、二十年後,當老人們離世了,誰來守護這些老宅子?“老人們喜歡這種冬暖夏涼的磚木房子,後輩們大多在村外找土地建水泥房了。”
旅游開發成為公認的傳統村落發展路徑,但一些地方改變特色村落固有風貌肆意改造,導致“千村一貌”,忽略了原有的地域風格。
江西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梁洪生說,傳統村落中的各式建築是物化的旅游資源。這種資源在旅游開發過程中被嚴重同質化,讓這些傳統村落的“小歷史”失去了特色化資源。
梁洪生注意到,許多傳統村落在保護過程中“重物質輕文化”,留住了建築卻留不住傳統。
撫州樂安縣的流坑古村是首批“中國傳統村落”之一,當地特色民俗豐富。其中,流坑傩舞是國家級非遺項目樂安傩舞的流派之一,小吹會則是江西省級非遺項目。流坑管理局文保辦主任沈文介紹,為將這兩大非遺傳承下去,縣裡在2007年開過培訓班,但培訓結束後沒能留住一個學員。“如今政府投入成立了表演隊,隊員平均年齡68歲。白教、有表演費,還沒什麼人願意來。”
受訪專家認為,傳統村落保護亟待扭轉“重物質輕文化”誤區,同時健全“活態保護”支撐體系。從傳統村落保護的規劃入手,推動保護工作從“重物質”向“重文化”轉型,健全成系統的、可持續的保護體系。
同時,加強傳統村落中的非遺保護工作。梁洪生建議,可在申報中國傳統村落文本中,明確要求“非遺”項目要有本村的真實傳承人,以確保“非遺”項目的認定和“傳承人”的保護落到實處。
記者了解到,江西省在全國率先出台了省級層面的傳統村落保護條例,將於12月1日起施行。根據《江西省傳統村落保護條例》要求,要對古村落進行“活態”保護,明確縣級政府為責任主體,進一步改善傳統村落的基礎設施、人居環境,提高村民的生活質量,把村民留住。同時,鼓勵傳統村落的居民以其所有的傳統建築、房屋、資金等入股參與傳統村落的保護、開發和利用,傳統建築所有人可以約定獲得合理的收益分成。
原標題:部分傳統村落淪為文物竊賊“淘寶地”,甚至整棟房子被拆除來源:澎湃新聞網- 上一頁:藏品文物保護亟待納入法律保護體系
- 下一頁:故宮大高玄殿修繕取得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