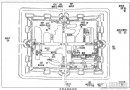石獸實際在一定程度上改寫了中國雕塑史
日期:2016/12/15 1:19:44 編輯:中國古代建築
“江水為害,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二枚在府中,一枚在市橋下,二枚在水中,以厭(壓)水精,因曰犀牛裡。”
——據《蜀王本紀》
“(李冰)外作石犀五頭以厭(壓)水精,穿石犀溪於江南,名曰犀牛裡。後轉置犀牛二頭;一在府市市橋門,今所謂石牛門是也,一在淵中。”
——據《華陽國志·蜀志》
2010年,天府廣場的鐘樓拆除,它帶走了一代人的記憶,也帶來了其下深埋石獸的重見天日。去年年初,考古人員在鐘樓原址發掘出的“千年石獸”轟動全國。如今,它在金沙遺址博物館的文物修復室裡享受“深度保養”,以使被土壤鹽分侵入的身體保持穩定。明年,它就將作為鎮館之寶入住新落成的成都博物院。
早有傳說
“新中國成立後修建電訊大樓(即鐘樓)時,掘得一石獅,則苑之瑞獸門當在斯地”
其實,早在40年前,天府廣場鐘樓修建之初,這頭石獸就曾短暫“現身”。根據《成都城坊古跡考》的記載,“新中國成立後修建電訊大樓(即鐘樓)時,掘得一石獅,則苑之瑞獸門當在斯。”當時,多名老人曾回憶,在1971年~1973年間,電信大樓施工前期挖地基、建地下室期間,曾發現石獸。一名叫車凡英的老人曾是四川省建築工程總公司的施工技術員,負責電信大樓設計施工。他回憶,當時挖開了一個直徑2米的大坑,見一“動物”四腳朝天,“仔細辨認一下,是只石象。”
今年93歲的苟治平告訴記者,自己是上世紀70年代的一名考古隊員,也是這頭石獸的“目擊證人”。上世紀70年代,鐘樓開建後,文管部門曾接到工地報告的情況,苟治平到現場勘查。苟老說,由於當時並未將這塊石頭全部刨出,只看得到局部,無法准確判斷是何動物。當時文管部門曾有將石獸發掘出來的打算,不過由於工程技術條件的限制,加之工地方工期較緊,只得深埋回填。石獸就此被鐘樓的基樁壓在地下。這頭埋藏於天府廣場東北側的石獸,也成為苟老心頭的牽掛。
當年的施工隊原助理工程師王順清表示,1971年修建鐘樓地下室時,他和幾名同事挖出了一匹兩米多高的石馬。“石馬”頭朝南尾朝北,“馬”身兩米多長,後被回填。原工藝設計負責人林昌海稱,當時地基樁一般都要向地下打七八米深,但石獸所在處只能打4米左右,就再也打不進去了。由於石獸“鼻子很長”,他推斷是一只和真象差不多大的石象。
據悉,目前國內大部分考古發掘均屬於搶救性發掘,而在考古力量未達到要求時,一般會將文物回填以待來日,比如金沙遺址博物館裡大量仍被填埋的象牙就是依照此原則。
單霁翔現場查看
“(石獸)實際在一定程度上改寫了中國雕塑史”
去年初,石獸完全從土中翻身而出,露出了清晰的輪廓:長3.3米、寬1.2米、高1.7米,重8.5噸。石獸身體的一側,雕刻著清晰的卷雲紋,分別分布在頭頂、腮邊、前蹄上部以及後臀處,背上有幾十處坑窪,每個約一元硬幣大小,疑似文字。
成都博物院院長王毅告訴記者,石獸是比較早的圓雕石刻,這種圓雕石刻在中國發現極其罕見,可能是迄今為止四川發現的最早的大型圓雕石刻。出土之時,前國家文物局局長、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霁翔曾現場查看並感歎:“(石獸)實際在一定程度上改寫了中國雕塑史。”
石獸發掘所在地四川大劇院考古工地位於成都市天府廣場東北側,西臨人民中路一段,東臨東華門街,南臨蜀都大道人民東路段,北臨四川省煤監局家屬樓。據史料記載,這一地帶在歷史上曾屬秦漢以來大城的范圍,亦為明代蜀王府皇城的東南隅,歷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2008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對天府廣場西側的成都博物館新址用地進行了考古發掘,揭露出大量的先秦至明清時期文化遺跡與遺物;2010年,天府廣場東南側又發現了兩件與漢代成都官學有關的石刻功德碑。上述發現情況充分表明,現在的天府廣場及其周邊是成都市區古代文化堆積最為豐厚的區域之一。
李冰治水
“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五犀牛”
目前,專家們傾向認為,石獸跟李冰治水有關系。據《蜀王本紀》、《華陽國志·蜀志》等史料記載,秦朝的蜀守李冰在修建都江堰時,曾經下令雕刻了5只石犀,兩頭運到了成都,另外3頭則在灌縣的江中。5只犀牛其實是水則即古代衡量水位的水尺,同時也是鎮水石神。唐代杜甫也曾寫詩:“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五犀牛,自古雖有厭勝法,天生江水向東流,蜀人矜誇一千載,泛濫不近張儀樓。”
王毅也表示,石獸與李冰治水緊密相關,“成都發展歷史就是與洪水的斗爭史,成都因水而困、因水而興。”
王毅說,在金沙遺址考古時,就發現了竹籠落石治水的遺物,文獻記載李冰制作五尊石犀鎮水,是古代勞動人民在科學技術不發達的時候,為抵御不可抗拒的自然災害,而尋求的精神寄托,“是當時科技和宗教的結合,也是一種精神勝利法。”
其他猜想
“石牛對石鼓,銀子萬萬五,誰能識得破,買來半個成都府”
在民間,對於石獸身份的猜想卻層出不窮。以下兩種觀點最具代表性:
2010年,成都作家謝天開曾在個人博客上提及,天府廣場鐘樓腳下,曾有一頭早在37年前就已經發現的唐代石獸。他發現,在《成都城坊古跡考》中有相關記錄:“建房後修建電訊大樓時,掘得一石獅,則苑之瑞獸門當在斯地。”電訊大樓即拆除的鐘樓,而“苑”即宣華苑,屬五代時環繞成都市中心的著名系列宮殿。他推斷,文中所說的石獸應可追溯到唐代。
四川省文史館館員馮廣宏曾參與《成都城坊古跡考》2006年再版修訂。他曾根據多年從事文史研究的經驗推測,鐘樓下的這頭石獸可能是用於鎮水的石犀、石牛,也可能是舊時宮廷門前的瑞獸。馮廣宏稱,自五代以來,成都的中心城區遭受過兩次重大毀壞,一次是宋末元初蒙古兵進城時造成的毀壞,一次則是明末清初張獻忠“入川屠蜀”。馮認為,相較於前一次,“入川屠蜀”帶來的破壞更為徹底。鐘樓腳下的這頭石獸,有可能就是在那時被埋於地下的。
在成都民間,有關於張獻忠“江中沉寶”的故事。“石牛對石鼓,銀子萬萬五,誰能識得破,買來半個成都府。”鐘樓腳下的那尊石獸,是否也與此有關?隨著石獸出土,謎團或將被解開。
(曾靈 綜合)
鑒寶
成都博物院漢代石碑
看點:出土於天府廣場東御街地下人防工程裡的兩塊漢代石碑形狀怪異:石頭有四個角,還是翹起的,上邊還有均勻的錾子紋路,刻著工整的文字……較大的大碑上,碑文末段提及“元嘉有二仲□”,專家將“元嘉有二”解讀為“東漢元嘉二年”,而“仲□”則可能是“仲夏”或“仲秋”。元嘉二年也就是公元152年,時值漢桓帝劉志在位。而在較小的一塊石碑上,落款處“本初元年六月下旬”字樣十分清晰。本初元年系公元146年,也就是說,兩塊石碑中,較小的一塊碑距今已有1864年。
價值:較大石碑的碑文以“巍巍大漢”開篇,專家解釋這有一種表功意味。而在內文中,“四世遵統”、“內任公輔、外宣藩國”等文字,也顯示出碑文記述的主人公身世顯赫。而且,兩塊碑的碑文上均有朱砂覆蓋。成都博物院院長王毅說,這是他20多年的考古生涯中遇到的最令人興奮的漢代考古發現。雖然碑文內容尚有待組織專家進行科學系統地解讀,但目前基本可以判定,這兩塊石碑是出現在廟堂等處的記功碑,與當時當地的最高行政長官有關。
——據《蜀王本紀》
“(李冰)外作石犀五頭以厭(壓)水精,穿石犀溪於江南,名曰犀牛裡。後轉置犀牛二頭;一在府市市橋門,今所謂石牛門是也,一在淵中。”
——據《華陽國志·蜀志》
2010年,天府廣場的鐘樓拆除,它帶走了一代人的記憶,也帶來了其下深埋石獸的重見天日。去年年初,考古人員在鐘樓原址發掘出的“千年石獸”轟動全國。如今,它在金沙遺址博物館的文物修復室裡享受“深度保養”,以使被土壤鹽分侵入的身體保持穩定。明年,它就將作為鎮館之寶入住新落成的成都博物院。
早有傳說
“新中國成立後修建電訊大樓(即鐘樓)時,掘得一石獅,則苑之瑞獸門當在斯地”
其實,早在40年前,天府廣場鐘樓修建之初,這頭石獸就曾短暫“現身”。根據《成都城坊古跡考》的記載,“新中國成立後修建電訊大樓(即鐘樓)時,掘得一石獅,則苑之瑞獸門當在斯。”當時,多名老人曾回憶,在1971年~1973年間,電信大樓施工前期挖地基、建地下室期間,曾發現石獸。一名叫車凡英的老人曾是四川省建築工程總公司的施工技術員,負責電信大樓設計施工。他回憶,當時挖開了一個直徑2米的大坑,見一“動物”四腳朝天,“仔細辨認一下,是只石象。”
今年93歲的苟治平告訴記者,自己是上世紀70年代的一名考古隊員,也是這頭石獸的“目擊證人”。上世紀70年代,鐘樓開建後,文管部門曾接到工地報告的情況,苟治平到現場勘查。苟老說,由於當時並未將這塊石頭全部刨出,只看得到局部,無法准確判斷是何動物。當時文管部門曾有將石獸發掘出來的打算,不過由於工程技術條件的限制,加之工地方工期較緊,只得深埋回填。石獸就此被鐘樓的基樁壓在地下。這頭埋藏於天府廣場東北側的石獸,也成為苟老心頭的牽掛。
當年的施工隊原助理工程師王順清表示,1971年修建鐘樓地下室時,他和幾名同事挖出了一匹兩米多高的石馬。“石馬”頭朝南尾朝北,“馬”身兩米多長,後被回填。原工藝設計負責人林昌海稱,當時地基樁一般都要向地下打七八米深,但石獸所在處只能打4米左右,就再也打不進去了。由於石獸“鼻子很長”,他推斷是一只和真象差不多大的石象。
據悉,目前國內大部分考古發掘均屬於搶救性發掘,而在考古力量未達到要求時,一般會將文物回填以待來日,比如金沙遺址博物館裡大量仍被填埋的象牙就是依照此原則。
單霁翔現場查看
“(石獸)實際在一定程度上改寫了中國雕塑史”
去年初,石獸完全從土中翻身而出,露出了清晰的輪廓:長3.3米、寬1.2米、高1.7米,重8.5噸。石獸身體的一側,雕刻著清晰的卷雲紋,分別分布在頭頂、腮邊、前蹄上部以及後臀處,背上有幾十處坑窪,每個約一元硬幣大小,疑似文字。
成都博物院院長王毅告訴記者,石獸是比較早的圓雕石刻,這種圓雕石刻在中國發現極其罕見,可能是迄今為止四川發現的最早的大型圓雕石刻。出土之時,前國家文物局局長、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霁翔曾現場查看並感歎:“(石獸)實際在一定程度上改寫了中國雕塑史。”
石獸發掘所在地四川大劇院考古工地位於成都市天府廣場東北側,西臨人民中路一段,東臨東華門街,南臨蜀都大道人民東路段,北臨四川省煤監局家屬樓。據史料記載,這一地帶在歷史上曾屬秦漢以來大城的范圍,亦為明代蜀王府皇城的東南隅,歷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2008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對天府廣場西側的成都博物館新址用地進行了考古發掘,揭露出大量的先秦至明清時期文化遺跡與遺物;2010年,天府廣場東南側又發現了兩件與漢代成都官學有關的石刻功德碑。上述發現情況充分表明,現在的天府廣場及其周邊是成都市區古代文化堆積最為豐厚的區域之一。
李冰治水
“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五犀牛”
目前,專家們傾向認為,石獸跟李冰治水有關系。據《蜀王本紀》、《華陽國志·蜀志》等史料記載,秦朝的蜀守李冰在修建都江堰時,曾經下令雕刻了5只石犀,兩頭運到了成都,另外3頭則在灌縣的江中。5只犀牛其實是水則即古代衡量水位的水尺,同時也是鎮水石神。唐代杜甫也曾寫詩:“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五犀牛,自古雖有厭勝法,天生江水向東流,蜀人矜誇一千載,泛濫不近張儀樓。”
王毅也表示,石獸與李冰治水緊密相關,“成都發展歷史就是與洪水的斗爭史,成都因水而困、因水而興。”
王毅說,在金沙遺址考古時,就發現了竹籠落石治水的遺物,文獻記載李冰制作五尊石犀鎮水,是古代勞動人民在科學技術不發達的時候,為抵御不可抗拒的自然災害,而尋求的精神寄托,“是當時科技和宗教的結合,也是一種精神勝利法。”
其他猜想
“石牛對石鼓,銀子萬萬五,誰能識得破,買來半個成都府”
在民間,對於石獸身份的猜想卻層出不窮。以下兩種觀點最具代表性:
2010年,成都作家謝天開曾在個人博客上提及,天府廣場鐘樓腳下,曾有一頭早在37年前就已經發現的唐代石獸。他發現,在《成都城坊古跡考》中有相關記錄:“建房後修建電訊大樓時,掘得一石獅,則苑之瑞獸門當在斯地。”電訊大樓即拆除的鐘樓,而“苑”即宣華苑,屬五代時環繞成都市中心的著名系列宮殿。他推斷,文中所說的石獸應可追溯到唐代。
四川省文史館館員馮廣宏曾參與《成都城坊古跡考》2006年再版修訂。他曾根據多年從事文史研究的經驗推測,鐘樓下的這頭石獸可能是用於鎮水的石犀、石牛,也可能是舊時宮廷門前的瑞獸。馮廣宏稱,自五代以來,成都的中心城區遭受過兩次重大毀壞,一次是宋末元初蒙古兵進城時造成的毀壞,一次則是明末清初張獻忠“入川屠蜀”。馮認為,相較於前一次,“入川屠蜀”帶來的破壞更為徹底。鐘樓腳下的這頭石獸,有可能就是在那時被埋於地下的。
在成都民間,有關於張獻忠“江中沉寶”的故事。“石牛對石鼓,銀子萬萬五,誰能識得破,買來半個成都府。”鐘樓腳下的那尊石獸,是否也與此有關?隨著石獸出土,謎團或將被解開。
(曾靈 綜合)
鑒寶
成都博物院漢代石碑
看點:出土於天府廣場東御街地下人防工程裡的兩塊漢代石碑形狀怪異:石頭有四個角,還是翹起的,上邊還有均勻的錾子紋路,刻著工整的文字……較大的大碑上,碑文末段提及“元嘉有二仲□”,專家將“元嘉有二”解讀為“東漢元嘉二年”,而“仲□”則可能是“仲夏”或“仲秋”。元嘉二年也就是公元152年,時值漢桓帝劉志在位。而在較小的一塊石碑上,落款處“本初元年六月下旬”字樣十分清晰。本初元年系公元146年,也就是說,兩塊石碑中,較小的一塊碑距今已有1864年。
價值:較大石碑的碑文以“巍巍大漢”開篇,專家解釋這有一種表功意味。而在內文中,“四世遵統”、“內任公輔、外宣藩國”等文字,也顯示出碑文記述的主人公身世顯赫。而且,兩塊碑的碑文上均有朱砂覆蓋。成都博物院院長王毅說,這是他20多年的考古生涯中遇到的最令人興奮的漢代考古發現。雖然碑文內容尚有待組織專家進行科學系統地解讀,但目前基本可以判定,這兩塊石碑是出現在廟堂等處的記功碑,與當時當地的最高行政長官有關。
熱門文章
熱門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