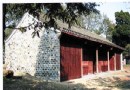萬枝丹彩灼春融
日期:2016/12/14 19:13:17 編輯:古建園林“桃紅又是一年春”,現在正是桃花開放之時,“滿樹如嬌爛漫紅,萬枝丹彩灼春融”,芳菲可愛。
桃具有本真美。古人稱頌的桃色之美,乃為未經嫁接之桃,其色極嬌、極純,有“桃腮”、“桃靥”之喻美人之面,並稱那純情至真的女孩為“桃花女”。李漁稱桃花與李為“領袖群芳者”。皮日休稱它為“艷外之艷”、“花中之花”(《桃花賦》)。因而,《詩經.周南》以“桃之夭夭,灼灼其華”稱美新嫁娘。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桃成為贈答、寄托愛情和友情的象征符號。唐李白用“桃花潭水深千尺”,來形容友人之情,“桃花潭”也盛滿了友誼的情感。宋黃庭堅用“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來寄寓思念朋友的悠悠情思。崔護的“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崔護《題都城南莊》)的詩歌,透露了桃花與浪漫愛情的信息。
桃和李還是對弟子的美稱。如稱頌教師的教育成果謂“桃李滿天下”;桃的默默無言、不事張揚,也成為品格的象征。司馬遷稱漢代的“飛將軍”李廣為“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桃花雖美,但卻不擇處所,“宜別墅山隈,小橋溪畔,橫參翠柳,斜映明霞”(陳浩子《課花十八法》),李漁也說,“惟鄉村籬落之間,牧童樵叟所居之地,能富有之”,因此,“欲看桃花者,必策蹇郊行,聽其所至,如武陵人之偶入桃源,始能復有其樂”,相反,“如僅載酒園亭,攜姬院落,為當春行樂計者,謂賞他卉則可,謂看桃花而能其真趣,吾不信也”(《閒情偶寄》)。
東晉陶淵明創構了集“美”“善”於一體的桃花源,成為農耕社會的“伊甸園”,那裡,“土地平曠,屋捨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發垂髫,並怡然自樂”。“雖有父子無君臣”(王安石《桃源行》),不廢父子老幼之禮。那裡人際關系雍雍和和,熱情、好客,“童孺縱行歌,斑白歡游詣”,“黃發垂髫,怡然自樂”。“直於污濁世界中另辟一天地,使人神游於黃、農之代。公蓋厭塵網而慕淳風,故嘗自命為無懷、葛天之民,而此記即其寄托之意。”(清丘嘉惠《東山草堂陶詩箋》卷五)。桃花源雖然是心造的海市蜃樓,但其動力,“是未被滿足的願望,每一個幻想都是一個願望的滿足,都是一次對令人不能滿足的現實的校正”,“夢的內容在於願望的達成,其動機在於某種願望”(弗洛伊德《作家與白日夢》),是現實的折光。所以,盡管“仙家一出尋無蹤”,“只見桃花不見人”,但後人依然把桃源視為神仙之境,蘇轼曾將南陽菊水、武都仇池比作桃花源,“桃源小隱”、“桃園”等園林題名,蘇州留園的“小桃塢”,唐伯虎的“桃花庵”,自稱自己是“桃花庵裡桃花仙”。
桃花與吏治廉潔清明也有關系。康熙皇帝南巡時書贈當時的江蘇巡撫吳存禮一副對聯,現在镌刻在滄浪亭的“御碑亭”內,聯語曰:“膏雨足時農戶喜,縣花明處長官清。”聯語對句典出西晉潘岳。潘岳在河陽當縣令時,多植桃柳,號稱花縣,以表示自己的清高廉潔。庾信《枯樹賦》有“若非金谷滿園樹,即是河陽一縣花。”又《春賦》雲:“河陽一縣並是花。金谷從來滿園樹。”潘岳河陽一縣花,甚至還與“五柳先生”陶淵明相提並論。康熙用此典,含有勸喻地方官吏清廉之意。
基於原始的植物崇拜,古人認為桃有驅鬼辟邪的作用,因有桃符、桃人、桃木劍等。《山海經》記載:“東海度朔山有大桃樹,蟠屈三千裡,其卑枝門東北曰鬼門,萬鬼出入也。有二神:一曰神荼,一曰郁壘,主閱領眾鬼之害人者。於是黃帝法而象之,驅除畢,因立桃板於門戶上,畫郁壘以御凶鬼,此則桃板之制也。”又據《淮南子》記載的傳說,後羿是被桃木杖殺而死的,所以,鬼怕桃木,因此,人們掛薄木板於門,上畫神像,下畫二神,或寫上春詞和祝禱之語,這就是王安石“總把新桃換舊符”詩句的來歷,五代後蜀時開始,在桃板上書寫對聯,即延之今日的春聯。
由於桃極艷,然壽極短,故也有“紅顏薄命”之說。至於把桃花作為輕薄妖冶淫蕩的象征,所謂“桃色新聞”、“桃花運”之類,乃是後代對古人桃文化的“誤讀”,實在應該為桃花“辯誣”。
- 上一頁:藝圃:那一股淡淡的藥香
- 下一頁:溫山軟水園中春事
-
没有相关古代建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