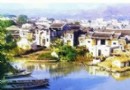到小黃看動情的小黃大歌
日期:2016/12/14 23:59:00 編輯:古代建築名稱
幾年前這個叫做小黃的侗寨,因為一曲侗族大歌而名揚海內外,青歌賽載譽而歸,少兒大歌隊出訪日本,很多人都是為聽大歌專程前來的。
班車盤山而上,雲海迢迢小黃寨子職的清晨安寧寂靜,雖然已名聞遐迩,雖然表演大歌要加收門票了,可是並沒有看到太多的游人,也沒有感覺到被旅游商業渲染的氣氛。人們還是要繼續走自己熟悉的生活節拍,還是水田中間的天然廁所,還是在自家門口抽著煙袋做著手工侗服裝的親切鄉民。

這裡住的地方都叫做歌堂旅社,有那麼點浪漫氣質,木樓,很干淨的房間床具,公用的衛生間和淋浴,條件大大超出我的預期,小黃村寨的本色並沒有進行過多的粉飾,可是為游人提供的便利卻有所改進。
鼓樓前的表演場上游客稀稀落落,一群盛裝的小姑娘悠閒地磕著瓜子,面對相機鏡頭絲
毫不怯,到底是見過世面的女孩子,唱歌終於不再只是娛樂,而成為改變生活際遇的重要途徑。走出小黃去外面演出了,有熱心人擔負學費,過年過節有人給他們寄錢寄衣服,她們的目光中終於不再只有羞澀和膽怯。
逆光的鼓樓下,演出開始了,男人們的歌,女人們的歌,男孩子的歌,女孩子的歌,男女搭配對歌約會的表演,琵琶歌、蟬歌、攔路歌,小黃的侗歌種類豐富多彩,他們的歌聲唱出了生活的喜怒哀樂,唱出了愛情的忠貞不渝,唱出了春花秋月的浪漫遐想,也唱出了對命運不公的控訴。行歌坐月的對唱讓青年男女互訴衷腸,蘆笙會的比賽在歌聲中決出勝負,一張簡單的名次獎狀可以讓全寨人歡喜動容。

大歌終於響起來了,這是所有侗歌中最完美協調的一種聲音,沒有樂器伴奏,沒有指揮協助,高、中、低音多聲部就這樣自然流暢地相互交融在了一起,來自於原生態大自然中的靈感,溪水潺潺的聲音,倦鳥歸林的聲音,蟲鳴蟬鳴的聲音,就這樣在歌聲中流淌出來了。他們都是沒有學過音樂理論的歌手,他們也認識五線譜,可是他們各自聲部的音都唱得那麼清晰那麼准確,一切似乎完美無瑕,一切又是渾然天成。
小黃的寨子裡有很多的歌班,同齡的孩子從小便開始組班,同歌班的歌友們是比兄弟姐妹還親的朋友。唱歌並不是什麼事業,唱歌就是生命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也許唱歌對他們來說太普通了,寨子裡年輕的男男女女們更熱衷於烤魚野餐,本來我以為我只是意外地加入了這一場野餐隊伍,可是回來的路上才發現田間處處有烤魚,以致後來在鼓樓內的壁畫上也看到了野外烤魚的情景,才知道這其實也是侗族民間古老的一項傳統娛樂。就像我們郊游踏青一樣,他們也用這樣的方式拜訪蘇醒的大自然。
左鄰右捨招呼著走了,背著漁網,挑著白菜和糯米飯,轉過村子進山了。這一走就是遙遙十裡路,走過一塊塊稻田,上了山坡,穿了密林,又下了山,魚塘真可謂是養在深閨人未識。
柴火早早地燃起來了,有人撈魚,有人拾柴,有人削樹枝,有人制作調料,也不開膛也不刮鱗也不抹鹽,插在樹枝上直接拷。野生的母姜和辣椒鹽、制成蘸水,看似簡單,味道卻很專業。塑料布一鋪,白菜葉子當盤子,烤得焦黃的魚,沒有筷子也沒有調羹,大家圍坐一圈,一手抓烤魚一手抓糯米飯,這才叫天然這才叫野餐。

回到旅捨,天已經快黑了,可是鼓樓廣場卻開始敲鑼打鼓熱鬧起來,樓裡燃起了炭火,嘩啦啦銀飾作響,兩隊盛裝女子入樓了,篝火的熱度熏染開來,火星點點,映紅了臉龐,真讓人懷疑這是不是也是一場衣香鬓影的夜宴。
一隊是十六七歲的少女,一隊是結了婚的小媳婦,詢問身邊的姑娘今天是否有什麼特別活動得到的回答是他們每天都是這樣練歌的。原來還有這樣鄭重其事的練歌。
侗歌一首接一首地唱起來了,間歇中有人在指點,有人在討論,唱得口渴了就去旁邊的水桶裡舀一碗水。他們的歌聲裡有專注,有執著,有悲傷也有快樂。那麼悠揚,那麼清亮,那麼自然又那麼奔放。這,才是小黃的歌。
一根粗壯的大木頭漸漸燃盡了,鼓樓的歌會散場了。唱歌的人走了,聽歌的人卻還意猶未盡。
經過經歷過這樣一個激蕩心弦的夜晚,白日裡的村落突然也變得多情起來。沒有歌聲的小黃可能是很平淡的,一樣的鼓樓,一樣的民居,一樣的稻田,一樣的侗女,可是我看他們的目光終於變得不一樣了。
交通:
從江每天有開往小黃的班車,上下午各一班。也可以考慮包車前往。早上可以坐面包車返回縣城。
住宿:
小黃比起岜沙的住宿條件略差一些,鼓樓前的一條街有幾個旅捨,都叫歌堂旅社,木樓,床鋪很干淨,公用衛生間,可洗熱水澡,吃飯的花費也不是很高,推薦主街盡頭的青山旅館和騰龍堂。
旅游貼士:
一、春節時候的大歌表演一般是初一到初六、上下午各一場,晚上有時候也會在鼓樓唱歌。
二、寨子裡會唱歌的人很多,同齡的人都會組成歌班,熟悉之後也可以跟他們一起練歌。
三、非春節或沒有團隊包場演出時,可親客棧的老板幫忙聯系歌隊來一場小型的表演,最少也要五個人出場。
四、距離小黃五公裡有個叫黃崗的寨子,隔年會有“正月初七抬官人”的活動,如果趕上去看看也是很熱鬧的。從江開往小黃的班車可以到黃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