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圖》的主題是啥?
日期:2016/12/14 11:14:33 編輯:中國古代建築隨著故宮博物院建院90周年而展出的《清明上河圖》目前已經撤出展覽,很多觀眾也是為了此畫而忍受六七個小時的排隊。《清明上河圖》名氣大、吸引人,但對於它的解讀卻不盡相同。故宮博物院研究室主任余輝近日撰文詳細闡述了古人對於《清明上河圖》的理解。

“故宮博物院藏《石渠寶笈》書畫特展”中展出的北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卷(以下簡稱《清》卷)已告別觀眾,這一次十分難得的是展出了卷後的全部題跋。在金元明三朝13家的14段題跋裡,記錄了他們對該圖的認識經過。古人和我們一樣,也經歷了一個由表及裡、由淺入深的認識階段,關鍵在於跋者能否結合畫家的生活背景去感知該卷的思想特性,與張擇端產生共鳴。
800多年前張公藥開始誤識《清》卷
並不是距離《清》卷時代越近的人越能把握其思想內涵,除了張著提供了張擇端的生平之外,其他金人給我們留下的是感歎和悲切,還有一些誤識。
最早給《清明上河圖》表現主題定位的是金代張公藥。張公藥(活動於十二世紀中後期),滕陽(今山東滕州市)人,其祖父張孝純(?—1144)是太原的降金大臣,張公藥受蔭入仕。他在跋文裡認定《清》卷的繪畫主題是表現徽宗宣和年間的“升平風物”、“好風煙”、“繁華夢”,這一認識對今人影響極大,許多人據此確定該卷的繪畫主題是表現徽宗宣和年間的“太平盛世”和“政治清明”中的“繁華”景象。
接下來的張公藥、郦權、王磵和張世積4位金代文人對《清》卷進行了相似的解讀。他們都是漢人,常結伴到宋宮遺址和廢墟去吟古懷舊,責怪亡國之君宋徽宗、抨擊蔡京、童貫,或是感歎舊城不在。北宋滅亡已經半個多世紀了,他們均沒有在北宋徽宗朝的生活記憶,憑借著主觀臆測畫中景物的位置,絲毫沒有考慮張擇端為什麼要畫這張畫。

650年前李祁最先看破張擇端動機
元代三位題跋者的惆怅之感漸漸消退,進入了藝術史范疇的思考。可以說,楊准是最早覺察到張擇端繪制該圖是有用心的,繼續進行探究的是李祁,他以其獨特的社會敏感開始探尋張擇端真正的畫意是什麼,告誡人們不要“嗟賞歆慕”該圖,提出畫家“猶有憂勤惕厲之意”。
楊准(生卒年不詳),泰和(今屬江西)人,擅長文章,當時的朝臣虞集、揭傒斯等都非常欽佩他。至正壬辰(1352),他在故裡泰和題寫了該卷,開始對張擇端的作畫動機進行了揣摩:“吾知畫者之意,蓋將以觀當時而誇後代也。不然則厄於時而思殚其伎。以傑然自異於眾史也。……其用心亦良苦矣。”畫家是為了形象地記錄客觀歷史,楊准開啟了後人對張擇端作畫動機的研究。
650年前,具有突破性認識的是李祁(1299—?),茶陵(今屬湖南)人,元統年間(1333—1335)進士,官翰林應奉,後因老母多病,回到了江南任職,開始了他的地方官生涯,後來任婺源州同知,累遷江浙儒學副提舉。元末江南大亂,他躲入雲陽山中,飽嘗世事艱辛,入明後不仕。其跋文題於旃蒙大荒落年(1365),他以一個地方官員的目光敏銳地看到了汴京城繁榮的反面,首先提醒人們不要以“嗟賞歆慕”心態去玩賞該圖,其中“猶有憂勤惕厲之意”,即老百姓生活過得很辛苦(即“勤”),是令人擔憂的,街頭出現那麼多的險情(即“厲”),一定要引起警覺,張擇端畫這些就是要讓當時的人們為此擔憂、引起警惕。李祁還提到了《無逸圖》,他認為應將《清》卷與歷史上的勸誡類名畫《無逸圖》相類比。“無逸”的意思是不要安於逍遙享樂,它出自《尚書·無逸》:“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穑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唐開元年間,宰相宋璟抄錄了《無逸》全篇並繪成《無逸圖》獻給唐玄宗,表現了周公勸成王不要耽於享樂的故事,玄宗將《無逸圖》掛在內殿自律。此後,歷代朝廷確定了《無逸圖》的規谏作用。
李祁將《清明上河圖》與《無逸圖》都視為勸誡一類的圖畫,這是元人看待《清》卷的一大轉折,這越來越接近張擇端的作畫目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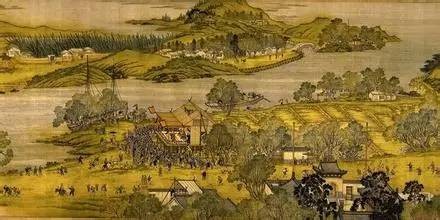
500年前邵寶最終看穿《清》卷
明代中後期的朝野盛行頹廢了的享樂主義,社會矛盾不斷加劇,影響到吳寬、李東陽、陸完、馮保等對《清》卷的認識,此外還有被裁去的邵寶跋文,他們形成了鮮明對立的兩種認識觀。最終是500年前邵寶的跋文看穿了《清》卷的用意。
1.以佞臣馮寶為代表的“心爽觀”
這是一群內廷重臣。如吳寬(1435—1504),長洲(今江蘇蘇州)人,明成化八年(1472)殿試獲第一,入翰林後一直侍奉宮中,官直至禮部尚書。還有權奸陸完(1458—1526),長洲(今江蘇蘇州)人,成化丁未(1487)進士,官做到吏部尚書。他的官宦生涯特別是他鎮壓劉六、劉七農民起義的暴行是不可能體察民情的。陸完的奸佞在於曾收受了寧王朱宸濠的巨賄並給予暗助,寧王起兵犯上被俘,陸完入獄,險些被殺。劫後余生、心灰意冷的他在1524年跋文裡不會替朝廷感慨社稷之難。吳寬和陸完長期脫離社會底層,遠離民情,不可能看出該卷所涉及的社會危機,他們作為收藏家只是關注《清》卷的收藏問題。
在此基礎上,馮保(?—1583)形成了他的“心爽觀”。他是深州(今河北深縣)人,嘉靖年間(1522—1566)入宮,萬歷年間(1573—1620)官司禮監掌印太監,死後家產被抄,《明史》將他列在佞臣之中。馮保早年淨身入宮,沒有接觸過社會底層,渾然不知稼穑之難。他在侍奉萬歷皇帝的空暇時,讀到了御藏的《清明上河圖》卷,他看到的是“人物界畫之精,樹木舟船之妙”,給他帶來的僅僅是十分膚淺和麻木的“心思爽然”而已。

2.以李東陽、邵寶等能臣為代表的“警世觀”
明代從李東陽開始,對《清》卷的認識越來越深入。李東陽(1447—1516),茶陵(今屬湖南)人,是李祁的五世從孫,他繼承了高祖的“憂勤惕厲說”。天順八年(1464),18歲的他登進士第,官至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他於平素關注朝政得失,曾多次谏上,如孝宗弘治五年(1492),他借《孟子》七篇大意,累數千言,批評時政得失。弘治十七年(1504),他上疏天津旱災、江南、浙東饑荒,親自查訪災區,指出國家吃閒飯的人太多,對老百姓來說,差役頻繁,苛捐雜稅太重,抨擊朝廷官員大肆靡費。
由於他熱衷於谏言甚至極谏的個性,滲透到觀覽該卷之中。他的感受是“獨從憂樂感興衰”,深感守住社稷江山是很難的,但失去實在是太容易了;一幅畫,可以看出時代的興衰、家業之聚散,這可真值得關注和借鑒啊!李東陽在1491年的跋詩裡還提到了《流民圖》:“豐亨豫大紛此徒,當時誰進流民圖。”那是北宋神宗朝舊黨的安上門監守、光州司法參軍鄭俠差遣畫工李榮作《流民圖》,奏報給宋神宗,以阻止王安石變法。顯然,李東陽由《清》卷聯想到了《流民圖》,可知他更多地看到並思考著該圖中的負面景象。
經筆者查驗,金元明的題跋紙都有不同程度的被古人裁剪,尤其是明代題跋最為明顯:明代接紙的第一、二、三、四段的長度分別為60、133.4、61.6和107厘米,可以推定,明代接紙的單張長度為133厘米左右,另三張接紙明顯短少,其中定有跋文被裁掉。全卷跋文接紙處均有“畢沅秘藏”、“畢”和“畢泷審定”的騎縫章,說明明代段被裁剪是在畢氏兄弟手裡或之前在重裱時完成的。裁去的目的主要是接在《清明上河圖》赝品的後面,以增加欺騙性。
其中裁去最重要的是邵寶的跋文,他的跋文原來就在其師李東陽跋文的後面,據其內容,應為真跡。邵寶的跋文後來被抄錄到清代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匯考》(吳興蔣氏密均樓藏本)畫卷十三裡,被劉淵臨等學者發現:“……若城市、若郊原、若橋坊第肆,無不纖纖悉悉攝入乎其中。令人反復展玩,洞心駭目……但想其工之苦,而未想其心之猶苦也。當建炎之秋,汴州之地,民物庶富,不繼可虞,君臣優靡淫樂有漸,明盛憂危之志,敢懷而不敢言,以不言之意而繪為圖。令人反復展閱,觸於目而警於心,溢於缣毫素絢之先。於戲!其在斯乎!其在斯乎!二泉邵寶識。”
邵寶(1460—1527)在明代是一位有政聲、有氣節的重臣,無錫(今屬江蘇)人。他3歲喪父,少年苦讀,成化二十年(1484)考中進士,官許州知州,此後他長期任職地方官,關注民生,移風易俗。他打消了江西農民在出土甲骨的土地上犁田的恐懼感,還改變了陳棺不葬等陋習。邵寶對權貴則是毫不畏懼,拒絕了寧王朱宸濠向他索要詩文的企圖。正德四年(1509),邵寶進京總管監督水路運輸,太監劉瑾誘逼邵寶陷害原水運長官平江伯陳熊,邵寶不從,於是被趕出北京。後來,劉瑾被處死,邵寶才被重新起用,一直晉升到南京禮部尚書。邵寶為官的格言是:“吾願為真士大夫,不願為假道學。”他是“茶陵詩派”盟主李東陽的得意門生,接著李東陽的跋文後繼續題寫,進一步闡發了他們對《清》卷的共識。
邵寶不同意金代張公藥的“升平觀”、明代馮保的“心爽觀”,就該圖的畫意提出了相反的意見:他“反復展閱”張擇端在鋪展汴京城清明節商貿繁華的景象,發現了使他“洞心駭目”和“觸目警心”的一系列社會問題。他很自然地將日常的從政觀念帶到了繪畫賞析中,與張擇端產生出共鳴。他認為該圖的主題是“明盛憂危之志”,邵寶進一步發現了這個秘密,他的內心十分激動!遺憾的是,該卷後的邵寶跋文被裁去,以至於他的觀點在今天幾乎被埋沒了。
元明清三朝文人的題跋留下了各自不同感受,這已不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視角問題,而是“喜者見喜,憂者見憂”的觀念問題,即不同執政觀、不同精神世界和不同宦跡的文人官僚,對該卷所繪的一系列景象產生出截然不同的思想判斷。張擇端是一位憂患之士,後世只有與他有相同心境的人才能產生共鳴。像馮保這種長期養尊處優的宦官和權奸陸完是無法感受到的。大凡體恤民情、敢於谏上者如李東陽等、或長期任職地方的親民之官且富有正義感者如李祁、邵寶等,都能在不同程度上感悟卷中的“憂樂”或“警心”之意,特別是邵寶的跋文,深刻地揭示出圖中的盛世警言,幫助今人打開了重新認識《清》卷的視窗。
因此,我們對《清》卷的深入探討不能無視古人的客觀認識;也不能拿離我們最近的封建王朝清宮畫家的行為標尺來度量張擇端畫《清》卷的勇氣。宋代朝廷鼓勵谏言,形成了那個時代憂患的開明政治和社會風氣,除了朝官的文谏,還有文人的詩谏、畫家的畫谏等,甚至民間雜劇家的戲谏可以一直演到徽宗的面前。這些,是張擇端繪制《清》卷的社會歷史背景之一,才有了畫中的種種警示。
(來源:網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