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應是文化先覺者 專訪著名文化學者馮骥才
日期:2016/12/13 23:10:50 編輯:古建築紀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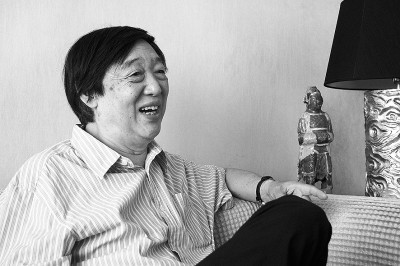
馮骥才

馮骥才畫作《冬日的詩》
因為在北京畫院舉辦“四駕馬車——馮骥才的繪畫、文學、文化遺產保護與教育”展,著名文化學者馮骥才方能夠在北京持續待上十余天。然而就是這十余天,每日工作也安排得滿滿當當,這一點我們是十分清楚的。所以,當我們在9月15日晚十點半提出第二天專訪的要求時,心裡並未抱什麼希望。出乎意料的是,他的助手很快回電說,馮先生已將第二日上午的原定日程作了修改,給記者騰出一個小時采訪的時間。
9月16日上午9點整,記者敲響北京某賓館1918號的房門。開門的正是馮骥才。“歡迎,歡迎!”很熱情。“記者的采訪,我一定要接受的。”還未落座,他便道:“我看到前兩天你在頭版頭條登的那篇保護老建築的文章了,不少文物界的朋友跟我提起,大家都很欣賞,認為有力度啊。”拿出9月13日的本報,他指著《老建築,別都拆了》一文贊不絕口:“寫得很深刻,很好。而且你們敢於在頭版頭條登出來,《光明日報》有膽識!”
於是話題就自然而然地從文化遺產保護開始了。
“知識分子應是文化先覺者”
征得記者同意後,馮骥才點燃了一支香煙。記得第一次專訪馮骥才,面前的桌上也有一包香煙,但他始終沒去碰它。
那是在天津一個普通居民小區的一套單元房裡,當時是馮骥才工作室的辦公地點。時間是2003年2月21日。三天前的18日,由馮骥才倡導和領導的“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正式啟動。
采訪被安排在一間幾乎被各種木制門窗、建築構件塞滿的所謂客廳裡進行。采訪中,他指著那些老物件有些激動地說:“能夠讓自己的文化損失在我們這一代人的手中嗎?能夠叫後人完全不了解先人這些偉大的文明創造嗎?不能!所以,現在第一位的是‘搶救’,而且是十萬火急!”
回憶起10年前關於搶救工程的動意,他提到了幾位著名的文化大家。當年,他跟啟功、季羨林、於光遠等先生一起在北師大開會,共同呼吁緊急搶救民間文化,並向年輕學子們發出著名的“把書桌搬到田野上”的號召。說起工程啟動之初工作之難,馮骥才吐出一口煙,略帶調侃地說:“他們可以花很多錢請客吃飯,一說要保護民間文化——對不起,沒錢。”
令人欣慰的是,十年過去,這種情況已大為改觀。他強調:“文化自覺,這十年的歷程顯現了我們的文化自覺。”中國在搶救非物質文化遺產方面走在了世界前面。“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開始工作時,國際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公約還沒簽署,2003年聯合國才將非遺列入文化遺產保護內容。“這說明中國的知識界是有文化自覺、有文化使命的。”
“我要強調文化先覺,”他加重了語氣。“我們的目標是文化自覺,這是全民的;而知識分子應該是當中的先覺者。”他認為,知識分子的特點是有前瞻性,不但可以用科學的眼光研究社會,還能運用逆向思維思考生活,因此應該是有文化先覺的。“當整個社會迷惘時,知識分子應該先清醒;當整個社會過於功利時,我們要給生活一點夢,美好的夢,給一點理想和精神的東西。”
“責任是第一位的”
“責任、擔當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優良傳統。我們這一代人由於與國家民族的命運糾結太緊,責任意識透入骨子裡,完全無需掂量。責任是天經地義的。”馮骥才如是說。
責任感,強烈的責任感,這一感受在采訪中不斷被強化。
人們認識馮骥才是緣於他的文學和繪畫作品,而他自己說,這兩種藝術於他是天性、是性情式的表達,文化遺產保護和教育則是責任、是自己的選擇。“責任是第一位的。”他說。
更重要的是,“責任”在他絕非只是說說,而是切實去承擔了。
因為責任,在絕大多數人對民間文化的內涵還沒有什麼認識的時候,他就以一個志願者的身份開始搶救與保護行動了。1994年,他在報紙上看到了天津市要大規模拆除老城、改建新城的消息。這意味著擁有著悠久歷史的天津城、義和團重要的塘口、五四運動的遺址,包括中國最早的電報局,還有地域文化裡面數不盡的財富,都將灰飛煙滅。他急了,拿出自己的一筆稿費,請了近百人,有歷史學家,有建築師,把整個老城考察了一遍,用相機全部拍下來。一年多的時間,拍了3萬多張照片,選出2000張印成畫冊。從市委書記、市長開始,到各局局長,每人送一本。最終,他們的努力有了結果,天津市委決定留下這筆巨大的文化財富。
在搶救估衣街的那段時間,他被天津媒體封殺,第一篇呼吁搶救的稿子是在《光明日報》2000年1月28日頭版發的。這件事他記得非常清楚。
因為責任,他幾乎放棄了鐘愛一生的文學創作。原因很簡單,沒時間寫。只有在長途車上,他才有機會閉上眼睛,將埋在心裡的故事翻出來,構思一下;可往往是剛剛“過瘾”,就到地方了,於是這個故事只能再次收藏進心底。
“始終不能落在紙上,不遺憾嗎?”記者問。“當然有遺憾。”他直言不諱,“但是創作只是我個人的事情,而一個民族的文明傳承更重要。”
因為責任,他幾乎賣掉了自己所有的畫作。他說,這麼做不只是要籌措資金,更主要是想喚起人們對遺產保護的關注。他沒有白費勁,如今捐贈者的名單越來越長,尤其是那些文化名人的參與,使更多的人知道了文化遺產保護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責任是第一位的。”馮骥才說得似乎很輕松。但在它的背後,這位古稀老人的付出是巨大的。
“把民間文化擺到廟堂裡”
“我六十歲的時候,接了兩件大事。”馮骥才又點了一支煙,卻沒怎麼吸,只是任由煙霧在眼前飄散。
在別人退休、可以頤養天年的年齡,馮骥才擔任了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的主席,同時受聘於天津大學,擔任馮骥才文學藝術研究院院長。前者讓他可以團結更多的有識之士,共同搶救保護民間文化遺產;後者,成為他進入教育界的開端。
既然是以馮骥才的名字命名,學院難免帶有他的色彩與氣息。2012年年初,一個寒冷的冬日,我第一次走進這座外形很現代的學院,立刻被無處不在的傳統文化氣息籠罩了。院子裡,一座古門樓,一個石雕,一塊長江纖夫石,無言地彰顯了學院所追求的歷史與人文的內涵,並與這座現代建築形成時代性的對比。就連電梯其實也是一件別出心裁的雕刻作品——“詩之門”。左邊刻的是英文的《奧德塞》,右邊是中文的唐詩,寓意打開門,就進入了人類的文明。而印象最深、感受最深的,還是它的博物館。
學院“博物館化”是馮骥才的追求。他認為大學應有一個功能——文化保存。他的想法是,把知識保存在圖書館,信息保存在數據庫,實物保存在博物館。他說:“在博物館裡,感受比看更重要。”所以,他對展覽的細節十分在意,從整體色調到每條說明文字,都親自動手。“我把做博物館當成一種創作,也作為一種享受。直到今天,還有一些美妙的博物館計劃。”
學院現有7個博物館,每一個都不大,卻都很精致,剪紙、年畫、雕塑、藍印花布、木活字印刷、民間畫工等,包羅了諸多民間文化種類。記者最愛的莫過於“跳龍門鄉土藝術博物館”了。民間傳說鯉魚跳過龍門便化龍升天。在這裡,馮骥才把民間文化的精華搬進博物館,正如他所說,“把民間文化擺到廟堂裡”,就是想讓大地燦爛的草根文化登堂入室,化魚成龍。
他說,促使自己到大學工作的最重要原因是,當今社會真正的文化學者匮乏,大學急需造就新人。
“目前能夠在非遺保護一線獨當一面的學者,幾乎全是60歲以上,急需後備力量。”他認為學生最需要的,一是視野,二是責任,三是能力。他也清楚地知道,一個人到了青年時,你不可能改變他,只能影響他。所以他盡量用學院的一切——硬件、軟件、思想、方法去影響學生,把學生的未來與時代的需要連接起來。“我最希望的是他們能夠走在時代的前沿,有思想也有能力,關切時代不空談,有‘天降大任’於我之感。”從課堂講授到田野調查,甚至連學院裡濃郁的民間文化氣息,都是要讓學生們浸潤其中,感受其魅力。“有個現代文學的博士生也轉到文化遺產了。”話語間臉上閃過一絲笑意。
另一方面,在中國,且不說省市縣級的非遺項目,僅現有的1300余項國家級非遺,絕大多數缺乏學術支撐,在它們後面的大多只有政府管理部門或開發商。這很容易造成所謂“保護性破壞”,即為了經濟利益而篡改非遺本體。而在日本、韓國,他們的每一項非遺都有專門的人在研究,換言之,每項非遺後面都有專家學者在支撐。“當務之急,是盡快培養有責任感、有事業心的年輕隊伍,讓非遺保護得到學術的支撐。”他說。
“四駕馬車全是為了一駕車”
話題回到正在展出的“四駕馬車——馮骥才的繪畫、文學、文化遺產保護與教育”展上。
“這是我對自己70年人生的一種梳理。”馮骥才思索了一下,“70年裡能做和所做的事太多太多。我只是揀了我最傾心、最重要的四個方面。”
直視記者的眼睛,他認真地說:“告訴你,這話我沒對別人說過,其實四駕馬車全是為了一駕車。”不用說,這駕車就是文化遺產保護。
“四駕馬車”展覽中有一幅作品,是馮骥才在開展前一天連夜創作的。那一夜他想到70年總結完了,之後要做什麼?——“古村落搶救保護,這是我今後最主要的工作。”一個曾在皖南見過的古老的木門撞進腦海。
畫面上是一座徽派建築的門。藍綠色的油漆已斑駁,但形制優美。陽光將樹影投在門上,光影中寫滿了歲月的深遠。畫上,馮骥才寫了一句話:“每一扇門都是歷史關上的,都等待著我們打開。”
馮骥才,這位中國文化的先覺者,已經做好再一次出發的准備。在有生之年,他還將繼續不懈地為中華民族、為子孫後代,去打開一扇又一扇被歷史關上的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