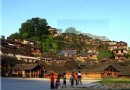中國古村落“爭奪戰”
日期:2016/12/13 21:11:10 編輯:古建築紀錄
在北京通州區一個不起眼的院落裡,有幾間總面積接近足球場大小的倉庫,裡面擺滿了從全國各地農村搜羅來的古舊家具、農具和各類飾品,市場價值不少於2個億。
類似的倉庫,《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在上海的青浦等地也遇到過。這些從中國鄉村低價收集來的古舊物品,很大一部分以數倍、數十倍甚至更高的價格賣出,進了私人豪宅、高檔會所、酒店、大公司甚至是一些駐華使館。
不過,與這些文物收藏者、文物販子相比,另一批人“胃口”更大,他們往往把整個古鎮、古村落“吞下”,整體包裝進行旅游開發,甚至拿去上市。
正如對礦產、石油、水力資源的爭奪一樣,眼下,在廣袤的中國大地上,在最偏遠的鄉村,那些最具鄉土特色和旅游價值的歷史遺跡、風土民情、古宅院落、民歌民調等資源,幾乎都有一只或幾只外來之手在操控。
那些外來之手,與當地政府合作好的,可以共同發財;合作不好的,則可能被掃地出門。而另一些村落則在經濟開發大潮的沖擊下,正在從中國文化的版圖中被抹去,變成另一種廉價的資源。
“拉鋸”肇興侗寨
7月16日,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縣。站在山坡上,遠遠就能看到在淡淡雲霧中時隱時現的侗寨,檐角高翹的鼓樓格外耀眼。這便是被譽為“中國最美的六大鄉村古鎮”之一的肇興侗寨。
肇興侗寨是黔東南侗族地區最大的村寨,寨子坐落在群山環抱的山間壩子中,清澈的肇興河穿寨而過。寨門口懸掛著著名作家馮骥才題寫的“侗鄉第一寨”橫匾。寨中房屋為干欄式吊腳樓,鱗次栉比,錯落有致,全部用杉木建造,屋頂覆以小青瓦,古樸實用。
在肇興侗寨,有五座鼓樓、五個戲台和五座風雨橋。肇興不僅是鼓樓之鄉,也是歌舞之鄉,侗族大歌、蟬歌、踩堂歌、攔路歌、琵琶歌等聲調婉轉悠揚,旋律優美動聽。其中,侗族大歌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傍晚時分,本報記者抵達寨子時,天空中正下著細雨,走在青石板路上,可以看見寨子裡悠閒的人們有的坐在家門前錘布、紡紗,有的坐在鼓樓下打牌、納涼。路上游人很少,偶爾才能見到一兩個背包客。
由於歷史和地域等原因,長期以來,這一帶一直處於相對封閉的狀態,原生民族人文生態系統保存完整。“上世紀80年代之後,肇興侗寨才陸續有游客進入,"打花臉"等傳統節目也被逐漸挖掘出來。”肇興鄉黨委書記黃傳文對本報記者說。
2003年,民營企業貴陽世紀風華旅游投資公司進入肇興。“按照世紀風華公司的設想,肇興侗寨整體打包,實行景區式封閉管理,門票等收入與當地分成。”曾經負責貴州世界銀行項目的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教授張小軍對本報記者說。
據世紀風華總經理熊希華此前向媒體介紹,到2010年,世紀風華在肇興侗寨已投資4000多萬元,建成兩個賓館,修整了游覽步道,平整了4個停車場,還成立了一個30人的侗族大歌表演隊。
與此同時,家庭旅館也在肇興侗寨興起,到2010年,整個肇興侗寨家庭旅館超過100家,景區的接待能力超過10萬人。2008年,僅法國、美國、瑞士等歐美國家游客到肇興侗寨旅游的就達3萬人次以上,肇興成為貴州鄉村旅游人氣最旺的地方之一。
但好景不長。“從2009年起,廈蓉高速公路和貴廣快速鐵路的建設,給肇興侗寨的可進入性帶來了很大挑戰。”黃傳文說,同期肇興侗寨景區的自身建設,也給當地旅游業帶來了負面影響。
而業績的下滑也加劇了世紀風華公司與當地政府的分歧。“當時的考慮是由政府主導,企業運作,群眾參與,共同致富。”黃傳文對本報記者說,但實際操作發現,完全按商業化模式的路子行不通。
他解釋說,政府、企業和群眾都有各自的考慮。“企業要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甚至會過度開發,群眾也希望盡快賺到錢。而政府的一些想法,老百姓也不認同,甚至認為政府站在企業一方。”
黃傳文並沒有告訴本報記者他們與世紀風華公司究竟在哪些項目上產生了分歧,他只是籠統地說:“天長日久,雙方的矛盾就會加劇、惡化。”當地村民則反映稱,世紀風華公司曾一度打算封閉鼓樓,對外收取門票,但遭到了村民們的抵制。
“世紀風華已經確定要撤出了,我們正在談回購的事。只是目前還沒有就回購價格達成共識。”黃傳文透露,世紀風華公司撤出後,肇興鄉會成立一家政府下轄的旅游開發公司,這樣一方面便於融資,另一方面也便於管理。
“從周邊其他景區的情況來看,目前這條路比較可行。”黃傳文說。
肇興鄉鄉長林世華告訴本報記者,肇興有可能在今年底由鄉改為鎮,而設鎮的標准是人均年收入在4000元以上,目前肇興鄉人均年收入只有3000多元,政府急需增加財政收入。
據黎平縣旅游局透露,今年黎平縣也將投入8.29億元全力打造肇興景區,資金主要用於景區基礎設施建設,包括排污系統、步道建設等工程。
截至發稿,本報記者一直沒有得到世紀風華公司有關撤出肇興的任何說明,其在肇興侗寨的兩個酒店仍在營業。
宏村傳奇
把破敗的鄉村包裝成旅游景區,變成一條賺錢的路子,有不少失敗的,也有許多成功的。中坤集團運作的安徽省黃山市古村落宏村就是一個樣板。
在安徽省黃山市黟縣縣城東北10公裡處,有一座始建於南宋紹興元年、至今已有800余年歷史的古村落——宏村。
宏村有432戶1280人,現存明清(公元1368年~1911年)時期民居158幢,其中137幢保存完整。整個村落呈“牛”形結構布局,其中最為突出的是有400余年歷史的月沼、南湖、水圳等水利工程,這種當時十分先進的村落水利設計,不僅為村民解決了消防用水,還調節了氣溫,為居民生產、生活用水提供方便,創造了一種“浣汲未防溪路遠,家家門前有清泉”的生活景象。
中坤集團與宏村的合作,追溯至1997年9月6日,中坤集團與黟縣政府官員在黟縣碧陽山莊洽談,商定共同組建“京黟旅游股份有限公司”,黟縣以古民居旅游資源和古祠堂群建設項目土地使用權為參股方式,中坤集團以現金方式逐步投入黟縣,以開發經營黟縣包括宏村在內的古村落。
當年9月27日,雙方正式簽訂了合作協議,中坤集團獲得黟縣宏村、南屏、關麓三個古村落為期30年的開發經營權,總投資2518萬元。
而在1997年前,宏村與現在很多行將消失的古村落一樣,面臨著現代化沖擊下的一系列問題:部分古建築年久失修,風雨飄搖;各種新式建築頻頻出現,與傳統風貌格格不入;不恰當的修補,使宏村不倫不類。最重要的是人去樓空的尴尬,青壯年外出求生,古村落的文化傳承面臨危機。
1997年,中坤集團進入宏村,邀請清華大學、同濟大學的古建築保護專家實地考察,共同研究制定《宏村保護與發展規劃》。1999年,該規劃通過了國家建設部、文物管理局等有關單位組成的專家評委會的審核。此後,中坤集團按照規劃要求,投入數千萬元對宏村進行修復。
值得一提的是,宏村的保護性開發同樣采取的是“政府主導、企業運作、村民參與”的三方合作模式,所不同的是,企業的角色在宏村很“淡”。
在當地政府的主導下,宏村建立保護管理機制,成立了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管理委員會和世界文化遺產辦公室,綜合協調、指導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管理工作。成立遺產管理委員會、遺產保護管理監察大隊和民間保護協會,強化保護工作的日常監管監控,形成了縣、鎮、村、民間組織四級保護管理網絡。
黟縣政府也制定了《黟縣西遞、宏村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管理辦法》及實施細則,以政府令形式發布實施。為確保保護規劃、制度與措施落到實處,黟縣嚴格依法管理。對違法違章建設,一經發現立即拆除。自2001年來,宏村共處理違章建築53戶,面積1221平方米,拆除違章篷位攤點1353.3平方米,封牆洞22個。
中坤集團董事長黃怒波告訴本報記者,對傳統建築中坤集團采取了分級保護的措施:被列為一級保護的,實行嚴格保護,加強維修,用作旅游參觀。采用原始材料並嚴格按照原樣修繕、復原,嚴格控制並整治周圍環境;被列為二級保護的,對內部、外觀恢復原貌,定期維修、適當復原;對以居住為主的建築,在不影響主體建築的前提下,可修建輔助用房以改善居住條件;被列為三級保護的,重點保護外觀,內部可適當調整更新,適應現代生活需要。
與此同時,政府鼓勵村民從事傳統的木雕、磚雕、石雕等手工藝品開發,售賣當地的茶葉、梅菜燒餅、野菜等特產,按照傳統習慣在溪水邊浣衣、用圓匾晾曬干菜等,在展現傳統生活形態的同時獲取收益。
2000年,宏村正式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為世界文化遺產。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專家考察評估的結論為“中國古村落的典型”。由於其屬於企業先行介入保護後獲評,因此宏村也成為全球第一個由民營企業參與管理並成功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古村落。
“宏村每年數千萬元的門票收入中有33%返還給當地政府與村民。旅游業已成為當地村民增收的重要途徑。”黃怒波說。
目前,宏村村民有300余戶在從事與旅游相關的生意,約占整個村總人數的83%。村民收入67%來自於旅游業,此外,宏村村民私人開辦旅館、飯店30多家,本村和鄰村客棧床位12000多個,各類攤點、商店300多個。景區內外的商鋪共為當地提供了10000余個就業機會。
我國目前有包括麗江旅游、黃山旅游、中青旅等旅游類上市公司約20家,其中不少已介入古村落的開發。
古村落保護與推土機賽跑
無論是肇興還是宏村,在各具特色的村落中都是幸運的,至少具有鄉土特色的東西被保護住了。而為數眾多的村落則在經濟開發的大背景下,正在從中國的文化版圖中被抹去。
“在新農村建設和土地整治過程中,由於缺乏生態景觀理論和技術指導,致使原有村莊的鄉土氣息消失殆盡,出現嚴重的"景觀污染"或"千村一面"現象,導致孕育不同地域文化的生產、生態和生活的鄉土景觀嚴重受損,生物多樣性降低。”在中國科協舉辦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國土資源部土地整理中心副主任鄖文聚對本報記者說。
他告訴本報記者,通過對全國255個村莊的人居環境調查及典型案例研究顯示:約60%鄉村景觀風貌“一般”或“差”。
馮骥才曾憂心忡忡地說:“現在中國的村落,除去西塘、甪直、南浔、周莊、同裡、烏鎮這所謂的江南六鎮保護得還比較好外,其余基本上正在消失。”
古村落的保護正在與推土機賽跑。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普查結果顯示,我國230萬個村莊中,目前依舊保存與自然相融合的村落規劃、代表性民居、經典建築、民俗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古村落,已由2005年的約5000個銳減至不到3000個。
2003年以來,住建部與國家文物局聯合公布了五批共350個中國歷史文化名鎮名村,其中名鎮181個,名村169個。然而,在現代文明與工業化的快速推進下,許多古鎮在城市化進程中遭到了嚴重損毀,有的已經永遠消失了。
“農村村寨是整個文化的資源地和持有地。這個基礎一旦喪失,中華文明的多樣性就會整體蛻變。”音樂制作人陳哲說。
17日,在肇興召開的“重估鄉村價值論壇”上,張小軍對本報記者說,全球化的強勢就在於它正全面取代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摧毀了一些從事傳統狩獵業、采集業的部落文明,特別是由於經濟增長的需要建設一些大型建設項目如大壩等,導致了大規模的人口遷移。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剝奪了當地居民選擇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這實際上是將當地的文化連根拔起。”張小軍說。
一個地方鄉村資源的豐富程度取決於原生態文化是否多樣和是否真正具有本地特色。“黎平縣有403個村,我們不貪多,做10個就夠了,每個村寨都有幾個精品文化節目。”黎平縣旅游局羅永光說。
與一些鄉村資源開發的做法不同,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眼下正在與黎平縣打造差別化的侗族生態旅游區。“把侗族的歌曲、服飾、建築、飲食、工藝包括農耕文化,在不同旅游產品中進行展示。”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執行秘書長窦瑞剛說。
“只有產業發展了,才能吸引年輕人回到鄉村,傳統文化資源才會得以保存、創新,被不斷地挖掘出來。”窦瑞剛說。
也是在論壇上,貴州省政府副省長謝慶生指出,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全球化的過程是任何人不能阻擋的,把保護簡單地理解為全封閉或什麼都不能改變也是不對的。比如,傳統的禮儀節慶習俗以及音樂、舞蹈、戲劇等,首先是保護好產生這類民族文化的生態環境。另一個途徑,是把民間的技藝提升為藝術,由專業的藝人來保存、傳承它。
今年4月,國家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文化部、國家文物局和財政部聯合下發《關於開展傳統村落調查的通知》,以全面掌握我國傳統村落的數量、種類、分布、價值及其生存狀態。按照時間表,各地省級住建部門要在本月15日之前將調查結果上報給這四個部門。
- 上一頁:中國古鎮保護網理事會章程
- 下一頁:首屆中國吉州窯文化研討會召開
熱門文章
熱門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