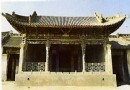徽州尋思—牌坊下的幽靈
日期:2016/12/15 15:33:50 編輯:古代建築名稱 從黃山出發,我們一行冒雨前往原徽州府所在地歙縣。沿著一條泥濘的田間小路(五年後的今天,或許馬路已經拓寬而面目全非了),我們徑直來到遠近聞名的理教重鎮原兩淮鹽務總督鮑志道的故鄉——棠樾。
從黃山出發,我們一行冒雨前往原徽州府所在地歙縣。沿著一條泥濘的田間小路(五年後的今天,或許馬路已經拓寬而面目全非了),我們徑直來到遠近聞名的理教重鎮原兩淮鹽務總督鮑志道的故鄉——棠樾。
抵達的時候雨奇跡般地停了。從依稀游玩的人群中,我的目光便迫不及待地投向那七座巍然挺立的古老牌坊。牌坊從南到北依路排開,蔚為壯觀。從前往後分別是:鮑象賢尚書坊、鮑逢昌孝子坊、鮑文淵繼妻節孝坊、樂善好施坊、鮑文齡妻節孝坊、慈孝裡坊和鮑燦孝行坊。
在江南象這樣的牌坊隨處可見,且以貞節牌坊為最多。但在這裡如此高密度的呈現,實屬罕見。我想如果沒有對程朱理學深入骨髓的貫徹怕是很難實現的。無疑它就是封建禮教的產物。
據說在當時的歙縣流傳著這樣的一句諺語:“嫁到棠模、棠樾,餓死也情願”。在明清兩代,棠樾便是有名的商賈出沒的地方。在牌坊附近的鮑氏宗祠中,關於誠、信、不克斤扣兩等鹽商的經營信條依然清晰可見。正是棠樾所造就了一批“商業巨子”,從而才有對於禮教的重新規范與深入。他們要努力地使桑梓鄉土塑造成“慈孝天下無雙裡,錦繡江南第一鄉”的真正意義上的“程朱阙裡”。
我們都曾聽過有關古代貞女與烈女傳奇的生動而悲涼的故事,但我們卻很少想過,她們因什麼而傳奇為什麼而生動與悲涼。我們只能聽憑自己的感覺在人們約定俗成的思維慣性之下而生發眾口一詞的感慨。站在那些不知經歷了多少淒風苦雨而昂首挺立的牌坊面前,我能感到的只是淒惶與不安。那些刻在牌坊上的名字象一個個弱小而堅強的幽靈一樣,向我的思維發起了猛烈的沖擊。
曾在千年以前,他們用自己的言行或身軀為寧靜的棠樾(封建社會)送上了最濃重的厚禮。他們是真正意義上的殉道者,他們用自己並不偉大的言行來捍衛自身崇高的精神信仰,並以此來為子孫後代樹立一個能夠警示世界的典范。他們是無私的,無私得看不見自己的軀體存在。他們的眼裡只看見別人幸福的生存,並為那些幸福的生存,義無反顧地獻上自己僅有的一切。
在棠樾的七座牌坊中其中有兩座是貞節牌坊。在“忠孝節義”禮教信念中,“節”被擺在了一個很重要的位置。“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精神鴉片在不知不覺中吞噬著棠樾(古代)女子脆弱的心靈。她們在丈夫外出經商多日不歸的孤寂時分,只能苦澀地咽下思念的淚水,甚至要強忍著英年失夫的長久落寞直到自己安眠於九泉之下。
看著那群“黝黑的軀體”,我無法抑制自己內心的悲憫。我似乎瞥見那群孤獨的幽靈在一步步向我走來,帶著幸福安詳的微笑走來。我感到無地自容,也從沒有感到過如此的自慚,那微笑分明是對我發出的一聲尖銳的嘲諷。因為我知道在那個善意的微笑背後,都隱藏著一曲曲悲涼泣血的故事。
你完全可以沒有這樣的感覺,但你無法逃避的是他們曾經用心構築的真誠的逼迫與透視。他們或許的確都是一群很平凡的人,平凡得在他們的生前,並沒有多少人知道他們的名字。可他們從不拒絕瑣屑,拒絕冷漠,反抗命運的不公正安排。他們是用自己的意志告訴世界,我是對得起別人的人。而他們恰恰對不起的是自己。他們將自己畢生的心血甚至生命獻給了別人,而將孤獨長夜中悲伧的傷神與哭泣留給了自己。這就是棠樾(古代)女子的命運,而牌坊無疑則成了他們用心血築成的一個蒼白的象征。
好在歷史再也沒有了這樣的輪回。那些“殺人不見血”的道德禮教的“崇高”要義終於被定格在那個久遠的年代而一言不發。我們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那些只能感染與陶醉自己的人格范式一去不復返。因此我們自作多情的無奈裡,又從此平添了一份深深的遺憾、一份淡淡的滿足與欣慰。
- 上一頁:漳州明清牌坊
- 下一頁:桓台“四世宮保”牌坊